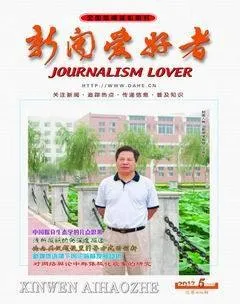中原文化的主流性与传播特点
【摘要】中原河洛文化在中国诸多区域文化当中具有主流性和辐射力,儒家学说是其内在核心。洛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传播辐射表现形式,但都体现出主流性、包容性和辐射力等特点。究史鉴今,对于今天繁荣与传播中原文化,增强中原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洛学;主流性;包容性;辐射力
自古以来,在华夏文化话语系统中,河洛地区始终被认为居于“天下”之中,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1]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儒学源头和后世流变几乎均在河洛地区展开,可以说,河洛文化自始就与儒学同质同构,河洛地区的文化演变与华夏文化主流演变同步。河洛地区一系列古代都城遗址的发现,尤其是属于夏代中晚期固定的都城遗址的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也为华夏文明找到了源头。后来十数个王朝在河洛地区建立大一统政权,使得这一地区长期成为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不为都蓟即为重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文化一定时期内实际上就是河洛文化。河洛文化一开始就占据了华夏文化的主流地位。
中原文化孕育洛学的产生
洛学为北宋中期程颐、程颢兄弟所创立。因其居住于洛阳伊川,一生主要学术和政治活动均在西京洛阳,所以人们把他们的学术思想称为“洛学”。洛学的出现既有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也有儒学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
唐宋之间,中国历史出现了五代十国这一段军阀割据、战乱纷争的分裂局面。伴随“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乱象的,是伦理纲常的败坏和宗法制度的废弃。手握重兵弑君夺权,文人士大夫“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3]。作为道德力量,儒学越来越没有感召力和约束力;作为思想学说,急需除旧立新,继往开来。
儒学本身在秦汉以后日渐衰微的状况令儒学后人痛心疾首。早在唐朝中期,柳宗元、韩愈就通过发起“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极力倡导儒学复兴。柳宗元主张“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4]。韩愈通过《原道》一文,论证了儒家的君子之道,批驳了佛教的小人之道,系统阐述了从尧舜禹、商汤文武、周公直到孔孟思想学说,并且认为这些正是儒家一以贯之的道统。通过《原性》一文,韩愈论述了性与情、善与恶的关系。韩愈门生李翱写了《复性书》,论述了性善情恶的观点。柳宗元、韩愈、李翱关于道统、性情、善恶的观点开了“洛学”的先河。
北宋建立以后,首都为开封,洛阳为西京,河洛处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有宋一代始终保持宽松的文化环境和优待知识阶层的政策,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行。印刷术的发明,儒学典籍得以大量刊行,儒家经书“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5]。而“宋初三先生”、欧阳修、范仲淹等时代知识精英畅言改革、怀疑经传、自由解经、重新研讨儒学典籍的治学思想,以及庆历年间“学统四起”的现象,也表现出富于忧患意识的学者复兴儒学的内在精神追求。
宋朝建立以后,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北宋统治者开始提倡儒家思想,抬高孔子地位。宋太祖、宋太宗曾亲自到国子监祭祀或拜谒文宣王,太祖将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作为定例。太宗恢复了孔氏后人免赋役的特权。宋真宗也于封禅泰山途中到曲阜拜谒孔墓。真宗甚至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太祖请王昭素在殿上讲《易经》,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宋仁宗在位期间的宰相多为儒学门生。表现出统治阶级重新建立一套适应并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理论体系的急切呼唤。
中原文化传播的主流性:洛学的“宗儒”地位
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阶段性表现,在宋代文化中起主导作用,而洛学则是理学最重要的流派。所以洛学的“宗儒”是显而易见的。
在洛学学派看来:“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6]就是说古代的学问是统一的,而现代的学问却分裂为三派。其中“文章之学”批判唐代文化偏重诗词歌赋,“训诂之学”批判汉儒治学只能寻章摘句,注经作传。只有二程自许的“儒者之学”才是学问正途,代表道学正统。程颐又将沉溺于“文章”、“训诂”和流于“异端”并称为“学者三弊”,“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6],认为只有剔除这三弊,才能回归儒学正途。洛学之所以旗帜鲜明地排斥训诂之学与文章之学,并非认为汉代经学、唐代诗赋造诣不够精湛。而是因为在二程看来,恰恰是汉代经学和唐代诗赋成就卓著,盛极一时,而导致偏入旁门,离开了孔孟学说之本意。程颐明确认为汉唐以来千百年间没有“真儒”产生,儒学正道没有得到传承。他们把传统儒学视为“圣人之学”,表明愿意以继承发扬孔孟所创立的传统儒学之道为己任,传“圣人之学”而实现天下“善治”的人生追求。
二程以宗儒为本,自幼读儒家经典,被称为儒学道统的继承人。程颐为学“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5]。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历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二程深入研究了儒学经典,并且对儒学经典重新作了阐释修正和解说,如《易传》、《书解》、《大学》、《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或者是运用儒家伦理纲常表述安邦治国的政治思想。从二程的志向追求、治学经历和学术成果等方面看,洛学源于儒而归于儒,宗儒的本质特点十分鲜明。
中原文化传播的包容性:洛学兼收佛道
洛学融会佛道,借用佛道成熟的理论特长,把体系紊乱、哲理思辨性不强,带有天命思想的传统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宋初学者表现出疑古惑经的勇气和反对固守前人的治学风尚。这种大胆独创而不随便迷信古人的精神对二程的影响很大。同时社会上盛行的儒释道相互融合的思想也为洛学借鉴吸收佛道有用成分提供了可能,逐渐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当时的佛教道教人士都曾论说三教合一的合理性,还能熟练引用儒学观点阐发本派思想。道士张伯端认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应该“混而同归”。[7]佛学大师契嵩主张“儒释一贯”,把儒家的孝和佛家的戒结合起来,证明佛教也讲孝道。[8]就连真宗皇帝也认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9]。
洛学援道论儒,主要在于吸收改造道教学说中的“理”“道”关系。二程洛学超越前人的地方主要在于自觉建立自身哲学体系,“天理”是洛学的全部理论基石。但是洛学“理”这一核心范畴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洛学还把老子思想中的最高范畴“道”移植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当中,将“理”“道”并列,“理便是天道也”[6]。在传统道教中,“道”为宇宙唯一本体,万物之源。“理”的作用在于阐释“道”这一范畴的内涵,即以“理”释“道”。到了洛学里,“理”与“道”地位并列,可以“理”“道”互释了。本来自老庄以来,清静无为、消极避世的道家学说大多数时间处于主流观念的外层。但是道家学说的理论创建却历经汉魏隋唐持续不断。到了真宗年间由政府主导进行了学术大总结。其理论体系远较注重经疏注传的儒学要精深圆润。二程非常赞赏道家的某些观点,认为“庄子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
洛学援佛论儒,主要在于借用改造佛教的心性学说,尤其是禅宗的心性观念。佛教学说富于思辨的哲理体系对思想学术界影响极大。宋代许多学者受佛学思想观念或理论体系的影响很大,“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10]。周敦颐曾经跟随佛印和东林寺常总研究佛法,张载“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11]。宋明理学又称心性学说。洛学在继承先秦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上,改造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以理为性,建立起洛学独特的心性论。尤其是禅宗慧能讲究“顿悟”,“明心见性”的悟道路径,对洛学富有启迪。由于二程“出入释老几十年”的治学经历,对于佛理有关心性的见解颇有感悟。所以,无论从体用关系上,还是从悟道路径上,洛学与佛教都有一定逻辑相通之处。
通过吸收改造道家“道”“理”的理论范畴,借鉴运用佛教的“心”“性”之用的关系理论,洛学将传统儒家学说由普通纲常道德和政治伦理学说上升为哲学化的理论体系。
中原文化传播的辐射性:洛学“闽学化”
一种理论学说的主流性并不总是和这一理论诞生的时代同步。有时候其主流价值要在下时代或更远的时间间隔之后才予以体现。先秦儒学并不是兴盛于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而是独尊于汉武年间。洛学主流性的显现也并不在二程生活的时代。自二程肇始,直到北宋末期,洛学始终处于和其他学派的相互斗争之中。尤其是和苏门蜀学和王安石新学的关系更为紧张。除了学术源流的价值取向、思想论说的逻辑方式不同的因素外,政治权力的斗争更是主要原因。出于党同伐异的需要,元佑更化时期司马光等当权人物曾经予以洛学大力支持,但时隔未几就被禁止。洛学“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程颐“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12]。不像新学,一开始就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独行于世者六十年”[13]。也不像关学,在张载有生之年颇为兴盛,但张载一死,“再传何其廖廖”[14]。但是作为有着主流潜质的洛学,创立之后能够“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15],而且弟子薪火相传,不断将洛学发展完善。到北宋结束,南宋偏安,随着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大量知识精英人士纷纷南下,洛学更是在南方以其“闽学化”的形式展现出主流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对洛学“闽学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主要是杨时、罗从彦、李侗和朱熹。洛学自二程肇始,因朱熹而集其大成,此间杨时、罗从彦、李侗道统相传,是洛学“闽学化”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递相传授,致力于二程洛学的传播和阐发,为闽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做了必要的准备。”[16]杨时更被人称为“理学大师”、“闽学鼻祖”。《宋史·杨时本传》中说:“其学得程氏之正。”康熙亲为杨时祠题写匾额“程氏正宗”。这是后人对闽学主流传承的多方认可。
杨时就学于程颢,程颢也对杨时另眼高看。杨时学成南归时,程颢“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6]。在二程的高足弟子中,“龟山独邀省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14]。杨时在洛学冷落的时候不改志向,积极传播二程之学。在洛学南传过程中,杨时首先发起对新学的猛烈批评,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新学以及王安石的新法。同时大力倡导洛学,以致“士大夫尊信其学者渐众”[15]。洛学在传播中发生歧异,尤其是二程弟子们所记载的大量语录不免失真,亟待整理。杨时重视洛学典籍整理,“以类相从”,亲手编辑整理了二程语录,用文雅的语言加以改写,修成《粹言》十篇。另外校定程颐《伊川易传》。更重要的是,杨时能够根据二程遗训,加以阐发,著书立说,讲学东林,尽力扩大洛学影响。
罗从彦师从杨时,其间远赴洛阳就学程颐,南归后终生从学杨时,“尽得龟山不传之秘”[16]。这样的求学经历使得罗从彦掌握洛学正宗,并能继往开来。康熙皇帝御书匾额“奥学清节”。罗从彦的学术成就在于传承洛学中的伦理道德学说。而李侗则以坚持道统观念和重视“理一分殊”著称。朱熹出自李侗门下,更是直接领悟到洛学正宗真传。
二程洛学和闽学合称程朱理学,从其学术流变来看,经朱熹之手集于大成的闽学是洛学的发展顶峰,代表洛学的最高成就。朱熹理学是对宋代理学思想的融会贯通,对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继承关系更是直接的,他以周敦颐所提倡的无极、太极和二程提出的理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17]理论结构宏大,逻辑缜密,真正称得上传统学术里最完备的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1]罗豪才.弘扬传统文化 推进文化创新,人民政协报,2006-02-27.
[2]《周易·系辞上》.
[3]《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传序》.
[4]《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人民出版社,1979.
[5]《宋史·邢昺传》.
[6]《二程集·遗书卷一八》,中华书局,1981.
[7]《悟真篇·序》.
[8]镡津文集[M],卷三.
[9]《景德传灯录》序.
[10]黄绾:《明道编》卷一.
[11]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12]《中庸义序》《杨龟山集》正谊堂全书本.
[1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上.
[14]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
[15]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16]刘树勋.闽学源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16]张伯行.重刻罗先生集序,罗豫章先生集,卷首.
[17]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部讲师,郑州大学2010级博士生)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