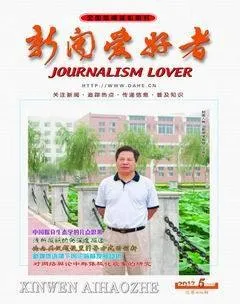媒体在拆迁传播机制中的“双刃剑”角色
【摘要】在现有拆迁传播机制中,拆迁人(开发商)、拆迁管理者(政府)和被拆迁人三者相互博弈,媒体通过舆论监督报道进行平衡,是对现有拆迁传播机制的良好补充。但是,媒体存在的偏向性报道、过于追求眼球而不重事实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传播方向,影响到拆迁问题的妥善解决。媒体可谓拆迁传播机制中的一把“双刃剑”,而拆迁过程中传播问题的妥善解决,有待于媒体加强自身管理,有待于现代拆迁传播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拆迁;媒体;政府;被拆迁人;传播机制
信息传播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群体的根本区别,杜威提出的社会不仅因为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1]。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信息传播机制作为信息传播的形式、方法,以及流程等各个环节的统称,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在当今社会热点的拆迁过程中也毫不例外地存在着这样一种信息传播机制:在拆迁过程中,拆迁传播机制随着拆迁人(开发商)、拆迁管理者(政府)和被拆迁人三者拆迁关系的形成而构筑起来。三者中,提出拆迁的拆迁人和批准拆迁的政府形成实际上的合谋关系,通过三者博弈,将被拆迁人以2∶1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轻易纳入拆迁传播机制中来。其中既当裁判员裁定拆迁纠纷,又当运动员推进拆迁的政府更是整个拆迁传播机制中的明显主导和控制力量,决定着整个机制中不同角色对传播渠道的使用和信息表达的自由度。
一、媒体参与制衡现行拆迁传播机制
在拆迁实际中,除了以上三个主体,媒体和法院作为平衡力量也时常参与其中。法院主要承担着提供司法救济和决定司法强迁这样两个看似矛盾的功能,而媒体的参与,则正是对新闻作为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2]这个定义的演绎。媒体和法院的参与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的参与都是一种选择性的参与,并非既有拆迁传播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多数的拆迁都是在没有打官司也没有媒体报道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的。其次,两者的参与多属于被动参与,即“被邀请”进入原来的拆迁传播机制当中,法院提供司法救济,并享有对拆迁完成的最终强制力:征收条例出台以后,司法强制执行是唯一可行的强制手段,救济与强制看似矛盾,其实正显现出法院在目的不同的角色之间尽可能做到的公平;媒体的参与,则一般由于突发事件的召唤介入整个机制,如2003年被称为“抗暴力拆迁第一案”的翁彪案[3]。
两者的参与也有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在于法院在进入拆迁传播机制以后,其表达的信息拥有非常大的权威,但是其影响力在跨地域和跨领域的情况下会快速式微。而媒体的参与尽管不在实质上改变整个拆迁传播机制中既有信息的表达和流动,但其表达的信息拥有跨地区和跨领域的影响力,甚至能影响到离发生地很远的地区的非拆迁活动。如2007年的“重庆最牛钉子户”[4],引起随后蔓延开来的“南宁最牛钉子户”、“上海最牛钉子户”等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此起彼伏的关于“钉子户”的报道,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新民权运动”风潮。在“新民权运动”中,传统媒体与新兴互联网之间的积极互动,构成了社会动员的最重要力量[5]。
二、媒体在拆迁传播机制内引发“新民权运动”
正是媒体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媒体可以在拆迁传播机制乃至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机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媒体本身拥有发布信息的渠道,其表达权基本不受政府对拆迁传播渠道的控制,相反,因为其报道而曝光的事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对整个拆迁传播机制的控制,因此受到急于表达意愿的被拆迁人的欢迎。因为在实际拆迁过程中,政府在现有拆迁传播渠道中留给被拆迁人的表达意见空间十分有限,大多采取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样一种方式,对时间、空间、形式要求明确,是层层设限的结构化表达,被拆迁人无法自由反馈信息。甚至在要不要成为被拆迁人这个核心问题上,被拆迁人作为主体却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在目前情况下,一旦政府的征地拆迁决定作出,以司法强制执行作为保障力量,可以说就决定了被拆迁人最后会全部搬走的命运。在这种垄断的信息传播体制内求生存,被拆迁人为了突破政府主导的拆迁传播模式,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媒体无疑是提供平台进行充分自由的非结构化表达的最优选择之一。
那么,通过媒体的报道能否真正有效地表达被拆迁人的意见,起到影响整个拆迁传播机制的作用,从而改变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随着媒体日渐深入介入拆迁传播机制,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南京翁彪“抗暴力拆迁第一案”来看,这在2003年时是不可能的,媒体当时只是在事后介入报道,作为对事实和结果的调查陈述,而对于翁彪们遭到拆迁的既成结果没有任何实质改变。而到了2007年,随着“新民权运动”日渐高涨,我们看到媒体不再仅仅作为“事后诸葛亮”,而是在事发过程中及时跟进、充分报道,成功调动起社会舆论,让“重庆最牛钉子户”在社会的关注下得到了满意的补偿。到了2010年,《长春晚报》报道了长春市职工宿舍部分居民在拆迁协议未签订的情况下,被强行拆迁的报道,引起长春市政府高度关注,并于当日发出政令:城市拆迁必须依法进行,绝不允许违法暴力强拆[6]。可见媒体对拆迁传播机制开始构成实质影响,标志是影响到处于机制核心的政府的信息表达。2010年1月和12月,国务院推出两稿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并于2011年1月21日出台新征收条例,正式废止原拆迁条例,正式取消行政强迁,有人将其看做是“新民权运动”的阶段性胜利,将“从拆迁到搬迁”[7]看做社会舆论的胜利和拆迁机制的进步。
可见,随着社会对拆迁的关注越来越多,媒体参与拆迁信息机制也越来越深入,媒体的参与在原有政府管控的拆迁传播机制之外构筑了一个新的平台,主要在于帮助在原机制中难以自由表达的被拆迁人发布信息,并组织社会舆论,最终将影响力渗透入拆迁传播机制中,对政府和拆迁人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规范拆迁行业运作。
从上述分析能看到一个非常乐观的趋势,媒体在社会整个信息传播机制中肩负起舆论监督的任务,帮助社会各方进行平等的表达,并从根本上推进社会民主进程,促进和谐社会的诞生,这也是许多学者希望媒体在化解社会风险中应起到的作用。
三、媒体参与不当引发新的“舆论暴力”
而实际上,辩证地说,媒体一方面打破了政府对拆迁传播机制的垄断,另一方面也干扰了既有机制的正常运作。媒体的参与对拆迁传播机制带来的不仅仅是福音,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如同约翰·密尔谈到的“多数的暴虐”,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8]。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舆论的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一旦处理失当,就会引发新的“舆论暴力”。
首先,媒体参与的偏向性让社会对拆迁行业形成妖魔化印象。米尔斯说过,大众媒体常常侵占了小规模的讨论,并摧毁了人们理智地、从容地相互交换意见的机会[9],这个困局是媒体报道新闻的本质属性带来的,正如博加特说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纽约太阳报》),日常的拆迁新闻并不具备做大新闻的新闻性,而仅仅作为信息列举在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并不会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引起关注。而容易引起关注的,往往是在社会形成共同关注的“暴力拆迁”、“野蛮强迁”等针对拆迁行业存在问题的揭丑报道。塔尔德认为,约束现代交谈的最强大力量是书籍和报纸[10],经过近几年来媒体在拆迁报道中关于暴力拆迁、违法拆迁这类一边倒的报道选择,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拆迁妖魔化”的议程设置效果,舆论往往谈拆色变,社会对拆迁产生偏见,被拆迁人群体中形成受害者想象,不愿采信拆迁信息机制中的所有政府信息,从而阻碍了整个拆迁过程的进行。
其次,媒体舆论监督换来的是公平合理的拆迁补偿吗?媒体构筑的表达平台允许被拆迁人突破现有政府控制的拆迁传播机制来发出声音,并通过社会舆论促使其获得“公平补偿”。但实际上这个“公平”背后往往浮现着那个寻求曝光的被拆迁人嘴角满意的微笑——在媒体报道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拆迁人对媒体所称的公平补偿往往远大于既定口径的“公平”,而政府最后不得不满足其在社会舆论中形成的“公平”补偿标准。在浦东的实际案例中,并不乏见某居民通过寻求媒体曝光而获得了超过原有补偿口径的所谓“公平补偿”,这种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很容易刺激其他居民纷纷模仿,通过媒体曝光要挟政府讨要天价补偿,这是对拆迁行业和社会公平本身的伤害。
再次,部分媒体过于追求受众注意力的刻意歪曲报道。个别媒体在报道中没有弄清事实,随意扩大“拆迁”事故的范围,对拆迁和拆违不加区分,将本不应该获得补偿的拆违事件报道成没有获得“公平”补偿的暴力拆迁,进一步深化在整个社会对于拆迁认识的妖魔化。受此“启发”,个别被拆迁人甚至开始利用媒体炮制关于拆迁的假新闻,如耸人听闻的“河南拆迁官员把孩子扔下楼”事件[11]、“扬州黑帮用上毒气弹拆迁”事件[12]等。这类假新闻在缺乏鉴别的情况下甚至通过媒体转载不断恶化影响。这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的伤害,这些并不是媒体介入报道拆迁问题的初衷。林语堂曾说,让人不安的反倒是新闻从业人员缺乏道德上的自我检查,其危害远甚于新闻检查制度[13],在呼吁新闻自由的今天,更重要的前提是新闻从业人员素质的普遍提升和新闻媒体自身责任感的增强。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拥有一个流畅的信息传播机制,针对目前拆迁传播机制中被拆迁人表达意见的传播渠道过窄的问题,通过媒体来进行舆论监督和报道曝光无疑是对现有拆迁传播机制的良好补充。但是,在媒体参与中,我们也要看到媒体对于解决拆迁问题这类社会风险并非万能。媒体的偏向性报道在舆论中形成上述对拆迁的妖魔化印象很难避免,再加上部分媒体在报道中过于关注眼球而不重事实,立意不是站在社会预警、化解风险的基础上,而是刻意渲染,更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媒体自身加强管理,也在于现有拆迁传播机制的自我完善和修正,让被拆迁人在整个拆迁传播机制中获得相对于政府和拆迁人更多更有效的信息表达权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3:4.
[2]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M].解放日报,1943-09-01.
[3]李明,李剑云.暴力拆迁问题分析——以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理论为研究视角[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1(2).
[4]聚焦重庆最牛钉子户[EB/OL].新浪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z/cqzndzh/.
[5]孙玮.中国“新民权运动”中的媒介“社会动员”——以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媒介报道为例[J].新闻大学,2008(4).
[6]长春市市长崔杰批示 绝不允许违法暴力强迁[EB/OL].新文化网,http://www.xwhb.com/news/system/2010/05/17/010117UAa1om1MluWAJSdfGPm6bJ2izSs1fEzy2oQIG1cQGos=275.shtml.
[7]新拆迁条例终结暴力强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十大看点[EB/OL].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11-01/22/content_2456659.htm?node=21611.
[8]约翰·密尔.论自由[M].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5.
[9]查尔斯·莱特·米尔斯.权力精英[M].王崑,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397.
[10]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M].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241.
[11]一条拆迁假新闻的传播[EB/OL].西西河社区,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80863.
[12]扬州黑帮用上毒气弹拆迁是假新闻[EB/OL].梦溪论坛,http://bbs.my0511.com/viewthread.php?tid=2087839.
[13]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6.
(郑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上海浦东新区房屋拆迁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