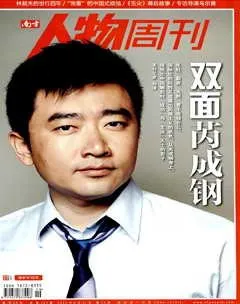文大川 顺流 而下的人生
2012-12-29 00:00:00杨潇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19期

在台上时,文大川扮演着一个不羁的美国小伙,当主持人介绍漂流是一项很酷的运动时,他使劲做出很酷的表情,主持人把话筒交给他后,他指着自己T恤上印着的“自由江河,自在生活”,用很酷的语调说,“是的,我的职业就是这个。”他的中文相当不错,播放漂流幻灯片时自己解说。幻灯片有点凌乱,他说他是故意没整理的,因为“一个人就是一条河流,不可以整理”。
“他现在好些了,”文大川的中国妻子李伟怡说,“以前他很内向,有时候就突然放空了。”文大川是TravisWinn的中文名,1984年出生在盐湖城一个漂流世家,5岁被父母放到河里漂流,七八岁开始自己划,13岁时一个人漂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在这项运动里,独行不是个好习惯,但文大川很喜欢,不是为了冒险,而是喜欢一个人在大自然里的感觉,不用照顾这个招呼那个。上一次他漂流怒江,在江边和一块石头说了半天的话,“探讨怒江的未来”。
但这和他正在干的事情有着巨大的矛盾——他的职业就是在中国带动安全的漂流业的发展,“我该怎么描述我这个非常危险的个人行为呢?”
2003年,父亲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因为非典取消,出资让儿子去看看四川西部那些江河,这是大川第一次走进中国的大川。“那时19岁,对自己的了解还不够清晰,”他在大渡河翻了船,落在一个漩涡里,水下很冷,没法呼吸,最后一次被波浪抛出来时已经开始呛水,“觉得完蛋了”。但他幸运地脱身了,在江面漂了两三公里后被下游的同伴捞了上来。
后来有媒体跟拍他,碰到一些没有十足把握的险滩,他就选择抬船(从岸上走),不为镜头冒险,“万一成功了,会自大,增加自己出事的几率。”他说,漂流越到高水平就越难只凭借技术去完成,“你要靠第六感,这个是根据你与河流的关系培养出来的。我在乎河流,河流也在乎我。”去年12月,他一个人跑到澜沧江漂了五十多公里,经过两个险滩时,一边对自己说走路过去走路过去,一边还是选择了漂流。“但这一次我很清楚客观情况,那两个滩,一个我以前漂过,一个在读水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条通道。”他那时刚从尼泊尔练了10天的内观课程回来,漂流时觉得非常特别,“你的大脑好像分成了几十部分,每一部分都在同时考虑不同的东西。每一个波浪都看得很清楚,很奇怪。”
文大川最喜欢的作家是爱德华·艾比(EdwardAbbey),自比沙漠仙人掌的艾比写过一本著名的《有意破坏帮》,讲述一群年轻人用有限度暴力阻止生态破坏的故事。接受采访时,大川掏出一张纸认真地念起艾比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为大地而战是不够的,享受大地才更重要,趁你还走得动,趁大地还在。”
从2003年起,文大川就开始“漂在中国的江湖上”。在西藏阿里的狮泉河,看着成群野马在岸边奔跑,而神山冈仁波钦就在远方伫立;在四川甘孜的雅砻江,第一大滩就连人带船翻进水里,“在水里的几分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安静,像在母亲的怀抱里……”他来大城市有时也不忘带一艘皮划艇。上次在北大做完讲座,他想跑到未名湖里演示静水漂流,学校保卫处没同意。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金沙江,从下虎跳的丽江大具乡往下两百多公里,可能是中国最适合大众漂流的河段,“这是可以和科罗拉多大峡谷媲美的线路,非常美,非常安全”,而且和几乎无人居住的美国大峡谷相比,金沙江沿岸有16个少数民族,“就像一个文化长廊”。
2006年,文大川和朋友发起成立了一家国际漂流运动组织“LastDescents(最后的漂流)”,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中国西部江河上建坝的数量和速度超出了他的想象——不少河流是首漂,但同时也成了尾漂。金沙江也不例外,那两百多公里最美的河段如今只剩下六十多公里可漂,其余的都成了高峡平湖。有人质疑,你们在漂流上获得的乐趣,可以和建坝发电的重要性相比吗?他回答,漂流只是形式,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应该来看看,你们自己的自由江河有多美。
中外对话中国办公室总编辑刘鉴强参加过一次文大川组织的金沙江漂流,“在大江之上,很容易找到人生的意义,也更能放下那些世俗的东西。你会想,人是需要大自然的,陶渊明的境界我们中国人已经丢失了,但在那儿它又回来了。”参加那次漂流的还有企业家王石,他对刘鉴强说,我是登山的,在山上看到那些河流就是一些线条,可是到了这里,和河流这么亲近,才会感觉到它们是有生命的。
“河流有生命吗?我不知道。”文大川说,“我父亲是地质学家,他觉得河流保护不重要,因为从地球的演变来看,就算人类消亡了河流也还会存在。我很难接受他的观点,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河流。”他说,他的理想是建个集漂流、内观、住宿于一体的“乌托邦”,而过去几年,他试着吸引一些有影响力的“高端”人群参加他的活动,希望通过这些人去影响更多的人,他甚至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也许河流保护的未来不会那么悲观。
“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撒谎,”他开玩笑说,“告诉大家这是最后的河流,也许它们就有救了。”2月份,他又漂了一次金沙江,过一个4级滩(级数越高难度越大,6级为不可漂流)时,“我一直告诉自己,翻船!翻船!因为我想了解karma(业)是什么,如果这是最后一次漂流,那我就下去拥抱一下,和金沙江道个别。”结果,船没翻,“也许它觉得,还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