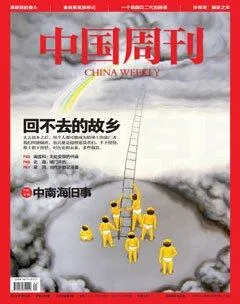梁鸿:当代乡愁记录者
2012-12-29 00:00:00李佳蔚
中国周刊 2012年1期

一直到成年,梁鸿才吃到第一碗家乡美食——河南烩面,“用盐揉面,抹上香油,醒一醒面,熬好的羊骨头汤,放上木耳、海带和粉条,早些年再撒上一些芝麻叶子、萝卜樱子做成的干菜,一大碗,热气腾腾,很滋补,真香。”
“那个时候,整个梁庄的人几乎都没有条件去吃。”她轻叹一声。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去年,她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自己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取名为《中国在梁庄》。
著名作家阎连科说,从《中国在梁庄》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撼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
“梁庄是我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乡愁,也是你的乡愁,是每个中国人化不开的心结。”梁鸿说。现在,她又从“梁庄”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里乡愁的模样。
乡愁记录者
与烩面的香味一样,令梁鸿印象深刻的还有饥饿。家里经常闹春荒,吃不饱,饿的时候,梁鸿就坐在墙角晒太阳,一天也就过去了。
饥饿岁月里的成长容易被忽视。某一天,上学的路上,梁鸿碰到了父亲。父亲打量着她,用一种吃惊的口气,说,呀,你都长这么大了!梁鸿回忆说,那好像是某一个清晨,在庄稼地里,看到庄稼一夜之间拔节蹿高时的惊喜。
每天,上学的时候,梁鸿说一声,妈,我走了。躺在炕上的母亲,因为中风不能说话,只发出一声“啊”的哭声,算是回应。
“它是乡愁里长长的阴影,不是黑暗的,是掺杂了哀伤、某种温柔又凄凉的记忆,至今,我还是没有走出,即便我已离开梁庄这么多年。”梁鸿说。
梁鸿彻底离开梁庄是在1994年,那一年,她20岁,考上了河南当地一所高校。
实际上,自从彻底离开梁庄后,梁鸿每年回不了几次家,更多的时候,留在故乡的姐妹们替她到母亲的坟前磕几个头。
可是每次回梁庄,梁鸿都会感觉村庄在发生变化。
梁鸿记得,原来梁庄的坑塘里长满了荷花。每到夏天,只需一场大雨,青绿的荷叶便铺满整个坑塘,到了盛夏,白色或者粉红色的荷花,露出水来,挺立着,随风摇曳。有时,她和耍伴们下河摸螺壳,抓泥鳅,带回家炒着吃。待莲子成熟后,她和耍伴们就偷偷去采莲子。
“一口咬进嘴里,那个清香。”梁鸿笑出声来。
可如今,滋养了莲子的水塘已经成了死水,青青的荷叶再也长不出来,一层层的绿藻漂了起来,像一块黑绿色的脏抹布盖在水面上,上面还有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种生活垃圾。
她曾经读书的梁庄小学,也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被改成了养猪场。校门口的标语,已经从“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原来升国旗的地方也只剩下了水泥墩。看门的老乡告诉梁鸿,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当废品卖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
“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轨迹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习惯了符号化处理,习惯了数字化衡量,哪怕是感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鸿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甚至是羞耻之心。
她说,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论文成为了学术生产,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五个月。每天,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和村庄里的人吃饭聊天,“用目光和脚步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
2010年上半年,梁鸿在北京的书斋里,开始写作《中国在梁庄》。中间一段时间里,梁鸿觉得自己无法再写下去了。她不时地问自己,“这个故事背后的痛苦有谁能够关心?乡村一定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湮没和牺牲,沦为一个个城市赝品吗?乡土中国在慢慢终结吗?”
刚开始,梁鸿用的是日记体,记录每天和谁谈话,听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写了十几万字后,她发觉日记体不足以呈现梁庄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后来,梁鸿把日记体换成纯抒情体,可还是不行,最后,她选择了“观察、素描、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
在梁鸿看来,用什么样的文本来处理,意味着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呈现。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乡愁记录者。”梁鸿说,“他们的自述很重要,我们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一直在遮蔽这种声音,把自己当做这种声音的代言人,其实他们的情感和痛苦超出你的把握。”
“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梁鸿的记忆中,1991年,也就是她从穰县师范学校毕业的那一年,邻居家出去打工的三兄弟回来了,每人穿着一件黄大衣,骑着崭新的自行车。
三兄弟是1989年出去的,他们成为了最早从梁庄走向城市的人,在梁鸿和其他庄里人眼里,“像一个神话一样”。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
她的少女时期最好的朋友菊秀,和哥哥离开梁庄,到河北做砖厂,在火车站帮着找工人。菊秀告诉梁鸿,自己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自己追求的美好生活,到最后怎么变成了这番样子?
在梁鸿的记忆里,菊秀骨子里是个特别浪漫的人,从小喜欢文学。在接到穰县师范学校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她和菊秀在村后的河边跑啊,跳啊,唱啊,疯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俩在当时“雪白的沙滩”上,恭敬地写了一句话:“菊秀和海青是好朋友。”
“一个那么崇尚高雅生活的女孩子,最后完全被生活压倒了。”每次想到菊秀说这番话的表情,梁鸿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在1991年来到北京。有一次,梁毅志想写封信回老家,他问一个老人邮局在哪里。对方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梁毅志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
可是到北京后第二天,梁毅志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长得洋气的柱子16岁到青岛一家首饰厂打工。干了十多年,柱子生病回梁庄了。他经常吐血,住了两个多月的院,还是没有止住。到后来,只要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柱子的兄弟姐妹凑钱给他治疗,可是没挨到柱子死,他们又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了。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得很。”父亲告诉梁鸿,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一连串的问号在梁鸿的脑海里浮现:他们在城市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怎么想梁庄?他们的精神与城市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交叉?
她打电话给家里人,把梁庄人打工的城市在地图上罗列出来:广州,东莞,青岛,西安,北京,内蒙古,新疆,西藏等。
从2010年年底开始,梁鸿就一个人去那些标注在地图上的城市,走进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讲梁庄人在城市里的日子。
“梁庄在中国。如果能把他们与城市的关系、生活状态写出来,能够展现当代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而在眼下的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每一个人的乡愁。”她说。
“乡愁就是一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刚从老家回来的梁弘志。1988年,梁弘志离开梁庄,来到西安卖菜,至今已有23年。
梁鸿到的时候,梁弘志刚从梁庄回来。他回梁庄治腿了,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起初,梁弘志去了西安一家大医院,医院说先交一万块钱住院费,梁弘志听了,二话没说,坐了十多个小时的汽车,就回了老家穰县的骨科医院,板子一夹,纱布一裹,花了150块钱,就把腿治了。
其实,梁弘志从县里回了梁庄,住了20多天,吃饭,喝酒,打牌,花的钱都超过一万了。梁鸿问他何苦这么折腾,梁弘志嘿嘿一乐,我回家了啊,开心啊,花得值啊!
在梁鸿一年多的访谈调查里,这不是孤例。有老乡得了痔疮,就从青岛赶回梁庄,赶回穰县,算上路费和回到梁庄的人情世故,花费要远超过在城市里的治疗费。
“可他们都选择了回到梁庄。在城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城市给他的异己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乡愁。回穰县,回家,花的钱多,他心里觉得踏实。”梁鸿说。
梁弘志在西安的家,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残垣断壁中。这是一片拆迁区,本来说要拆,可是后来又不拆了。从来到西安,梁弘志一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经常断电。
以梁弘志的经济实力,可以在西安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梁鸿问他,为什么不买一套公寓房?梁弘志眉毛一挑,直愣愣地说,“打死也不会在西安,要回梁庄!”
梁弘志已经在梁庄盖好了房子。去年,梁弘志的儿子结婚,他们回梁庄住了一段时间。“梁庄美啊,呆着就是舒服。”
对于西安的感觉,梁弘志则归结为朴素的一句话:“人家不要咱。”“到了菜市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指着咱的鼻子骂。”
“他们没有被城市吸纳,”指着自己拍的梁弘志家的照片,梁鸿说,“最关键的是,他们也没有被纳入到一个制度里面,孤独的感觉一直在他们心里,他们内心里遵从了这种安排,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
梁鸿的西安之行中,还有这么一张照片:一条小巷子里,一个小女孩独自坐着,头顶上仿佛只有一线的蓝天,蓝天是那么窄,那么高,似乎永远触碰不到。
照片里的小女孩,正是梁弘志的小侄女。
梁鸿还有一个堂哥。有一段时间,堂哥发觉自己特别能吃,可是越吃越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得了糖尿病。堂哥听了,整天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堂嫂说,要不然,你回梁庄住几天吧。堂哥开了些药,就回了梁庄,“感觉病也好了一半,也没有再瘦,它没有要我的命,高兴坏了。”
“这就是乡愁,只不过他们没有用一个词汇来总结,去表达,”梁鸿说,“乡愁在他们那里就是——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乡关何处
在东莞虎门镇,梁鸿见到了老乡梁东来(化名)。1997年,梁东来高中毕业,从梁庄来到东莞。十多年的打拼后,他从一名打工仔做到了一个小老板。
梁东来做的是童装生意,一个小作坊,有十多个工人。最好的时候,梁东来手里有差不多一百万,而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他的钱差不多赔光了,勉强维持。“撑不起,就从小老板再做回打工仔呗。”
可当梁鸿问他“将来去哪里时”,梁东来没有了这份淡然。他不想在东莞买房子,也不是很想回梁庄,“回去没有希望”,况且老家的房子也已经塌了,“将来赚了钱,可能会去郑州买房子吧,可这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
梁鸿清楚地记得,在那间“推开一扇门,就是一个工厂”的作坊里,梁东来说这番话时的表情,“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乡关何处?在一年多的调查采访里,这个问题不时地冲击着梁鸿的心。直到有一天,她似乎找到了模糊的答案。
她与一位在北京买了房的老乡聊天。原本是波澜不惊的家长里短,可老乡突然蹦出一句:“我想回咱们镇上买一个房子,和原来的老邻居住在一起,半夜生病了可以有一个门儿去敲,死了之后有人抬棺材。”
前两天,梁鸿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做讲座。讲到土葬政策,梁鸿说,土葬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独特的情感传递,是不是应该用更包容的方式来理解和执行土葬政策?
话音刚落,台下一个老太太就站起来,神情激动地说,我有一个办法,还是用棺材,埋上土,一个棺材上面种一棵树,在树上挂一个小牌牌,上面写着他是谁,从哪里来,这辈子做了什么,到时候,放眼一望是一片绿色的树林。
“多好的一个画面!树根紧紧包裹着棺材,像是回到了大地的子宫,母亲的子宫,那么的有安全感,”梁鸿不禁唏嘘,“那是回归大地的渴望,落叶归根的乡愁。”
而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却告诉梁鸿,在他们老家,坟头上的树是不能砍的,谁砍了,会遭天谴,会被全村的人咒,“可春节我回去看,村边到处是木材加工厂,坟头上的树都砍完了。”
在西安,梁鸿遇到了一场“城市里的葬礼”:四个人抬着一张小桌子,一张老太太的照片放在上面。桌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披麻戴孝的人,最前头应该是老太太的女儿,哭得伤心,可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尴尬,想哭又哭不出来,因为周围围了一圈人,在对他们指指点点。
“整个场景显得不伦不类。”梁鸿回忆说。后来,她知道了,这是一群农村人在按照老家的规矩,进行一场葬礼。
“他们在城市里,依然要坚守乡村里的规矩,”梁鸿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勇气,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心里面维护着故乡的习惯。”
“如何回到故乡”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故乡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乡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
也有人写评论说:“《中国在梁庄》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它让我们感同身受、辗转难眠,《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
去年上半年,梁鸿接到了许多封读者来信,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部队军官,城市农民工,大学老师等。除了表达对于《中国在梁庄》的喜爱,读者的来信都写了自己的故乡和乡愁。
“《中国在梁庄》击中了每个人心中的痛,这种痛是一种隐痛,平时我们是把它忽略掉的,”梁鸿起身把一摞读者来信放好,说,“城市里的我们都很奔忙,不断被挟裹着往前走,遗忘掉我们的故乡,但是它一直在,我们经常看一些零散的新闻,有时会心有所动,可是都忽略过去了,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打开了城市里的人尘封已久的乡愁。”
顿了一下,梁鸿做了一比喻:“就像在心里开了一道小缝儿,阳光‘唰’的一下,射进来,那种问题感,一种蛰伏已久的痛感,让你知道,其实一直在自己心里放着。”
2011年年初,《中国在梁庄》获评某个门户网站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梁鸿去领奖,登台发言那一刻,她说,梁庄那些熟悉的亲人、乡亲和风景,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她眼睛里闪着泪光,哽咽了:“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
最近,梁鸿有一个设想:回梁庄盖一个房子,办一个村图书馆,或者给梁庄的孩子上上课,放放电影。她把想法告诉父亲,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连说了几个好,主动请缨做管理员。现在,父亲几乎每天给梁鸿打电话,催她赶紧回梁庄找地方。
5月份,梁鸿接到了一个邀请:给参加“百村调研”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做一场讲座。
“本来不想去,”可她转念一想,“讲座可能会影响某一个官员的心灵,在未来,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与某一个‘梁庄’相遇,希望能够让他们多点对‘梁庄’的爱,他们是能够改变千万个‘梁庄’命运的人。”
梁鸿如约出现。那一天,面对人手一本《中国在梁庄》的600多名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她讲座的题目叫做——《我们如何回到故乡》。
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
Q=《中国周刊》
A =梁鸿
A:是的,乡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种感觉更多的是出于对乡村现状的不满,看到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凋落,没有秩序,而不单单是家里的老屋塌了,记忆中的河流再也没有鱼。现在的中国太快了,整个社会病态的发展,在乡村有一种显性的体现。这些一下子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强烈的感觉,自己的故乡沦陷了。
Q:我们今天的“乡愁”,更多的是什么呢?
A:乡愁已经不再是李白的乡愁,也不再是唐诗宋词的乡愁,不再是狭义的乡愁,现在的乡愁已经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乡愁,中国的乡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都市里,以都市文明或者工业文明去看农业文明的乡愁,与农业文明时代是不一样的。
在农业文明,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没有变的,而现在的乡愁,是在高速现代化发展下,人的本源被急剧地抛弃的,人与自然没有关系了,与四季没有关系了,被孤零零地悬在都市的钢筋水泥里,这时候的乡愁是怀念人的自然属性,想念的是与自然、与大江大河的一种相互偎依的感觉。
Q:乡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A:乡愁是有质的变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愁,更多的是寻找一种传统。
过去,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愁是对于农业文明的一种想念,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精神方式,农业文明下的状态与四时相合,春种秋收,晨起昏睡。
现在,“乡愁”的背后,是隐蔽的多层制度与歧视:城市不能给他很好的安定感,归属感,他们现在的状态是在一种常年被隔离的状态下,看起来很像融入了城市,实际上是被隔离,这不是自主选择的,而是被所谓时代的潮流裹挟。现在,到了我们该反思的时刻,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再不思辨,恐怕以后就没有什么好思辨的了。
乡愁,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如何保持自性的问题。
Q:如何保持自性?
A:现在我们的文明,与四时、季节、植物是没有关系的,它貌似是超越一切的。人无所不能啊,无所畏惧了。所以,康德说过,望星空,只有两种事物让我们敬畏,这就是浩瀚无际的星空与我们内心的道德,可是星空和道德似乎消失已久了。现在没有这种敬畏感了,人太狂妄了。
在这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乡愁的,它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在每个人的心里蔓延。
你回到家乡为什么会感到特别舒适,因为你觉得自然界还在,你突然找到一种生存感,一种活着的感觉。当代的乡愁,是有一种巨大的批评在里面,一种传统的回望,只是我们没有去清晰地梳理它。
Q:现在,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
A:是的,现在的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当你有一天,你回望,突然发现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传统反映在生活的丝丝缕缕中,你的根没有了,人生活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你连回头的地方都没有了。
现在的我们,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物质、金钱与权力,这个社会怨气冲天,你去烦躁,去抱怨,去不择手段,觉得社会亏欠你太多。在滚滚洪流中,需要一点定力,稍微拉回一些自己,这需要很大的反省能力。
Q:如何找回我们的故乡?
A:找回故乡,广义上,实际上是找回曾经支撑维系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最朴素的道德方式。
找回我们的故乡,需要我们重新思索自己与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的关系。从自己的故乡出发,思索自己的家人、邻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需求,然后再来思索这个时代的发展。
人类社会肯定不止趋同性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共性高速一体化的发展下,怎么样重新找到自我,就是怎么样重新找到自己的故乡,这既是自己的自我,也是民族的自我。现在,我们的国家需要找回它,否则有一天,如果我们没有一点点寻找的欲望和痕迹,我们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了别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