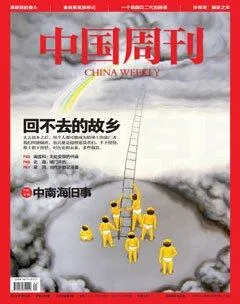弹起吉他 忘了故乡
2012-12-29 00:00:00杨洋
中国周刊 2012年1期

如果那一晚,沙建微没有在打烊后弹唱自创歌词的中文版《加州旅馆》,如果这段视频没有被朋友上传到网上,不会有什么人在意,这个漂在北京的烧烤店厨子,还有着一个关于音乐的梦想。
在视频里,扎着小辫的沙建微敞着怀,穿着半旧的白色厨师服,拨弄着吉他。用熟悉的《加州旅馆》的曲调,唱起自创的伤感的中文歌词:“来到这城市两年,却没有归宿感;已回不去我的故乡,只为了梦想……”
从2011年9月上网至今,这段视频的点击次数,已经超过了500万。沙建微的歌声戳痛了无数异乡人“漂泊”不定的心,厨师哥一夜之间,火了。
一
沙建微现在住在烧烤店老板的家里,顶层一间不到10平米的阁楼,是他的栖身之地。顺着颤巍巍的楼梯走上阁楼,斜屋顶、一扇天窗,没有床,只有一张床垫。四周散落着一些杂物,还有两双鞋。阁楼上没有暖气。在玻璃茶几上,放着昨夜吃剩的火锅,红油凝固在锅里,旁边立着几个空酒瓶。
因为天气冷,烧烤店已经停业。但沙建微依然保持着在烧烤店做厨师时的作息时间,每天中午十二点起床,夜里两三点入眠。
2011年的秋天开始,为了听他的歌,陆续有人特意跑到通州的小路邑海鲜烧烤广场捧场。台子搭在广场的中央,四周围是海鲜市场、烧烤大排档,超市和杂货小铺。沙建微拥着吉他,他的听众,是菜场的小贩和拎着蔬菜水果的大爷大妈。
他会唱汪峰、许巍、齐秦的歌,但大家点得最多的还是他作词的中文版《加州旅馆》。新老主顾们点歌、鼓掌、送啤酒,是沙建微在北京少有的快乐时光。
不唱歌的时候,沙建微穿着厨师服串串、烤串,赚着每月1300元的工资。他期盼周五、周六、周日的到来。每周的那三天,他可以穿着体面,拥着吉他在小舞台上表演。每天有100元的收入。
2009年初,为了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年仅19岁的沙建微来到北京,开始了在天桥、广场、地下通道唱歌的生活。
作为流浪歌手,沙建微不得不长期面对身无分文的窘境。他背着吉他行走于各个广场和地下通道,但是他发现,当个流浪歌手并不是他想象得那样洒脱。
“经常是刚拿琴走进地下通道,就被管理人员轰走,一天下来,别说挣钱了,甚至连一个能放下琴唱首歌的地方都没有。”他感叹道,“理想在现实面前会越变越小。”
在地下通道里,人们来去匆匆,很少有人肯为沙建微的歌声停留。沙建微感到深深的孤独。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认识的流浪歌手也只是短暂一聚,随后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
为了改变现状,沙建微也曾经背着吉他到后海的酒吧求职。刚推开门,酒吧的老板就会很职业地直接摆摆手:“不需要。”去后海寻找机会的歌手太多了。沙建微后来听说,几乎每天,酒吧的老板们都会遇到三十个左右的求职歌手。
2010年,沙建微已经在北京当了两年的流浪歌手。夜里睡不着,他一个人在城市里游荡。经常,沙建微回到租住的地下室,戴着耳塞听歌,反反复复地听,凌晨三点才能入眠。
这时候,他开始想家了。《加州旅馆》的中文歌词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他将歌词深藏在心里,像是秘密,又像是对自己的宣言,不曾唱与他人听。
2011年的夏天,沙建微被介绍到海鲜烧烤广场当驻唱。总算,他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周一至周四,他和那些油腻的烤串和炭火打交道,周五至周日驻唱。烤串的时候,也会有人要听歌,他就穿着厨师服给大家唱。
这首中文版《加州旅馆》,沙建微一直没敢唱。他怕自己作词的外国歌曲,顾客不接受。
2011年9月,烧烤店的一位厨师辞职,在送别宴上,沙建微唱出了这首深埋心底的“北漂”心声。那一晚,琴弦拨动,杯盏几巡。在沙建微沙哑的歌声中,梦想和家乡忽明忽暗、忽远忽近。
虽然有很多留在北京的理由,但让沙建微留下的最主要原因却是,他不想回家:“我就是不想再像我的祖爷爷、爷爷、父亲和我的同乡们那样再生活一辈子。”
二
沙建微站在故乡的空地上,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是绵延不断的青山。
“只有一条路通向远方。但是你看不到城市的踪迹。”他说。去到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只有私人揽活儿的,单程10元。
对少年时的沙建微来说,来回20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何况去市里要六个多小时的车程。初中的时候,沙建微还在听任贤齐的盒带,把喜欢的歌词都抄到日记本上,“那时候,别的地方早听CD了,我们那里的90后还在重复着人家70、80年代做的事情。”
云南省西南部贴近缅甸的永德县,是沙建微的故乡。永德县,隶属临沧市。沙建微并不知道临沧的名字是因为濒临澜沧江而得名。得知临沧号称“滇红”之乡,他也表现得非常惊讶。旅行者向往的永德大雪山他仅是听说,从未攀爬过。
这个云南小伙子只知道家乡很穷,对家里一年收入多少,沙建微也只能抱歉地笑笑:“我真的不知道。”
村里人都是布朗族,却不懂布朗族的语言和文字,日常交流说的是傣族中汉傣的语言。其余方面,基本汉化了。
有时候,回忆起故乡,他像打开了一道回家的闸门,思绪在那些家乡快乐的记忆里兜兜转转,不肯回来。
在沙建微的记忆中,故乡是连绵不绝的山和一年四季的绿色。天空蓝得透明,少有的几朵云彩会白得炫目。奶奶和母亲会在中午时分背上大竹筐上山采野生菌。两三个小时就回来,背了满满的两大筐,而且全是能吃又美味的蘑菇。
沙建微也会跟小伙伴们上山采菌。“小孩儿就是为了玩儿嘛,也不认得哪些能吃。”沙建微的眼神闪着光亮,嘴里却一口京腔。已经听不出一点点乡音,“现在当地人都吃不到那些野生菌了。污染,山里没有了。”
沙建微的家,住在祖爷爷留下的老宅里。白墙、黑瓦,小飞檐,瓦当上镶嵌着图案。院子里种着洋瓜、青瓜等藤蔓植物,池塘里是白嫩的莲藕,田地里有水稻、玉米和甘蔗,山上还有茶树和木瓜。
父辈们将大片的烟叶撕掉叶脉,搓成一个个小卷,用菜刀切成细细的烟丝,咕嘟咕嘟地抽着水烟。每天只要下田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到邻居家聊天、打牌、喝喝茶。四季更替、播种、收获。父亲只想着种田的事儿,甚至连种田也无需操心太多,只要按照时令规律来做就行了。
“村里人身体都好,也不像城里人还想着生病没钱看病怎么办。”村里有个老中医,基本上看病都是找他。沙建微生病,父亲会上山采草药给他吃。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认得一些草药,哪些治感冒,哪些治肚子痛。
过年的时候,家家都杀猪。会留下两个猪后腿用很多盐腌制成火腿。做菜的时候要先洗干净,放在水里煮,煮熟了再切成片,放在锅里炒,这样才不会太咸。用豆腐、猪血、鲜肉灌制的香肠、辣乳腐、牛干巴,这些都是沙建微爱吃的。
沙建微虽然想念家乡的美食,母亲打电话问他需要什么吃的,他却总是一口回绝。他尽量避免和家乡产生什么“过分亲密的联系”。
“歌词里我写过,已回不去我的故乡。安逸的生活背后是无聊。”沙建微的村里,家家户户都认识。除了谁家娶了外地的新娘子能让小山村热闹上几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沙建微只能是打牌、喝茶。到田里、河边、山上乱逛。
对故乡,沙建微有着既思念又害怕的情感。他常想起在临沧市读技校时的一次回家。一路上一直盼着,快到家的时候,看到熟悉的景色又开始后悔。家里安逸得让人失去斗志,他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三
北京满足了沙建微对于城市的一切想象。
此前,在沙建微和他的家乡人看来,北京太神秘了,“我家四世同堂,从我的祖爷爷开始,就想来北京看看。在我们的眼里,北京就像是神。”
沙建微对来北京的那个日子印象深刻。2009年2月19日。那天的北京下了雪。他第一次知道河水结冰、雪花落下是什么样子。
不过,也就是在那天,在北京火车站附近,沙建微见到了一段古城墙。举目四望,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古老与现代的结合。”在他的自我感觉里,他一下子就“读懂了这座城市”。
在这种神奇力量的驱使下,很多城市的不如意也就微不足道了。只要能生活在这里,看看那些光鲜的,“原本只有在电视里能看到的大城市生活。”沙建微依然很知足。就连北京混浊的空气,也成了他生活在城市的存在感。
“城市的空气就该是这样的。”他说。
不过,在老乡和父母的眼中,沙建微是个不孝子。自从17岁离开家,沙建微从来没有给家里邮寄过一分钱。
沙建微所在的村子不大,只有二百多人,大部分人家都姓沙,互相都能攀上亲戚。十五六岁的年轻人都会跟随着亲戚朋友外出打工。这些年轻人,每个月都会给家里邮寄三四百元。就连比沙建微还要小两岁的弟弟,也每月给家里邮寄400元。
但沙建微不认同给家里邮钱的做法:“每个月800元的工资,邮寄给家里一半,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大城市是怎么生活的。像我在饭店工作下班晚,每天晚上吃个宵夜,一个月也得三四百吧。”
离开家的第一年,沙建微跟表哥在深圳一家电子元件厂工作。这儿和沙建微对城市的想象完全不同。一片片的厂房、蚂蚁一样的人群,没有高过六层的厂房,单调的流水线上的工作,沙建微甚至不认识工厂之外的街道。
十个月后,沙建微离开深圳,去了广州,找了一份在饭店传菜的工作。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攒钱买了把三百多块钱的吉他,自学乐谱,后来干脆去当了流浪歌手。
在最初的一年里,父母会打电话要沙建微邮钱回家,后来渐渐的,父母不再提邮钱回家的事,但沙建微“不孝子”的名声渐渐在老乡们中间传开了。
到现在,沙建微的父母也没搞清楚,沙建微怎么学会了弹吉他,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听他唱歌,怎么他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据当初看到节目跑来报信的邻居说,沙建微是找了个女朋友,被人甩了,他写了首歌,去电视台唱了。
母亲很担心,打来电话。沙建微莫名其妙又无可奈何。他很少跟父母沟通。甚至不愿意接父亲的电话。来到北京后,沙建微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自从在网上火爆后,沙建微接到一些商演的机会。他还签了一家经纪公司,生活似乎有了方向。
他对现在的生活似乎很满意。采访的间隙,在这个只能看见星斗的小阁楼里,沙建微又一次把头转向窗外,侧耳倾听。
“多好啊,川流不息的车声,灰蒙蒙的天。城市就该是这样的啊。”他感叹道。
“可城市里少有绿色,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我问。
“那要是我喜欢钢筋水泥呢?”沙建微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