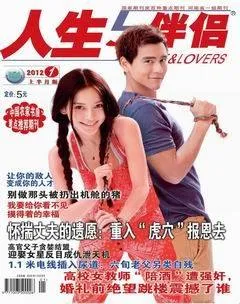女外交家接受外媒采访前的六轮痛苦演练
2011年8月17日,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苏珊娜·科博勒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进行了采访,涉及内容很广泛。在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傅莹女士举止雅致、专业,思想锐利,始终以东方人固有的骄傲口吻同西方人平等交流。她的自信和雄辩,让我明显有一种‘中国赢了’的感觉。”苏珊娜感叹道。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部第二位女性副部长的傅莹,2011年9月17日应邀与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进行交流,谈及自己此次采访前的准备时说:“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较量,必须进行大量痛苦的练习。我先后进行过6轮演练,并一度感到非常挫败,但最终还是赢了。”
第一次演练,傅莹让外交部欧洲司的20多个年轻人进行角色互换,分别扮演记者和被采访者。她在一旁发现,“扮演记者的个个比《明镜》周刊的记者都‘狠毒’,一小时提出30个问题,中间还常被打断,就是要压迫被采访者做出第一反应。而当提问者扮演被采访者时,却一个个败下阵来”。
第二次演练,傅莹亲自上阵接受同事的采访,没有几个回合,她也败下阵来。她很沮丧,也很苦恼,忍不住埋怨下属:“别总是把问题设计得那么复杂,别人根本不会那么问的。”
虽然在第三次用英文练习时,傅莹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提问者准备的问题更多,结果“自己非常混乱、挫败,完全被提问者牵着走,觉得很痛苦”。
三次演练的失败,让傅莹找出一个窍门:必须掌握主动权,包括如何把握节奏、如何抓住听众注意力,以及如何利用尖锐问题表达自己立场等,“得有个筐子把众多问题装起来,不能被别人牵着走”。虽然如此,在接下来的3轮演练中,她仍“饱受同事的刁难,他们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好在每次她都准备了10倍于对方提的问题,六轮演练结束时已变得从容自信,完全掌控了局面。
坐在《明镜》周刊记者苏珊娜面前时,此前演练收到了成效。傅莹先发制人:“记者的诉求就是要难倒被采访对象,这是你的职业。我接受采访是有风险的,但要表达我的观点,就得冒这个险。”
傅莹的直白表露,让苏珊娜一时无语,讪笑道:“您说得对,说得对。”
其时,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海试,苏珊娜第一个问题便提出:“中国为什么需要把自己武装到如此地步?你们难道没有比增加军费预算更重要的花钱地方吗?”这是傅莹意料之中的,她不卑不亢:“中国第一艘航母海试确实令人振奋,这是中国人民的夙愿,也是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我看来,你们对中国军力的担心,是受到陈旧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立思维的影响。你们对美国、法国等盟友拥有航母就感到放心,而中国拥有一艘航母你们就感到担心了?这是什么逻辑?”
傅莹的强硬口气,虽让苏珊娜猝不及防,却仍不失逼人之气:“最近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被捕在德国被视为挑衅行为,而且他被捕就发生在德国外长韦斯特维勒访华并在北京出席德国启蒙艺术展之后不久,这是不是有意而为?”傅莹反击道:“你们确实太看重自己了。中国为什么要将自己在一个内部事务上的处理与某位欧洲国家外长访华联系在一起呢?我看不到二者之间有任何关联。你所提及的是一起进入司法调查的案件。我对此不感兴趣。”
苏珊娜不甘心服输:“您对中国被看做新兴经济超级大国的感觉如何?这是否也让你们感到了压力?”
傅莹微笑道:“你过奖了。但压力谈不上。我们不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你在中国身上不会看到美国,也不会看到前苏联。你会看到一个人口众多、有文化底蕴的大国,一个更满足、更幸福,有自己的目标和对世界友好的国家。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认为自己垄断了一切真理、一切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那当你们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价值观和文化的多样性时就会感到不舒服。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要再居高临下,也不要试图包办代替,请与我们平等对话,学习去尊重其他人,而不是以冷战方式去臆造一个新对手,大家一起合作才有出路。”
苏珊娜又接连提出了15个尖锐问题,都被傅莹一一自如应对。采访结束后,苏珊娜由衷地对傅莹说:“您是最能清晰传递中国声音的使者之一,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职业外交家,应对媒体坚毅自信,表达不满时反应迅速。我敬佩您的直率,很高兴结识您。”
傅莹对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说:“如果没有采访前六轮痛苦演练,就不会有后来的从容应对。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和媒体交锋时,观众才是最终的决定者。即使你把对方狠狠批一顿,占了上风也没用,因为最终要看观众是否站在你这边,赞同你的说法。一句话,只有以理服人才是真本事。”
编辑 / 尤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