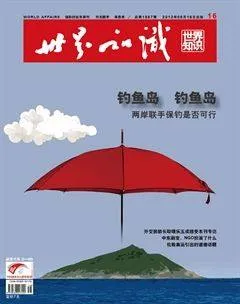它们一直在行动:中东剧变中的NGOO
2012-12-29 00:00:00
世界知识 2012年16期


在许多人眼中,非政府组织(NGO)或许没有官方机构那么强大和富有,然而,有时候这些“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却比官方机构更能有效地推动社会政治变革。在这次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剧变中,我们便不难看到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重重魅影。
就在今年年初,埃及检方突击搜查了17家埃及境内的非政府组织办公室,宣布起诉43名涉案人员,其中包括19名美国人,其余来自埃及、德国、挪威、塞尔维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遭到搜查的美国组织包括麦凯恩任董事会主席的国际共和研究所、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任董事会主席的全国民主研究所、“自由之家”和国际记者中心。埃及方面表示,受调查的非政府组织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在埃及境内从事纯粹政治活动,非法从国外获得资金援助,其工作人员持旅游签证而非工作许可,并且未能遵守埃及税务法等相关法律。
绕过执政当局公开资助政治活动
相对而言,中东地区的公民社会并不发达,这里本来也并非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渗透重点。然而,9.11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由于9.11事件中的劫机嫌犯大多来自中东地区,在痛定思痛之后,美欧等西方国家开始把自身安全与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改造联系在一起。2003年,小布什总统在美国民主捐赠基金会(NED)成立20周年的讲话中公开表示:“60年来,西方国家迁就和适应中东缺乏民主的做法并未带来安全。因为从长远来说,追求稳定并不能以自由为代价。只要中东依然缺乏民主,它就仍然是一个输出落后、怨愤和暴力的地区。”为此,在“中东伙伴倡议”计划和“大中东计划”名义下,美国国会每年拨款数十亿美元,在中东设立了名目繁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援助项目。2009年,仅美国一个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援助预算就超过了从1991年到2001年的总额。其中大量资金通过国务院、中情局、国际开发署和民主捐赠基金会等途径进入了非政府组织的口袋。
起初,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量西方援助都必须经过当地政府才能到达当地非政府组织手中。不过在2004年,根据美国参议员山姆•布朗克提议,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向国务院拨出专款用于为埃及提供民主、人权和治理援助活动,并“向开展此类援助的公民组织提供帮助,而且此类援助不必事先得到埃及政府的批准”。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开始绕过执政当局,公开资助各类非政府组织在埃及从事政治活动。此令一出,大量西方非政府组织如潮水般涌入埃及和其他中东国家,以帮助当地建设“公民社会”的名义,在人权、劳工、妇女以及经济与政治改革等领域开始进行全方位渗透。在外部资金和技术援助下,一些原本受到限制或发展缓慢的当地非政府组织也快速发展起来。
从事的是20前中情局的秘密工作
从名义上说,在中东地区活动的很多公民组织是非官方的,与西方国家政府毫无瓜葛,但它们在事实上却与属国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今年年初被埃及执政当局搜查的几家非政府组织,虽然大多自诩为“非官方”组织,但国际共和研究所、全国民主研究所、“自由之家”等不仅从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等联邦机构获得大量资助,“自由之家”还是美国对阿拉伯国家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的主要渠道。在2008年“青年运动联盟”纽约峰会上,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和其他国务院政策官员亲自到场助威,而谷歌、脸谱和MTV等西方大公司则为这次活动提供了主要赞助。参加此次会议的埃及青年代表中就包括了后来创建“四六青年运动”的默罕默德•阿德尔等人。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以后,西方国家大幅增加了对活跃于中东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力度。埃及国际合作部长阿布•纳贾表示:2011年3~6月,埃及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大约1.75亿美元外来援助,是之前四年总额的三倍。
除了直接提供经济资助,西方国家还通过各种途径为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技术援助。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在2011年表示,美国政府在过去两年内投资了大约5000多万美元发展新网络技术,以“帮助中东地区的社会活动者保护自己,免于被当局抓捕或迫害”。这些技术包括如何突破网络封锁,如何组建社交网络,以及如何进行网络宣传并避免网络追踪等。其中一项被称为“应急按钮”的新技术,能够帮助抗议人士在被捕后立即清除手机中的联系人名单和通讯记录;另一项被称为“手提箱里的互联网”技术,可以在当局切断网络联系的情况下接通网络。一位曾经接受过“自由之家”培训的埃及青年运动领袖表示:“我们在培训过程中学习了如何组建抗议联盟,这在革命过程中非常有用。”
美国民主捐赠基金会曾长期为许多国内外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其第一任主席艾伦•韦恩斯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20多年前中情局秘密从事的工作。”
一个星期的“革命培训”足以让人大显身手
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2月11日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埃及短短18天就“变天”的速度令人惊叹。但实际上,事情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2009年7月,大约20名埃及青年活动分子前往塞尔维亚,接受一个名为“坎华斯”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革命培训”。尽管培训时间仅为一周,但在2011年的社会变革中,这些人利用所学知识大显身手。那么,坎华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简单地说,坎华斯(CANVAS)的全称是“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其前身正是长期受西方资助和支持的“奥特普尔”(OUTPOOR)组织。1998年,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物系学生波波维奇和同伴一起创建了奥特普尔,其目的是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米”成功之后,波波维奇开始投身于选举政治,随后又创立了坎华斯,专门为世界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抗议人士提供“非暴力抗议”培训,以复制前南联盟自下而上的政权更替模式。目前该组织的“毕业生”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近年来发生在中亚和高加索等地的“颜色革命”中都不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埃及、叙利亚等地的反对派也从中受益良多。在埃及抗议运动中,人们在解放广场和开罗街头甚至还曾看到奥特普尔的标识,据说埃及“四六青年运动”的网站也是在该组织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正因为如此,年仅39岁的波波维奇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革命教授”和“全球政治变革设计师”,坎华斯也被冠以“革命公司”称号。
波波维奇自称是一个“非暴力”革命人士,继承了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思想。但如果单靠贩卖“非暴力抗议”的思想和技巧,波波维奇和坎华斯恐怕永远都无法获得今天的影响力。其实,无论是奥特普尔还是坎华斯,其背后的主要支持者都来自欧美国家。奥特普尔早年曾从美国民主捐赠基金会获得资助,从事“非暴力行动和战略推广”的坎华斯则主要从一些欧洲的安全与合作组织、联合国开发项目、“自由之家”,包括那些受美国民主捐赠基金会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中获得资助。
“驱”还是“留”:想说爱你不容易
如果笼统地认为西方非政府组织都在从事“非暴力性”政治活动,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有失公允。事实上,确有不少非政府组织在当地从事维护人权、改善民生或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的公益事业,这也正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对不少非政府组织活动不闻不问的原因。在如何认识非政府组织与中东剧变关系的问题上,西方学者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长期开展意识形态渗透是推动这次中东剧变的关键因素,正如“和平演变”对苏东剧变的影响一样;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效果根本无法得到验证,有关非政府组织活动成效的种种神话不过是这些组织为了扩大影响力而进行的美化和宣传。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塑造了有利于中东政治变革的社会话语体系,为政治反对派开展活动创造了宽松环境。
西方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当地的政治抗议活动提供了思想、组织、经济和技术基础。埃及学者艾曼•奥克尔指出,外来援助对埃及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前就已经显现,在后来的社会剧变过程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非政府组织所推动的“民主治理援助”成功地培育了埃及青年人的“权利意识”,为他们组建政治团体、举行街头示威和集体游行等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2011年4~12月,仅全国民主研究所就在埃及开展了739次短期培训,接受培训的人数多达13671人,其中参加培训的政党领导人、活动人士和候选人约有7700多人,培训内容涉及舆论观察、社会调查、选举制度、妇女候选人培训、志愿者招募、通信联络、新媒体技术等。一位接受过美国非政府组织培训的也门青年活动者说:“培训对我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之前认为变革只能通过武器和暴力才会发生。现在看来,和平抗议和其他非暴力手段也可以达到目的。”
其次,放大了普通民众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和愤懑情绪,增加了执政当局的改革压力。对于大多数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要想在短期内彻底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现代化并非易事。这些非政府组织提出的保护人权、实行宪政、反对腐败、实现社会公平等种种看似合理的社会改革诉求,既提升了民众对于社会政治改革的期待,也增加了执政当局进行社会变革的压力。
最后,引起了当地社会精英在本土价值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的思想混乱,降低了原有的社会共识和凝聚力。在全球反恐战争的名义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夸大极少数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极端活动,使伊斯兰成了落后、愚昧乃至国际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面对西方非政府组织所鼓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一大批当地精英在民族传统和西方主流价值之间出现了认知混乱,甚至丧失了对自身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判断。在这场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变革中,不管是公开呼吁西方介入,还是对其他阿拉伯兄弟采取“党同伐异”的围殴政策,以及在国内政治重建问题上的沉默,多数阿拉伯文化精英都出现了“集体失语”。这种“集体失语”并不是因为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个体差异”、“历史传统”和“长期政治压制”等因素,恰恰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混乱的表现。于是,在革命狂热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原本复杂而多元的改革诉求被简化成了“民主与专制”之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又被异化为不惜一切代价打破现状的愤怒与躁动,并简单地把实行“民主”当做解决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困境的惟一出路。然而,急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未必能够解决阿拉伯世界面临的困境,相反却使一些国家陷入了内乱和动荡之中,并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回潮创造了条件,恶化了原本就脆弱的政治生态和安全环境。
埃及查封西方非政府组织,一度使美埃关系陷入危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甚至威胁取消对埃及的年度援助。实际上,面临类似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不止埃及一个:驱逐西方非政府组织,不仅会失去西方国家的巨额援助,也会失去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助、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等领域的帮助;然而,保留它们又难免会遇到前述的种种风险。
其实,应对西方非政府组织挑战的关键并不在于它们的去留。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非西方国家能够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敢于通过改革和发展消除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那么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非暴力”渗透也就不可能转变为颠覆现存社会体系的力量;如果非西方国家能够牢牢把握自身政治改革的主导权,能够准确识别某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在“援助”与“合作”外衣下的隐性渗透并加以规范,那么这些非政府组织就会成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补充而不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