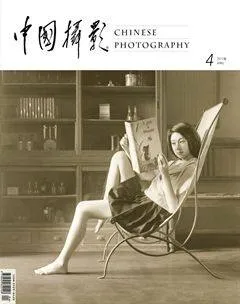摄影,说一个当下的故事
伊芙·阿诺(Eve Arnold)等了15年,终于在1979年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完成了她一直梦想的“终极采访”。前后两次共五个月的拍摄给《生活》杂志提供了一个专题,还出了一本画册《在中国》。前言中,她提及了很多采访时的情景和感受,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她与陪同的新华社同行关于摄影主体与表现的讨论。
“我拍的片子里没有几张被质疑过。有一张被质疑的片子是:六个男人肩扛着一根大石粱,那场景看上去好像是在古埃及的法老时代。领头的随着步子,唱着有节奏的号子,其他人和着节拍扛着梁子走几步,歇口气,再随着号子扛起粱子,移步,停下,放下梁子,歇口气,再上肩,如此重复。”
“虽然我被允许拍这张照片,但之后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和担忧。我们花了一晚上讨论这张片子。中国同行追问到,拍这张片子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吗?是否要在2000年再发表?那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这张片子就可以呈现历史的演进?我说:不,我不指望活到2000年,我只想向这些勇士们致敬,他们为帮助人们实现理想目标而贡献出了一切,我感到他们现在就应该受到赞美。”
2005年秋天,丹尼·莱昂(Danny Lyon)造访了平遥。作为1967年“面向社会景观的当代摄影师”(Contemporary Photographers Toward a Social Landscape)之一的当代美国新纪实摄影先驱,莱昂一直期盼有一天能到中国看看。9月一行把莱昂的心留下了。随后的两年里,莱昂在纽约和山西之间飞行了5次,带着他的两架徕卡和一堆柯达Tri-X,把太原和大同之间的山西记录在了胶片的每一格空间上。2010年,取名《深潜者》(Deep Sea Diver)的影集终于要由费顿(Phiadon)出版社出版了,莱昂也想着把他的山西印象带回中国,特别是呈现给山西。于是,一次试探性的对话开始了:“美国著名新纪实摄影先驱丹尼·莱昂希望把他两年拍摄的山西呈现给平遥摄影节,有可能吗?”“哎呀,对不起,拍山西煤矿的现在谁都不敢碰。算了吧。”其实答话者连样片都没看过,而且根本不知道莱昂的项目都拍了些什么。
我后来有幸看到了莱昂成书的那80张片子和他3万多字的文字故事。那是一种从自己的家世和经历衍伸到另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和社会中的发散性纪实,讲述一个通过另一种文化折射出来的、探寻自我文化中消失了的传统以及人类生存价值的故事。影像和文字中的山西和它的一方水土只是莱昂讲述自我故事时的一个场景道具,但这个场景和道具就像中国之于阿诺那样又是一面冥冥之中等待着的镜子——那面雕着中国古典图案的大铜镜,折射出来的,是人类的共性。
1972年受中国政府邀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的意大利新浪潮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到中国转了一大圈,回去后剪出了一部长达3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之行和所见所闻可能使他再也想不出一个比《中国》更实在的片名,一个理想中的王国居然那么真实地存在于他的面前。当年批判这部片子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包括我。很多年后终于看到了这部取名既抽象又直接的《中国》,那最后近10分钟长的杂技,真让人觉得是否大师在剪片时睡着了以至忘了落刀。现在看来,安大师当年受中国官方邀请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其想法和切入点跟伊芙·阿诺一样,只是依从自己的视点去观照现实而没有去为未来的回眸设想——那段10多分钟的杂技,应该就是安大师心中当时直面中国的感受 。
摄影无论是作为艺术还是记录形式,都是担当一个说故事的角色。说给别人听的故事多少都带着自己的见解,但一定是关于当下的。摄影应该可以确认为是一种艺术无疑了。和其他艺术一样,摄影也忌讳从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做的恰恰都是希望别人认同的事,即使是那些睿智机灵的人,其实也是在为着他人完成自认为引领众人的大业。小八拉子摄影爱好者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社会的关怀者,而大腕名师们则努力用影像为未来竖碑留名——摄影者的初衷就是为着影像以外的宏大叙事意义而创作。于是,作为艺术的摄影呈现的景观是:蜂拥的入门者试图以观念符号的堆砌向那些自己也搞不清想用影像说些什么的成功者们看齐;而作为记录的摄影则是:那些舍弃了休息时间在街头执著搜寻社会意义的扫街人努力发掘着市井角落那些曾经被大师们赋予过意义的决定性瞬间。
经常看到摄影师从“私摄影”的角度把自己的摄影抽离开社会现实谈论自身摄影的“终极”意义,或者从“社会责任感”的崇高境界把自我的感受掩盖在“社会意义”的宏大叙事之中。很少有人能够从讲述一个打动自己的故事开始,用平铺直叙的方式来合盘托出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观点。
每一个有关人的故事就像每一个人自身一样,绝对不会依样重复的。讲好一个人的故事就是讲好了一个有关人类的故事,因为人类的共性就是由无数个人的个性所组成的。
大概是10年前,为了写一篇有关数字技术和视觉影像表现相互作用的论文,与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约翰·佩福利克(John Pavlik)访谈有关数字技术对视觉叙事方式的影响。交谈的最后,佩福利克总结到,无论技术如何先进,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技术永远只是服务于我们讲故事的本能。
把宏大叙事的意愿收起来,想一想小时候奶奶给我们讲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讲自己当下的故事,而未来的意义,就让未来的奶奶们去赋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