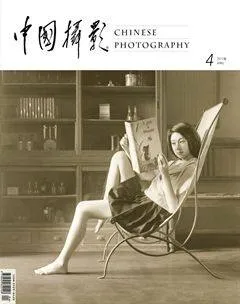去五棵松买一卷胶卷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去五棵松摄影器材城溜达一圈儿。上次去已经是五年前了。
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蹭一个家具城的免费班车去买胶卷。与摄影师绞尽脑汁给自己的照片起题目不同,这个北京最著名的摄影器材交易市场无名无姓,地名成了它的代号。其实,要依了旁边家具城的名字——集美,似乎显得更为理所当然。
器材城有个颇为宏大的官方介绍:“西邻风景名胜香山、颐和园,东邻科技园区中关村……与集美家具城、汽配城、爱家家居、中南电气等一系列专业化市场遥相呼应。”这些不搭界东西混杂在一起,却正好就是掀开厚门帘,你嗅到的味道。
穿过门口的大玻璃镜子,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卖化妆品的摊位;一群穿红马甲的导购,眼睛齐刷刷地朝你身上瞅过来,似乎一眼就能看穿你的来头和钱包的厚度。大厅中央位置的店铺名叫“东方感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门口站柜台的仍然是当年那个丫头,但她已经不卖胶卷了,各种数据线、读卡器堆满柜台。显然,这个柜台的中枢位置仍然没有改变——圆形的柜台空间连通门口最重要的几家商店,只不过它已经升级换代了。
门廊处的古董相机展览还在。一男一女正贴着玻璃瞅,女人对双反相机很好奇,旁边的男人看了一下:“上面那个是闪光灯,下面是镜头。”然后又仔细看看,很确信地说:“就是这样。”四处都响着这种嗡嗡嗡的声音,“焦段是什么意思?”“就是拉近拉远;”净是半懂不懂的人拉着“假行家”在通道里穿行,怀着一种即将变成专业摄影师的渴望。
我得提醒自己,我来这里是为了买一卷胶卷。
五年前,胶卷就已经撤退到商场东头的角落,我朝自己熟悉的方向走过去。几家二手相机商店缩在楼梯间的小格子里,店主在最里面的拐角幽幽地望着外面,让人有些不敢踏进去。经营放大设备的商店,摆着一台微型的裁纸刀,可以托在掌心,淡蓝色。店主说这个不卖:“以前裁一寸照片的,还带花边。”回答完我的问题,他打了个哈欠,准备继续睡觉。
相册和相框还是一门生意,不过,它们不再老实,个个张牙舞爪,呈树状,一堆框连在一起,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盛下不分昼夜涌出的照片。随便走进一家店,门口是成堆的简易相册,这种背面印着“分享此刻,分享生活”的黄色小册子,以前每次在小店冲完胶卷就会得到一个;但正如你在街头任何一个所谓的柯达冲印店都能看到的复杂生态,五棵松的这家店,柯达胶卷和柯达家用照片打印机放在一起,旁边是电池和光盘。
这个冬天,柯达破产的消息沸沸扬扬。在其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柯达雇佣了一个来自惠普的家伙,试图通过做打印机生意进入数字世界。瞧瞧,这些来自机械时代的家伙,面对鬼魅的数字科技,其想象力显得多么有限,就在柯达为其最后的生存拼命挣扎之时,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电子产品展览会如期举行,这座无根的沙漠之城,又绽放出更多奇异的花朵,在这里生成的“摄影”,不用镜头,不用对焦,甚至不用被摄对象就可以拍照。
器材城狭窄的走廊上有个摄影展,用数码相机拍摄的风光照片,都被剪裁成正方形的样貌,这些纵横交错的巷子被官方予以不同的命名:“以器材经营、艺术交流、专业培训为一体,形成了数码产品一条街、婚纱礼服一条街、化妆饰品一条街、技能培训一条街、彩扩设备一条街、二手相机一条街等特色规模经营”。这大概就是大众摄影文化的全产业链。
与一楼被男性主宰的现状完全不同,二楼婚纱礼服一条街四处都是嫩粉和桃红,一间间小店里,男人茫然地被女人牵着,疲惫导致他们在自己的女人披上婚纱从试衣间钻出来的那一刻,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你能听到这样一些零散的话语:“不要选红色,太俗气”;“中国人结婚总应该穿旗袍嘛。”
把婚纱归到摄影器材,似乎荒诞,但这正是平民百姓眼中的摄影,摄影器材挨着家具建材卖自有其中的道理。
前年,我搬了几箱胶卷在家里楼下打车,要寄给一些年轻摄影师,保安小伙子一边帮我,一边顺口问我箱子装的是什么,当了解到都是胶卷,他笑了:“现在谁还用这些玩意儿。”我和他开玩笑:“是啊,所以打算捐给农村。”“什么!”他叫起来:“农村也没人用胶卷!”我继续逗他,“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狡猾:“去送给艺术家。”
五棵松没有艺术家,甚至连文艺青年都没有,最有文化气息的书店清清冷冷,几个人无聊地翻着画册。看了看书架的分类,依旧是婚纱、旅游,器材,其中有一个奇怪的标签:“理论史论/先锋摄影/特种摄影”,里面零乱地堆着新闻摄影教材和战地摄影作品。
在这个迷宫里,我得记着,我来这里是为了买一卷胶卷。
那间常去的胶卷店竟然还在,依旧是精明的掌柜大姐在招呼客人,先生于柜台边忙碌,各色胶卷乖乖地冰柜里呆着。一进门,她就认出我来了,如五年前一样,打了个招呼:“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