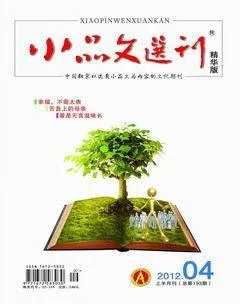过生日
中国传统过生日是吃面条的,以喻长寿长命。生日文化,中外相差极大。老派人家小孩子不让过生日。生日这天称为“母难节”,是母亲受尽生产痛苦才将你带到人间,因此“母难节”要吃素,要向母亲磕头。所以老早小孩子只有过百日、过周岁,没有过生日之说。唯有成年之后,家庭较富有的,闲得发慌找个由头热闹热闹,就做做生日,如《红楼梦》所述。但一般小百姓,小生日也就吃碗面条算了。不过跪谢母亲之举,是一定得有的。
犹清晰记得九十年代我祖父九十大寿, 我正住在香港。一早起来给祖父拜寿,他笑着笑着忽然哭起来:“九十年前这个辰光,我姆妈肚皮痛。养我前还在桑树林里做生活(干活),养了我第三天,又去采桑喂蚕宝宝,可怜姆妈还缠着一双小脚……我今年90岁了,姆妈你在哪里?”白发苍苍的祖父哭得如小孩子。人对母亲的思恋与感恩,是一辈子的!
祖父的九十华诞自然照足顺序做——在香港著名的老上海人蒲点(聚合点),中环的“上海总会”,寿桃寿面定胜糕外加一尊三层的生日蛋糕,自然都做得十分到位。祖父一世思绪敏捷清晰,九十岁也如此。在生日宴上应对得体,但我总觉得,早上祖父那场因怀念母亲的嚎啕大哭,才是他过生日的真性情……
自从上海有了西饼店,就有了过生日吃蛋糕的节目了。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就有DDS、沙利文、马赛、飞达、罗斯玛丽等西饼咖啡店,经营者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不过因为生日蛋糕的裱花不外乎白脱和鲜奶两种,都是白乎乎的,一般上海人觉得不如寿桃那般红彤彤的喜气。当时是连一盘长寿挂面上都要盖一张红寿字的,就是觉得生的面条太素气。因此能接受生日蛋糕文化的,经济能否承担固然是一大原因,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那些有洋大学生洋白领的开明家庭,自然十分热衷洋派的生日派对:切蛋糕、吹蜡烛祈愿、 跳舞、Play Band(玩乐队)……不少年轻人美好的姻缘多是在这样的派对上结缘的。
一些聪明的商家为抢客源,专门做些海派蛋糕——即蛋糕正中由大红糖饼做出“寿”或“生日快乐”字样,边上一圈也同样用糖饼浇制出红红绿绿的各种吉祥图案。这种蛋糕一般都是中国人开的西饼店做的,尺寸比正宗西饼店的要大,包装也是红彤彤的圆盒,盒盖上是一层玻璃纸,一目了然。一般上海小市民贪其价格便宜(其裱花不是鲜奶白脱,是蛋白打发的,成本差好远)又热闹吉祥,倒也很受欢迎。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奶白大蛋糕在过年过节时还十分受欢迎,连南货店都有出售。不过,真正识货的,宁可要素色的白脱鲜奶,那才叫品位。
所谓民心所向,解放了,运动不断,但上海的“凯司令”、“上海咖啡馆”、“老大昌”等仍有原尊的生日蛋糕,哪怕最初的红色风暴过后,“凯司令”改名叫“凯歌”了,橱窗里仍静静地搁着几尊蛋糕。那些资本家老白领白天被斗得七荤八素,该吃生日蛋糕的那天,仍不会忘记。
老友上海啤酒厂小开是六十年代的富二代,1966年8月大抄家后次日恰是太太的25岁生日,家里连床都抄走了,只能打地铺,太太哭了一夜,根本想不到第二天是自己生日。岂知次日一早,丈夫手托一只自制的面包布丁,上面的裱花还是用儿子的奶糕调好代替的,正中插着一支蜡烛,唱着“生日快乐”来到太太的地铺前!
这是我听到的最美最浪漫的过生日的故事。
选自《今晚报》2012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