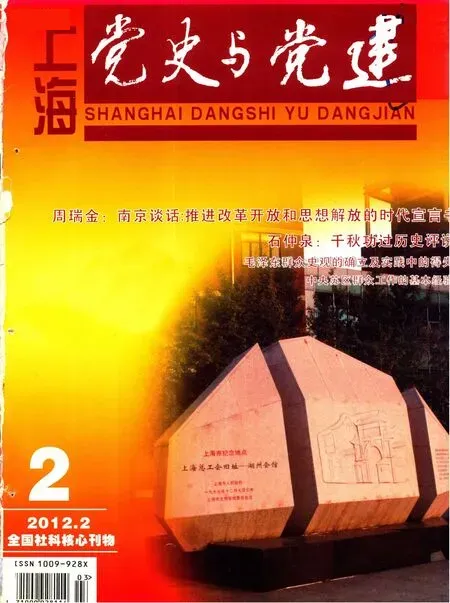“政党领导”:群众路线的逻辑
●李 华
“政党领导”:群众路线的逻辑
●李 华
“政党领导”(或谓“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问题,它既不是无足轻重的简单教条,也不是难以理解的意识形态说教,探讨“政党领导”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变迁的重要方式与应有内容。中国共产党“政党领导”的合法性、稳定性和成效是由其独特的群众路线所界定、规范和实现的,不理解群众路线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地位和方式。本文以“政党领导”及其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为视角,由此审视中国政治的独特逻辑。
政党领导;群众路线;规范领导;领导方法
一、政党领导:群众路线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便寻求从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向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转变,在革命和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共从城市转入农村,由工人阶级转向农民,这一转变使得党的核心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发生了改变。为了应对这一转变,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通过诉诸思想改造、党与农民群众的紧密结合以及整风审干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合法性、稳定性和先进性——总之,正是由以工人为主体转向以农民为主体,才使得中共的群众路线得以产生和发展,也正是由于中国式的群众路线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党能够在远离城市和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下实现了对于农民群众的组织动员,保障了党的领导。
(一)从阶级到政党:“政党领导”的形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是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主导下的行为,无产阶级打破旧社会的革命往往不是这一阶级有意识的整体行为,而是需要少数先进分子对这一阶级以及其他各被压迫阶级的唤醒和领导,由此,正如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革命中的先锋一样,无产阶级的革命也由其先锋队所引导,这一先锋队便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少数革命的领袖。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任务使得列宁更加注重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以及作为阶级和党的领袖的职业革命家团体,“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社会阶级;而对列宁来说,关键却是政党。”[1]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从无产阶级的领导向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的转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偏重于——或者说演变和表述为党主导的革命和党的领导。由此,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而言,重要的不是无产阶级是否发展成熟,是否可以自觉自主地完成其变革社会的历史使命,而在于是否有集中统一的、由阶级和知识的精英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苏联及其既有理论和经验的影响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知识分子的小团体逐渐转变为阶级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由此领导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政党领导”的基本逻辑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又有着自己的创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更加倚重于,甚至直接等同于党的领导,“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的一个特征,就是政党和它的一个领袖的决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在一个更长的时期中,比其他国家更直接,更重要,更显而易见。”[2]
(二)从小团体到广泛的党:“政党领导”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将推动和领导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当做自己的目标,党认识到从理论走向斗争、从精英走向群众、从狭小的团体走向广泛的组织的重要性,党的广泛性、群众性的基础在于党自身的组织纪律与统一,而表现则在于党深入群众和深入现实。
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研究性的小团体到广泛的、群众的党的转变,首先必须增加党员的数量,改善党员的质量,使党员成为能够深入现实和斗争,成为动员群众的精英,使党能够成为领导社会革命的稳定而有效的核心力量。此外,党要领导革命,党要生存和发展,就不仅要从少数人走向多数人,更需要从抽象的理论研究走向现实流血的斗争,从以自我为中心走向领导群众以及从唤起群众的自觉走向发动群众的抗争。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逐渐完成了自身的组织建设以及对群众的组织动员这双重任务,进而从一个最初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研究性团体特征以及脱离现实和群众的小的组织转变为组织有效、领导有力以及深入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由此,“政党领导”这一革命理想得以真正落实。
(三)阶级的党与群众的党:“政党领导”与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既作为阶级政党,又作为群众政党存在,即党既具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又必须深入和领导群众。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和先进性有着自身的生成逻辑,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定义,而近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更是远离了无产阶级所在的城市。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和定义由经济和社会属性为基础转变为思想意识的属性为基础。由此,在无产阶级的判定上,思想意愿和立场较之于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阶级属性往往显得更为重要,思想上的锻炼则可以实现由其他阶级向无产阶级立场和属性的转变,“人的思想倾向并不像历史唯物主义所断定的那样来自于他的阶级出身。他的阶级现在要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一个聪明的农民可以成为一个‘无产者’。这是主观的政治考虑对经济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的胜利。”[3]而对于社会现实真理性的认知、正确的思想作风以及最重要的价值立场便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式群众路线具体的认识论、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组织原则以及价值取向在党的领导中的落实——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属性和毋庸置疑的先进性——使中国共产党在脱离无产阶级现实基础的同时实现了其对于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意识和正确立场的诉诸。
就中国共产党群众政党的本质而言,由城市转入农村,使中国共产党由一个以工人成分为主体的党转变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通过理论的创造和现实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农民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共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这种能力体现了似乎是共产党革命的悖论:即它与其说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倒不如说是以农民为基础。”[4]在党看来,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可以赋予并体现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进而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党代表、领导和解放农民群众所体现出的先进性较之于其对城市无产阶级的代表、领导和解放更为现实,也更为重要,“我们说领导关系,上下左右关系,归根到底是同人民的关系,主要是同农民的关系。因之,我们的作风,领导方法,归根到底是同人民,主要是同农民的关系问题。”[5]这一转变直接造就了中国式的群众路线的产生,“群众路线是针对农民社会的问题与缺陷而提出的。”[6]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基本群众,是党群众路线的主要对象,群众路线的认识论、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组织原则以及价值取向也主要是基于和针对农民展开的。
总之,群众路线不仅保障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思想价值上的联系,维系了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更直接推动了党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确立了其群众政党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阶级党和群众党角色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了内在的契合——即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角色而诉诸群众路线,而这一群众路线是党与农民之间的、针对农民的群众路线。由此,群众路线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领导得以顺利展开。
二、政党领导:群众路线的构建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抑或社会革命的现实来看,都需要党对于群众的领导。没有对群众的领导,党的生存和合法性便无法实现,对群众而言,革命理论主导下的外来领导必然是对其既有角色和社会关系的改造,进而形成对群众带有强制性的组织和动员。
“领导”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作为历史主体和沉默大多数的群众的唤醒与动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群众,在于党认为自己具有相对于群众的“政治远见”,这种政治远见必须形成对群众的落后意识的主导和改造,这种对于现实和未来的、超越群众的预见性使党得以领导群众。“领导”联系着党和群众,党是领导的实施者和主体,“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7]群众是领导的接受者和对象。作为领导者的党和作为被领导者的群众是相伴而生的,“领导”并不是简单的少数人主宰多数人的方式和过程,从理想上看,“领导”是党让群众自己理解、自己践行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角色和作用,即自己解放自己,领导的本质在于唤醒群众的自觉。党自身没有力量,而只是为群众“指出方向”,从而使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解放自己”的目标。
当然,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则群众本身的存在以及历史作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无群众的领袖固然无用,无领袖的群众又何能成为有组织的争斗?”[8]因此,可以认为“自发性的群众”的存在是“党的领导”的前提,也可以认为,“党的领导”则是作为“自觉性的群众”存在的前提。没有党的领导(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领导),则群众永远只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永远无法实现其历史意义,实现自身的解放。总之,“多数人”作为现实的存在物一直在历史中发挥着不自觉的作用,但“多数人”转变为“群众”,并实现自我的解放的过程则是从党的领导的确立开始的。
“群众路线”所构建和规范的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党的领导”与“群众自主”辩证而有效的统一。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党的领导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群众的这种自主性又必须导向党所指出和所需要的方向,而不能发展到冲击乃至否定党的领导的程度。群众自主性反对党的“强迫和替代”,但这种自主性又不能极端化为抛弃党的领导,成为“放任和自流”。
从根本意义上说,党对群众的领导不是基于“法律体系”,否则领导便是一种“强制关系”;不是基于“组织原则”,否则领导便是一种“命令关系”;更不是基于“武力强制”,否则领导便是一种“胁迫关系”:
信号发生部分分别通过SDATA(串行数据输入引脚)、SCLK(串行时钟输出引脚)、FYSYNC(控制输入引脚,低电平有效)引脚与单片机控制部分相连,通过这三个串行I/O口将数据写入AD9833芯片中[8]。AD9833的工作时序图如图6所示。
党是群众的先锋队,他的责任是教育群众领导群众,他并不能命令群众……党对群众的领导,不能站在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法律观点上,也不是站在“以党治国”的组织系统上,更不是因为党有武装力量,乃是因为党的一切政治主张都适合于群众的要求,都能取得群众之自愿的拥护。党应当说服群众,而不能强迫群众。[9]
由此,党领导群众,源自党能够取得群众“自愿的拥护”,即党的一切主张都是适合群众需要的,无需“命令”和“强制”,只需要“宣传教育”和“耐心说服”。当然,在现实革命和政治中这是难以很好实现的,这便构成“群众路线”的主要任务和自身难题。
“党的领导”需要党深入、贴近群众,但党的领导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党直接领导群众,而是通过各种“中介”和“链条”来完成的——如政权、军队和群众团体等,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内容。因此,群众路线要求党不应该只通过自身的组织与群众发生关联,也不应该过分约束——尤其是国家政权和群众团体——的自主性及其与群众的关联。如果仅仅强调党对于“群众的组织”(政权、军队和群众团体)的领导而不发挥其自主性,便是一种“包办”,即国民党“以党治国”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而仅仅强调“群众的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那么“群众的组织”便会因失去“价值引导”而无法存在。当党既能够合理有效地领导政权、军队和群众团体等作为联系群众的“中介”和“链条”,又能够保障政权、军队和群众团体动员组织群众的自主性和效力时,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党的领导便能够得到切实的实现。
三、政党领导:群众路线的规范
(一)群众路线与党的自我约束
有领导,就必须有对领导的规范和约束。群众路线既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以其独特的方式规范着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式的党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平衡意味着党要保持其领导地位、规范其自身权力行使和范围,就必须进行必要的“自我的约束”:一方面,党如果不进行自我的约束,则容易形成对于群众、国家和社会的凌驾和过分压制;另一方面,对党的约束从根本上说是党自行完成的,在党看来,这种自我的约束是保障党的领导最有效和最主要的方式。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在现实中,党都非常强调其对自身的约束,也认为这种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是可能的,群众路线为党的自我约束提供了基本的手段和价值取向。具体而言,这种“自我约束”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党员的自我约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强调党员干部的理想特质,它要求党员必须为群众而不能为自己存在,能够在群众面前忘却自己;它要求党员干部既要超拔群众之上,又时刻与群众一致,乃至时刻向群众学习;它要求党员在公共权力面前忘记一己私利,能够合法、公正和有效地为群众执掌公共权力……总之,它要求党员成为一种特别的人,进而更多地通过党员自己以及其内在的精神和理想实现对自己责任的承担和义务的履行,而由这样的党员所组成的政党必然也是能够实现对自我的合理定位,能够实现对自己的约束,最终服务于群众,实现群众路线的理想价值。
其次,党内的纪律与民主。党内的纪律与民主是保障并制约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党对自身的一种约束,即通过自身组织和制度的完善使党的领导的外部效果合理化和最大化。如果没有党内的组织纪律,党的内部便无法统一,党的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以及党组织对党员便难以实行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党的领导能力因内在的张力而削弱,无法规约党内部出现的对领导逻辑和方式的冲击。如果没有党内的民主,领导权力过分地集中于党的组织、中央和上级,则会使得党丧失内在活力,进而丧失领导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总之,党内的纪律与民主是党内部进行上下级、组织与党员之间相互平衡的根本方式,这是作为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群众路线对党的基本要求。
当然,除此之外,不应该忽略现实环境和现实条件对党的领导的有效规范与制约。群众路线是现实逼煎下的产物,也正是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群众路线得到了更好的落实,现实环境和条件使得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在群众的认可和对群众的柔性动员基础上,使得党的领导不能过度地向党的集权倾斜。然而,随着革命的成功和新的国家的建立,群众路线所借由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现实的严峻环境得到了根本意义上的改善,这虽然使党能够通过更多的方式接触群众,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的诉求,但是当没有了现实生存的危机以及拥有了更多的权威和对群众更多的控制方式时,党往往难以像革命年代那样,继续在深入群众、贴近群众上坚定不移。从这一意义上说,群众路线对党的领导的约束效力与党的特殊处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处境的改善使得群众路线对党的约束逐渐削弱,这就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群众路线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发展。
现实来看,党员人数的增多和成分的变化使其通过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以保障党员的先进性的困难增加;党的组织复杂化和所执权力的扩张使党的内部整合和自身建设有待提高;社会的多元化和自主性使得党动员群众的能力和方式不断弱化……凡此种种,不仅削弱了对党的领导的约束,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党的领导本身造成了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在保持领导的同时要实现对这种领导的规范和制约,必须一方面继续诉诸群众路线;另一方面,则必须加强整个国家法制体系的构建及其对党的领导的明确和规范——当然,由于国家的法制体系本身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公民身份的形成和权力的增长意味着作为党的基础的群众的消解,而试图从党对群众的领导中寻找作为第三种力量的公民和国家对党进行监督和制约既难以一时奏效,又构成了对党既有领导角色、地位和逻辑的冲击,因此这样的取向虽然适应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路径和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但其过程必然是渐进的,这构成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个困境。
(二)群众路线与党的自我整肃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和党员队伍的理想性和纯洁性。当党由城市转入农村,面临艰巨的斗争困境时,为了实现内部整合、加强对党员的控制以及对党内施加进行外部斗争的压力,仅仅诉诸党内的纪律是不够的,或者为了加强惩戒的效果,使纪律演变为“非常的恐怖纪律”,这最终便造成了苏维埃时期的“肃反”及其扩大化——即通过将党内的纪律极端化或者诉诸纪律之外的斗争运动,寻求党在外在困境面前的内在统一和动力。
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至1944年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另一种方式的全党性的内部整肃运动。延安时期领导地位的维系和动荡艰巨的环境使得党内在的统一、思想和人员的纯洁依旧难以仅仅通过诉诸党的纲领和纪律来实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于苏维埃时期肃反扩大化的反思,创造出了新的、群众路线式的整党审干的方法,这一整党审干方式实际上是对党内的群众路线(“组织路线”)的诉诸,进而更好地落实党与人民群众(革命时期的农民群众)之间的群众路线(“政治路线”),“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10]这种群众路线式的整党审干与苏维埃时期的肃反扩大化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强调人的可改造性。即认为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成分不仅仅是由其阶级角色和社会地位决定的,而是与人对现实的认知和态度直接相关,因此人对现实的认知和态度的正确性源自其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的、不间断的改造。党为了净化党员、落实党的纪律以及整合党的力量,必须依靠对党员思想的改造,依靠党员“心灵深处的革命”,由此,不断出现的“整风审干”替代了肉体的消灭作为解决党的问题的有效方式。虽然这种运动式的、诉诸于党员内心革命的整风审干并非没有其强制性的特征,也并不能一劳永逸抑或制度化地解决党内以及党所面临的问题,但它在一定时期有效地保障了党的统一和纪律,也并没有通过极端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群众路线成熟的表现和价值。
其次,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而非意识形态的教条成为评价党员最重要的标准。即对党员而言,真理不源自党的意识形态——尤其不源自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而来源于“群众”(底层群众,其现状与所处环境),“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11]党自我整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对其意识形态的遵循,更在于对群众和现实的贴近与契合。因此,党员干部需要改造的原因,即党员干部思想意识和现实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仅仅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掌握的不够,而在于其与群众的脱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不仅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更在于对党的历史现实的理解和对群众的贴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群众化和现实化。出现问题,需要进行整风改造的党员必然是脱离群众的,反之亦然,这样,整风运动中对党员问题的界定和解决是十分清楚的和具体的,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再次,采取群众性的整党审干的方式。即在整风运动中,发动党员进行相互的和自我的批评,形成一个学习和改造的热潮,所有党员,包括领导者都必须加入到这一热潮,接受运动的洗礼。党的自我整肃不仅仅要依靠和改造领导干部,还要依靠和改造普通党员;不仅仅改造党自身,而且发动和教育普遍意义上的人民群众;不仅从上到下,而且自下而上地推行和开展。当然,群众路线要求这种群众性的整党审干运动是在党的控制和领导下进行的,是党发动下的行为,“群众性”也主要体现在党内,而不是一种对党外普通群众及其无知和狂热的简单利用。
总之,群众路线式的整党审干较之于血腥的肃反更好地实现了党内部的统一,保障了党员干部的纯洁,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创造更好地维系并规约了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群众路线式的整风审干走向了其过分偏重于群众自主的极端,发动起来的狂热群众并未达到对党及其领导进行整肃和规约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对党的冲击,削弱了党的领导。进入新时期之后,党群众路线式的自我整肃仍继续通过更加柔和与多样化的方式进行,这是党为规范其领导作风和保持领导地位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75.
[2]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23.
[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279-280.
[4][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江苏:江苏人民出版,2007.12.
[5]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九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387.
[6][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魏晓明,冯崇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9.
[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4.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427.
[9]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240.
[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19.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7.
D261
A
1009-928X(2012)02-0009-05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