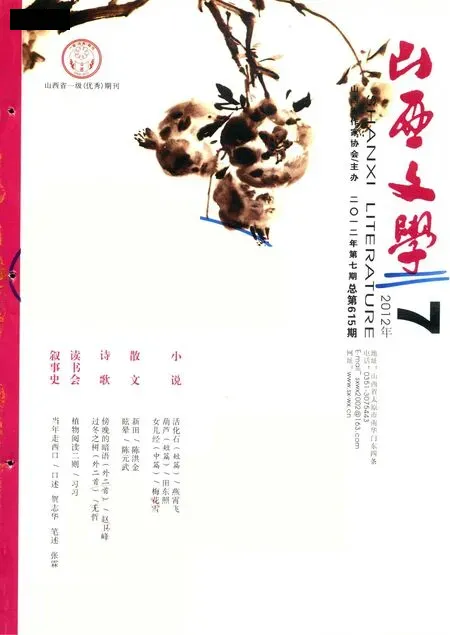眩 晕
陈元武
1
眩晕开始于一次寻常的意外,耳朵里长了一些耵耳,痒痒的,老想拿什么东西去掏一下,棉签不好使,就听信了修脸剃头师傅的话,让他用大耳勺子掏了一回,耳朵里突然就舒坦了起来,仿佛揭开了几层被子,让皮肤裸露于清爽的空气中,那种清凉是无法形容的,透气的感觉舒服极了。那个剃头师傅还拿一只毛掸子在掏过的耳朵里轻轻地旋转,耳朵里敏感的神经顿时都让这毛掸子给唿扇了起来,感觉极为舒适而美妙,在接近于痒与舒服之间游移。修脸师傅说,你这人太懒了,耳朵里都堆满了耵屎,你不感觉堵得慌?我说都习惯了,也不太难受,就是有一阵子耳朵有点不好使。他说那是正常的,都堵成这样了,能听到动静就算不错了。脸上感觉有点烧,我对耳朵似乎从来就没太在意过,耳朵嘛,能有什么事情可折腾的?不像鼻子,堵了就喘不上气,自然会想办法让它通通气儿。师傅说,再过几年不掏这耳朵,就堵死了,再也疏通不了。我问为啥,他说,耳耵在里头久了,就硬成石头一样,跟肉长在一起了,可不就堵死了?哦,不掏耳朵的风险如此之大,于是养成了天天掏耳朵的习惯,这耳朵里仿佛有无限的皮质脱落和耳耵,天天掏都有收获。渐渐的,耳朵里有点痛,痛起来仿佛有一条通道直达大脑,连着头也眩晕起来,于是,不敢太用劲掏,只敢用棉签轻轻拨弄。左耳朵原先经常闹中耳炎,鼓膜穿孔过一回,算是残废的耳朵,感觉某一处特别敏感,似乎声音的收集器就在那儿,尽管棉签只是轻轻地撩拨,也感觉动静特别大,简直像是在耳边炸了一炮仗似,脑袋嗡嗡嗡地响,似有一千只蜜蜂在耳朵边叫着。走路时也感觉天旋地转的,别人老问我为啥不敢睁大眼睛看大街,我说是阳光太刺眼了,晃得厉害,其实是脑袋晕得厉害。
我是十多年前患中耳炎的,起因就是一次意外,那时候经常去河里游泳。乡下的河就是儿童的天堂,在夏天的时候,乡下的孩子就整天泡在河里,像水牛牯一样,我也是这其中的一个。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河流,水进入了眼睛、鼻子和耳朵。中耳炎发作,头痛欲裂,耳朵里火辣辣地疼,流脓水,腮帮肿,喉咙肿,吞咽困难。乡村的赤脚医生阿叶给我注射庆大霉素,在那个简陋的乡村医疗室的长板床上,我侧躺,让他往耳朵里注入双氧水,双氧水沸腾,冒泡,耳朵里全是冒泡的声音,然后往下,让脓液随双氧水流出,淌向地上,滴滴答答,继续冒着气泡。耳朵里微凉了片刻,然后继续肿痛、难受,嗡嗡嗡幻听。头晕目眩,对着墙壁上的毛主席像和语录,对着人体穴位图和解剖图,我睁不开眼睛。我只想闭着眼静静地待着,直到庆大针剂产生作用。墙上的挂钟嘀答嘀答地响着,当当当,准点报时,阿叶说可以回去了。我走下台阶,阳光刺眼,只得微闭着眼睛,眼前一阵旋转,看到的事物都是幽绿色的,暗晦不清。又不敢睁大眼睛,那眩晕感渐渐地消退,耳朵里依然疼痛,但已经没有方才那种肿胀感了。
中耳炎让我不得不在家休息,河流成为别人的乐园。风从瓦垄间吹落,扬起尘埃和细微的事物,麻雀在屋檐底下聒噪,似乎在评头论足我的熊样。要是平时,我早就摁捺不住给麻雀们点颜色了,现在不行,我只能静静地躺在竹床上,闭着眼睛,怕炫目的光芒。耳朵里依然叫着一千只蜜蜂。烦躁、难受,让心情坏到极点。连家里的鸡都来欺侮我,在竹床底下咯咯咯叫个不停,轰走了还回来。我知道是哪几只鸡在跟我捣乱,家里有一只芦花鸡,是这群鸡的祖母辈,就属它最懂人心事,无事时,它就带着一群孩子去树底下练习刨坑钻沙子扒拉出泥土深处的虫子。鸡的叫声断断续续,叫一阵子,就沉默了,扑扇着翅膀,扇出满屋浓郁的鸡粪味。我起身撵它们,呼啦啦跑了出去。过一阵子又都转悠了回来,原来鸡怕热,外边热,屋檐底下凉快。麻雀根本就不理睬我,它们想说话就说话,想拉屎就拉屎,屋檐底下弄得乌七八糟。早晚得让这些麻雀后悔,我心里不再顾着疼痛了,只是发狠。
2
有一回重感冒发烧,烧得昏天黑地的,也不知道在床上躺了几天几夜。再看墙壁是绿色的,屋里的物什也是绿色的。想坐起身来,天旋地转,感觉身体处于一个可怕的漩涡里,天花板在旋转,地板也在旋转,那盏45瓦的白炽灯泡在头顶也直晃悠。父亲喊我吃饭,我说实在不想吃,父亲说都两天不吃东西了咧,那咋能行,不吃东西更晕得厉害。父亲说的不无道理。于是强喝下一小碗稀粥,然后渐渐地适应了站立的状态。
屋外的风呼呼地刮,南方的冬天就是风大,那风无孔不入。楼上的窗户让风刮得啪啪响,几乎要将窗扇吹下来。我说还想去睡,出不了门。平常吃过饭,我都出去走走。村子里有条道,临着河和一片稻田,秋后的田野里空荡荡的,种下的麦苗还未长出,垄畦间是一道白一道黑,白的是垄,黑的是畦,萝卜刚种下,得放水淹着畦催苗。麦子更得放水催根,南方没有雪,但冬天的风能把大树刮瘦一圈,那风将任何见得着的水分都挤干了去。麦子生根的时节,怕旱,像我这会儿一样,头重脚轻了不行,容易让风刮跑了。
我踮着脚跟往窗外瞧,对过就是凤子的家,凤子是我同学,两天来我没去上学,她到我家瞧我好几回。塞给我一只煨得软乎烂透的地瓜,说你生病了就得多吃点,吃了这个就有力气。我吃了,虽然不像她说的那么灵,但似乎真的不那么腿软眩晕了。凤子握着我的手喊我小名:狗子,身体好点了么?我摇了摇头,脑袋晕得厉害,不敢太用力摇。我握着她的手也不肯撒,她的手软得像鹅毛一样,温温的,她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睫毛里透出一些难过的神情,她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说没事的,你不用担心。凤子出去的时候,抹了一下眼睛。
身体好了的时候,我碰到凤子,凤子说她爹不让她再读书了,女孩子念个小学能认点字就够了,读那么高文化有啥用?她父亲肯定是说我姐,我姐读到高中,上山下乡回来,在大队做赤脚医生阿叶的助手。姐能认得乡下几十种草的名儿,哪些是药草,哪些不是。凤子的爹想给凤子的哥提亲娶我姐,提了一回让我父亲一口回绝了,凤子哥是个木匠,整天走村串户的辛苦,人也老相,看上去不像是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姐喜欢城里人,老想嫁到城里。凤子支支吾吾地说出她喜欢我的话来,我说你喜欢我啥?凤子的脸飞红了,瞧你那损样,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我说真不懂,凤子急红了脸,再损我可真生气了。到时候,我嫁给你,你姐嫁给我哥,可不是亲上加亲么?我说,我是我,我姐是我姐,你是你,你哥是你哥。这怎么能扯到一块去?凤子生气走了。
那一夜,我也睡不着,小学五年级多了,乡下的孩子懂事迟,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事情,班上要是谁在黑板上写谁谁跟谁谁好上了,当事人准哭红鼻子,这是件羞臊人的事情,凤子怎么敢在我跟前说那种话呢?我翻来覆去地想,也没想明白是咋回事,眼前总是晃悠着凤子那好看的丹凤眼,长长的睫毛和红红的脸颊,凤子长得可不是一般的俊俏,要不我母亲也不喜欢她来我家。凤子好几天不理我,见到我脸上像冻着冰,没好脸色了几天,我主动跟她打招呼,她竟应了,笑得挺不自然,但我感觉她笑得好看极了。凤子说,我爹说晚上可以去你家做作业,你是不是乐意我去?我说当然乐意,太乐意了。凤子跟我一起做作业,我心不在焉地乱瞅她的脸。她抬起头,干吗这么睃人家,眼睛像贼似的。那天我头突然不觉得晕了,心跳得厉害,像怀揣了一只小兔子。我说凤子,明儿个咱们俩去打猪草,你去不?她点点头。
麦子已经长到齐踝高了,村里人在这段时间里不管麦子,也不管麦地里悠悠长着的草。凤子扎了根大麻花辫子,辫梢还特地系了条窄红布条,宽松得像朵倒垂的金钟花。蹲在麦地里薅草,红蓼和鼠尾巴草还有大叶牛蒡。薅着薅着,就停了下来,凤子说,你头还晕不?我说有点,她赶紧将我的头搂住,可不是,这野地里风大,不会是让风吹着了吧?我说兴许是吧,风大着哩,吹得我眩晕。你闭上眼睛一会儿就好了。我闭上眼睛了,她的脸贴着我的脸,身上散出好闻的气息,我说你抹了百雀翎了吧,她说哪有啊,我说我都闻见了,好香。她一下子甩开我说你真坏。那时候我真想说点什么,少年内心里的那一点朦胧的美好瞬间被点燃了。我睁开眼睛,她正瞅着我笑,那笑容美得让我心醉。我说,那天晚上你说过的话还记得不?啥话?就是你将来想嫁给我的话。凤子的脸飞起一抹红,啥时候我说过这话?瞧瞧你说话不算话。凤子说那你姐又不肯嫁给我哥。我说咱们俩的事情扯到你哥我姐干什么。当然得扯上了,要不我爹能答应么?怎么不能,将来我肯定比你哥出息,你跟着我肯定幸福。那一年我们十五岁,我躺在麦子上,天空多么蓝,太阳直直地升起,将天边染得金光闪闪。
3
凤子成为我眼里的媳妇了,那一年我考上了初中,到县城里去了。学校离家很远,寄宿在学校,很少回来。凤子在家里成了村子里的新劳力,村里像她这样的女孩都没继续上学了。凤子书读得一般般,她没考上县中。母亲说,凤子这丫头要不住我家吧,她爹死活不肯,这没三媒四妁的就住你家,算怎么回事?其实两家就隔着一条弄子一个院子而已。两家的屋檐滴水线都接到了一块。有一次,在学校的游泳比赛里,我的中耳炎再次发作,只好回家休息。在我家楼上看到凤子,坐在她家院子里搓草绳准备收割早稻。她胖了许多,脸也圆了黑了,特别是她那双手,粗瓷了不少。凤子,我喊,她跑了过来,她一下变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像桥下的村妇一样黑而微胖,脸上没有了少女的红晕,只有日头晒出的古铜色。她摸了摸我的额头,手粗糙得像一块砾石。她的手上还裂开许多血道道,是让稻草绳割破的,手掌心的老茧像铜钱般大小。母亲说,这孩子真是好劳力啊,为替她哥攒钱娶媳妇,跟她父亲一样上山扛石头做重活。这孩子要是到咱家,就是福气了!母亲说得眉飞眼笑的。凤子已经和村子里的那些女人并无区别了,她的改变让我惊讶和无奈,和我的同学相比,那些城里的同学显得娇气而美丽。凤子坚持说要替我洗耳朵,她扶着我去村医疗所,医生还是那个阿叶,不过,他现在不叫赤脚医生,是乡村医疗所的正式执业医生。凤子执意要扶着我去,她的手劲大得让我惊讶,我在她手里像一只软绵绵的布袋一样。路上,我的脸一直偏向另一边,我不想和她说话。凤子脸上布满了焦急,她嗫嚅着,想说什么。风从她的身体吹过来,如此接近的距离,让我闻到她身上的酸臭味和一股莫名的骚气。她原先的好闻的香味哪里去了?凤子说,她哥到现在还打着光棍,人家说你家要房子没房子,要钱没钱,凭啥嫁给你哥?凤子说她现在和父亲一起打工,早上到一家养猪场打饲料喂猪,下午到城里的工地摔泥坯码砖头,天天风吹日晒的,就成这样了。凤子咬着下巴,她似乎不愿意说更多的事情,她也察觉出我对她的冷淡,她说你现在是城里的学生了,将来会读大学的,我是无望和你兑现诺言的。她说着,我听得心里酸酸的。我感觉自己的脸都烧得快冒出火焰。
阿叶看了我的耳朵说,你的耳朵恐怕治不断根了,是慢性中耳炎了,怎么一直好不起来?凤子脸上的焦急神色愈加浓重,她问阿叶,那不是要聋了么?阿叶说那不一定。可我知道,那就是有可能。凤子的眼里淌下晶亮的泪水,她以一种同情和无奈的表情看着我,阳光从她的脸上掠过,她汗涔涔的脸像秋后的苹果皮一样,细微的汗毛在额顶晶亮闪耀,她的眼睫毛梢挂着未干的泪水,凤子的眼睛红红的,我心里一下子软了下来。凤子忽然问阿叶,我能不能来这里学打针?阿叶说,不行,你得去城里的护校学,你得有那里的毕业证才行。凤子急得直晃脑袋,我不学那个,就学打针行吗?阿叶说那你来吧,正好我这也缺一个帮手。凤子后来学会打针,扎绷带和换纱布缝针挂瓶子,母亲说,凤子这孩子真是好,心灵手巧的,还特别懂事。凤子知道,她将来有可能用得着那些手艺,虽然没有工资拿,她一到晚上就去医疗所义务帮忙。凤子吃力地读那些医疗书籍,比比划划。后来凡是我或者父亲、母亲他们碰到生病,她就来家里做护理,换药和吊瓶打针都方便多了。凤子说,狗子的身体很弱,读书伤身耗神哩。我经常接到母亲的信,说凤子如何如何。但我实在犹豫,我不可能在家乡务农,我会走得很远的。事实上,我考上大学以后,凤子就很少来我家问这问那了,母亲读出了她内心的想法。凤子有一天突然来信说,她要出嫁了,是离村三十里的海埕角,换她的嫂子回来。信纸上满是梅花状的渍痕,一点点一圈圈,纸都皱得不成样子。那一天,我也伤心哭了,跑到学校的后山上转悠了一个下午。我不知道该给她怎样回信。
4
春节回来,没看到凤子,看到她家窗户和大门上贴着红红的喜字。凤子爹阴沉着脸,我打招呼他也不理睬。嘴里咬着一只木头烟斗,使劲嘬烟,大口大口地咽。他将我喊进屋,说凤子给你留了许多信,他递给我一只上了锁的木匣子,说,她不让我开锁看,都在这里,都给你的。他的眼睛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我低下头走了。信有几十封,都封着信皮,只是没贴上邮票邮出去。一封信里说:“我今天出嫁了,可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像是一块石头沉向大海,永远也回不来了。狗子弟,你的耳朵还出毛病吗?北方天冷,冬天得买皮帽子遮脸遮耳朵,要不冻坏了……”“今天我头一次下海,这边的生活很艰苦,一点也不比家里舒坦,婆婆的脸色也是难看的。早里嘀咕了好久,不知道在嘀咕什么,老往我这里瞧,估计是嘀咕我的……”“天上飘着小雨,海风不大,但海浪很急,今天得收两船紫菜和海蛎子,我的手都裂开了,海水咬得钻心疼,他也不管我,腰都快断了似的……”“你啥时候放寒假,来看我好吗?我都数着日子,你还有四天放寒假哩。昨天傍晚,喜鹊一直在树梢叫……”我的眼泪如泉水般淌了下来。母亲让我吃饭,我说没胃口。母亲大概知道了咋回事。她也在一旁叹着气,唉,多好的孩子,咱们家没福气哦。母亲说的是凤子出嫁前还替母亲扎了两床稻草褥子,打了两副竹簸箕。母亲说,她认了凤子做干女儿。以后回家,就到家里来吃饭。
凤子回来了,她瘦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海边风大,刮得她的脸更黑,并且长了许多雀斑。她看到我,脸上开心得像灿烂的荻花。狗子回来了,她攥着我的手就不肯放开。耳朵好了么?我说好了,很久都不曾疼过了。北方冷么,我说冷,下厚厚的雪,快淹到膝盖上了。啧啧,那么大的雪,该多冷呢!凤子的笑声让屋里的气氛顿时热烈了起来。他爹端一盆羊肉来,一起吃饭,凤子哥和嫂子不来。聊的尽是大学那边的事情,凤子不肯说她自己的事情,都说挺好的挺好的。凤子让我吃一包干海参,说是她自己淘海淘来的,全是野生的。凤子说你耳朵不好,得吃这些海货,再说北方那么冷,肯定吃不到这些东西。母亲一直瞅着凤子的脸。我低头闷吃闷喝,嘴笨着哩。凤子爹叹了一口气,这孩子没福气啊。到那海边受那洋罪。凤子低头,胸口起伏得厉害。那顿饭吃得没滋没味的,虽然凤子一直有笑声。其他人都心事重重。
后来,凤子就再没消息了,她也没给我写过信。我都不知道她的情况。母亲告诉我,凤下海浸坏了身子,不能生育,丈夫离婚了,现在一个人去了广东。他父亲也去世了,喝闷酒喝坏了身体。我再次头晕目眩,许多年后,我还记得那一次,冬天的阳光刺眼地照着凤子家那陈旧残破的大门,墙头长着干枯的野草,凤子家里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她哥和嫂也出去打工了。家里没人,托我母亲照看。那棵苦楝树已经掉光了叶子,枝梢还挂着一些干枯的苦楝籽,风吹得燥响,一阵一阵的。太阳刺痛了我的眼睛。那张泛白的喜字已经让风吹得只剩下一些残片。凤子,你在哪里?母亲念叨着,这孩子要强哪!她抹着泪。我的头胀痛欲裂,这是老毛病了,只不过很久没犯了。我不敢抬头看天空中那轮太阳,头晕得难受。人生无常,人生无常啊。母亲总念叨这一句。
眩晕从此一直缠绕着我,白天或者黑夜。我想起那些往事,一点点,像放幻灯片似的。凤子那张青春而美丽的脸在脑海里一闪而过,泛黄,陈旧,却是那么的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