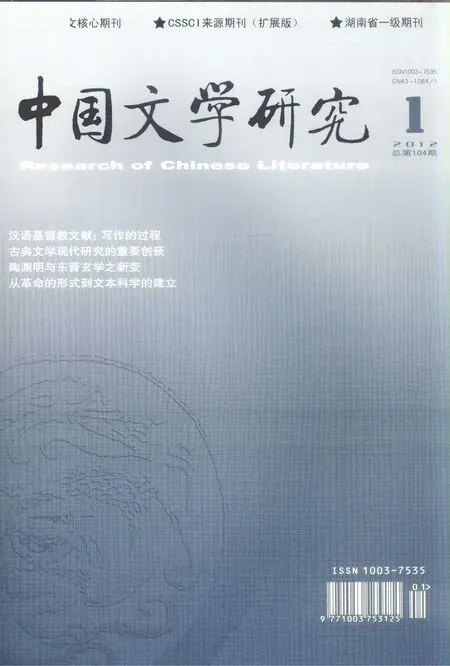史诗的崩溃与日常生活的深入:从海子到安琪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精英文化,随着90年代的经济转型,也发生了根本性质变。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似乎把中国推进了现代社会,而事实上,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社会转轨过程之中。伪现代社会兼有封建性的交杂的社会型态,与移植过来的后现代文化,使得中国的价值尺度从来没有如此的混乱。社会主义官方话语的主流、封建话语的余毒、现代主义话语的梦幻、后现代话语的迎合,一片喧哗与骚动。90年代以后和21世纪初的社会状貌,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英雄史诗时代的终结。李泽厚说:
现代社会的特点恰恰是没有也不需要主角或英雄,这个时代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所谓散文时代,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平凡而琐碎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没有英雄的壮举,没有浪漫的豪情,这是深刻的历史观。〔1〕(p506)
当代知识分子也许不承认自己的士大夫心态,但恐怕还是自以为社会“精英”,老实说,以为可以依靠“精英分子”来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以为充当王者师或社会精英,可以设计一套治国方案、社会蓝图,然后按照这套方案和蓝图去改变中国,完全是一种幼稚病。〔1〕(p509)
在这么一个语境的变迁中,诗坛一个巨大的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和此后的“中间代”诗人的史诗意识开始崩溃。海子和安琪分别是两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诗人之一。
一
20世纪80年代的史诗形态有多种多样,既有朦胧诗人北岛和江河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对垒中书写着英雄史诗;又有朦胧诗人另一代表杨炼和第三代诗人宋渠、宋玮、石光华等书写着文化史诗,则是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相对思维、儒道互补还原成为富有宇宙感的文化意象,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还有第三代诗人中的廖亦武等人,以激进的生命激情和生命原欲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审判;更有还有被命名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等,在私人化的精神空间容纳了很强的史诗意识。海子则是20世纪80年代史诗情结的集大成者。他的理想是成为“诗歌王子”、“太阳王子”。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的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2〕(扉页)在《诗学:一份提纲》里他呼唤:“人类经历了个人巨匠的创造之后,又会在20世纪以后重回集体创造。”〔2〕(p901)
诗人海子成为一个巨大的“精神神话”已是公认事实。其实,一种东西被称为“神话”主要是由于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些原型,这些原型成为不同地点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所认同的共同话语,他的个人话语与人类共同话语有一种同构性。海子在它的诗篇中揭示了天空与大地、天堂与地狱、黑暗与光明等人类生存的基本母题,使同时存在着的彼此对立的两极各自沿自己的方向无限延展,将人类生命的矛盾加以强化。由于20世纪80年代精英文化理念的凝聚力的强大作用,海子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核心定力和充分的自信。他这种自信是那个朝气蓬勃的时代氛围酿就并促成的。同时,这种自信也影响到他的诗歌文本形态:海子的诗作都用鲜明的意象处理他的史诗题材,思维路向是线性的、执拗的、形而上的。在海子的《太阳·七部书》以及长诗《河流》、《传说》、《但是水、水》等诗作中,在线性的思维路径上,在“天”、“地”、“神”、“人”等母题构建的意象群落里,充分展开了“生”与“死”的冲突。明显可以看出,他的意象空间往往是“真空”的,是在一个纯粹的时空里展开的。其结构的整一与其宏大抒情构成了完整的统一。海子的史诗写作的模式是:习惯从远方寻找诗意。诗意的奥秘存在于远方,这是一种逃避现实存在的倾向,往往被称为获得诗意的传统的经典方式。这种倾向西渡称为“童话写作倾向”。海子内心的执拗找寻与时代末日般的黑暗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以至他有一种“走到人类尽头”的悲剧感。我们用灵魂去阅读海子的长诗《太阳》七部书时,会强烈感受到这是海子站在人类尽头凄厉的叫喊。他透彻的喊声像一束圣火洞穿了黑夜,将众多长眠的死者和睡去的活者一齐唤醒,这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后对于生存的绝对本质即形而上永恒追求的绝望与痛苦的质问。人类的生存是一种相对时空中动态的历史存在方式,在动态而相对的生存状态中寻找人类终极的绝对的形而上本质,无疑是虚幻的乌托邦的追寻,他那绝对的“爱”和绝对的“尽头”使人的生存趋向犹如西绪弗斯神话是一种悲壮的结局,因此海子禁不住对自己和人类身后漫长的羁旅发出痛苦的质问:“我们生存的理由是什么?”
1989年成为中国文化的分水岭!有多少意识形态的东西打着历史的旗号篡改了历史事实!残酷的历史事实打破了人们对于历史理性主义的幻梦……历史理性曾经甚至现在仍然像一个绝对意义的幽灵主宰着国民的价值根基。历史理性主义是一种价值的设定,在黑格尔那儿,历史有其内在的规律,也就是说,历史是一条必然之路,当历史沿着自己的必由之路往前走的时候,它似乎是一种雄踞于人的生命之上的绝对力量,个体生命乃至意义在无情的历史必然的面前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换句话说,当某些人物被命名为、被指认为历史的代言、历史规律的象征或者历史精神来实现的人格载体时,他似乎就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历史”不是人的创造物,反而成了人的异化物,历史的主体“人”让位于虚构出来的“规律”和“历史理性”,规律超过和压倒了任何主体,人便成了历史的道具。现在,历史理性主义的幽灵已经或正被人们的理智所洞穿,历史理性主义的大厦即将倾颓!在历史理性主义即将解体的背景下,一些诗人虽然写出了不少优秀的长诗,但是,宏大的历史抒情少了,大多不再拥有书写史诗的野心,而更多地把历史置换为经验的素材。
安琪倒是中国当下诗坛具有明确的史诗写作意识的一个个案。安琪说:“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像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3〕(p23)其诗学理想与海子的自我企望多么相似!安琪的《五月五:灵魂烹煮者的实验仪式》副标题则是《屈原作为我自己》,由此可见安琪的诗学野心——成为一种史诗性诗人!她的《轮回碑》、《九寨沟》、《九龙江》、《西藏》、《张家界》等结集于诗集《任性》中的长诗,追求天、地、神、人的合一大境。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她的“对于史诗的一往情深和建构自我史诗体系的野心”(马步升语)与“历史断裂、破碎状况所决定的这种野心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史诗崩溃的见证。如果说海子是在“人类尽头”和“世纪末日”的西绪弗斯,他一次又一次地绝望地把时代的巨石推向山顶,终于在最后的一瞬间,他的战胜历史的历史理性主义对峙轰然倒塌,被巨石碾过了身躯,殉身于历史理性主义,那么,安琪则是见证了西绪弗斯神话解体之后历史理性主义的破灭。她是以史诗性写作的自我解构的方式见证了历史理性主义解体后的废墟!
安琪本来是以其尖厉的短诗锐出诗坛的。她的诗集《奔跑的栅栏》绝大多数诗歌是短制,以极其富爆发力和冲击力的情绪意象,冲破了语言的栅栏,集中将其内力喷射出来。这些短诗的内涵还是非常私人化的。经由《干蚂蚁》、《未完成》、《节律》、《风景》、《曦光》等长诗的过渡,到了长诗结集《任性》,她的诗歌内涵逐渐阔大开来,向史诗境界突进。诗集《任性》中的《西藏》、《张家界》、《轮回碑》、《灵魂碑》等长诗,充分显示了安琪建构史诗的野心。由于诗境的尽情拓展,九寨沟、西藏、九龙江、张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全部纳入她的精神视界。她抛弃了早期诗歌中鲜明的意象诗写路径,将写实、夸张、灵气、原始、天文、历史、地理,“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变构为集大成的合题,诗人分裂为多个自我:“安”、“黄”、“安琪”,既审视世界,与外物对话,同时又多层自我进行对话、独白、驳斥、辩解。形式上,她的语言颠覆性非常鲜明,冲破了语言的“奔跑的栅栏”之后,开始了新的“语词的私奔”(格式语),她的“私奔”历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与“反动”,而是语境的拓展过程,在“一路私奔”中历史语境、现实语境和她的灵魂世界得到最大限度的拓展。诗歌建行出现反美学的极端不规则,这在巨诗《轮回碑》中汪洋恣肆达到了极至。虽然安琪也从“天”、“地”、“神”、“人”等母题构建其史诗体系,但是,她诗作中的这些基本母题不是“真空”的。海子是内敛的、无指向的痛苦,安琪是发散的、及物的痛苦。其痛苦的精神指证了其所处的生存语境的罪恶,她的诗作是对大自然、历史、现实、文本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整合,所以,她的诗作常常被称作“大拼盘”、“大杂烩”,过去、现在、未来一维的时间成了立体的往返空间,古今中外,现象界与精神界互融,现实与冥界勾通。她不是海子式的——精神痛苦指向一个焦点,而是将精神碎片辐射到构成并且遮蔽了精神之痛的一切,这个“一切”不是焦点透视,而是散点透视,它是无中心的,有指向而无中心之痛,是弥漫开来的“场”,她的痛苦的灵魂就像一朵花,只闻其香味,而无法触摸香味之所由。这正是安琪之痛的独异之处。无中心之痛,使得她的文本成为“形散神也散”的巨大的耗散结构,为了更充分地展示精神破碎的“场”,她将任命书、邀请函、访谈、戏剧、儿歌等各种文体融入了她的长诗之中,开放性的文本“恰如时代的拼盘:股票、军火、土地、民族……/什么都往里装。”安琪在建构史诗体系的同时,恰恰是在深层解构了史诗。德里达的对立学说认为,任何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都是无中心的系统,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的稳定结构,而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这张“蛛网”上的各个网结都相互联结,相互牵制,相互影响且不断变动游移,做着不断的循环和交换,因此,一个符号需要保持自身的某种连续性,以使自己能够被理解。但在实际运用中它又事实上被分裂着,它无法永远同自身保持一致,它在有限的构成中不断的解构自己。它因此具有了提供多重涵义的可能性,阅读的过程,或者说,对某种意义的把握过程,但究其本身,还是对原有文本的破坏过程和解构过程。不过,其支离破碎的精神之痛与支离破碎的结构的统一,不是证明安琪的“无能”,恰恰证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状况——破碎感。
如果说,海子的史诗里“自我主体”虽然集中了他“全部的死亡与疼痛,全部的呜咽和悲伤,全部的混乱、内焚与危机”〔4〕(p110),但是他的自我主体是完整的,内敛的,凝聚的。海子内心深处潜藏的历史理性主义价值幽灵在90年代已经被驱逐,历史理性主义的空洞在80年代末让大家跌入虚空。80年代所坚执的凌空蹈虚的价值一下子被抛向了90年代破碎的“在场”中,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无能”与“无力”。因而安琪的史诗“自我”则是分裂的、难以整合的,发散的,碎片化的。安琪的史诗建构野心的破灭,与其说是她自我的内部瓦解,毋宁说是历史理性主义破裂带来的自我碎片化生存状况的觉醒,更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指证!安琪以史诗性写作的自我解构的方式见证了历史理性主义解体后的废墟!她在非史诗时代所做的史诗写作,这种行为本身即是一个巨大悖论。
二
这个悖论在诗学意义上促使安琪2004年前后发生了剧烈的诗写转型——由史诗写作转向生活写作。由此,我们把她的写作分为福建时期和北京时期两个阶段。如果说,安琪福建时期的史诗写作靠的是激情与想象,是反生活写作,那么,北京时期的安琪则是生活化的写作。用她自己的话说:生活更像小说,而不像诗。
如果考察安琪这一时段的生活化诗写行为,就会发现,她接续了海子式的大悲痛,但是二者痛苦的震源却完全不同。海子的痛苦源于他对于形而上的绝对力量的追逐,胡书庆将海子悲剧概括为“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5〕。海子的绝笔之作《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可以说是海子精神上下求索中断而最终导致灵魂破裂与自焚的心史,形象地显现出海子精神世界的悲剧实质。在他的心中,一直包孕着天空与大地、光明与黑暗、寻求与分裂多种精神元素,构成他的诗歌内在力的图式呈现向上与向下截然相反的两极。作为精神依托的大地,最终“荒凉”下来,“天空”一无所有。海子是屹立在痛苦风暴的中心歌唱痛苦的人,痛苦是他创作的源泉,他不惜以生命的消失取走了诗歌的痛苦。他的悲剧性的诗思是凌空蹈虚的,但内在的力的图式倔强得保持着不可遏制的向上的动感。这也是海子史诗写作的根本推动力。
而步入90年代以后,中国大的时代语境是从凌空蹈虚的向上的精神图式转型为底层生存境遇的勘察,以激情为动力的史诗理想破灭了,诗人不再倚赖激情、才气和想象力的自动式写作,而多以具体生活语境下的生命体验为主。在这个阶段,安琪基本上放弃了史诗写作。她早期的史诗写作是发散的、无序的、无方向的、激情的,而北京时期的诗歌写作则是内敛的、下沉的、生活化的,相当一部分诗歌即是充分生活化的日记体。她2007年初创作的《你我有幸相逢,同一时代——致过年回家的你和贺知章》、《北京往南》、《父母国》、《幸福时代》、《天真的鞭炮响了又响》、《归乡路》等,明显加大了生活品质,故国、亲情等传统母题,成为她诗歌动力的重要元素,甚至带有某种温情主义的味道。这时候安琪的诗歌,强化了感情色彩,而减弱了实验色彩,重新恢复了诗歌的抒情特质。如《七月开始》。尤其是诗的结尾“你在发短信,想我,像房东在想她的房租”,堪称经典,把一对情人之间的相依为命的感觉写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承续了福建时期的语词上的非常规组合的奇异效果,同时又不同于福建时期的超现实语境,而是具有了非常丰富的人间气息和生活三昧。
北京时期的安琪其实是双声部的,既有“沉潜的静思”,又有“逼利的沉痛”,既有试图超脱的“安”的追索,又有尖锐的“不安”的生活体验,大安的超远与不安的沉痛,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当然,在她的作品里,经常出现沉静的情境,乃至于对生命的参悟,如《活在一条河的边上》、《要去的地方》等等。这大概与安琪信佛有关。她对佛有一种本能的亲近。2005年她有不少诗歌是以宫、寺、殿、坛等为题,如《大觉寺》、《地坛》、《雍和宫》、《潭柘寺》、《白塔寺》、《法源寺》、《欢喜佛》。也许只有经历了太多磨难的人,才会相信佛教。安琪信佛教,试图找寻出对人生意义的超越。爱、死,是她的创作母题。《雍和宫》、《地坛》、《大觉寺》等都渗透进了安琪对于灵魂隐痛的超越意图。但是这种超越是非常艰难的,在她试图超越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她浓得化不开的苦痛与苦衷,乃至于对于彻悟的反动:“看见和被看见都不会静止不动/看见不会使灵魂安宁/被看见不会使生命真实”(《雍和宫》)。在大觉寺,她并没有“大彻大悟”,“找你找得那么苦/阳光在手臂上,痛,热,辣。/路在脚上,远,辗转,到达。”所以她说:“大觉寺,要多少个漫无边际的恍惚才能顿悟/我起身,步态迷离/我离开,心怀期待”。虽然她执著地说:“你们在那里,等我走近,等我坐在长长的,有背景的/银杏树下,阴凉的石凳,我重新出生”,但是,实际上,这种执著的背后是难以言传的悲恸。
她越是想超脱,越是敏感到痛苦。尤其是2006年的新作,痛苦的焦灼越来越显豁开来。用安琪的诗句说就是:“往极限处再任性一点/点,就一点,就能达到碎裂部位,就会看见/脑浆汹涌”(《再任性下去》)。她在2006年的诗作接续了她早期代表作《干蚂蚁》的大痛风格。如果说早期的痛苦,更多的是对人生的直觉性感受,那么,现在的安琪则是生活深处的那种椎心之痛,是人生变故带来的沧桑之苦。原来的痛苦是弥漫的无根基之痛,犹如被蚊子叮咬后到处是痒,但是无处可抓,那么现在则是具体伤疤下无法抑止的鲜活血液。她的诗“用一连串的阴暗引爆一连串/又一连串/的阴暗”(《循着阴暗跟我走》),充满了大量的“恐惧”、“悲哀”等语词。她的诗境有时非常阔大:“那宴席浩大,一字排开,那宴席装下了你、我/日月山川”,但是,如此阔大的诗境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确证,而是证明自我的破碎与分裂:“星光灿烂在梦里/宴席浩大在梦里/如此灿烂的星光方能照到我满腹的苍凉/如此浩大的宴席方能装得下我无边的惶恐”(《宴席浩大》),真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沉痛!她不再是冲破语言的栅栏从自我向阔大的外在世界一路狂奔,而是走进灵魂的逼仄的内在通道。她开始从无限的宇宙向内在宇宙开掘,诗境趋向内敛,她的《悼词》同样是沉痛之作。她展示给我们的总是现世生活的负面部分,生活中的她俨然“一个丧失爱的能力的人”,努力地“在一个所处非人的时代,活得,像一个人。”(《为己消防》)近作《浮生歌》、《恐惧深如坟墓》则几乎可以看作安琪个人的灵魂痛史。正是这种深深的恐惧式体验与超脱现实生存的追求,紧紧纠结在一起,构成了安琪近期写作的多元色。在对“大安”的渴慕中,无法遮蔽的是剧烈的“不安”。
非常有意味的是,她的史诗写作,显得汪洋恣肆,充分自信,现在的生活写作,表面上在追寻“大安”境界,而深层显示出的却恰是充分的不自信与“大不安”。从以生命为根基的生存到以生活为根基的生存之转型,虽然她一再表示认同,但是,她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神空隙供我们遐思。有必要再次提到安琪的诗歌《大觉寺》和散文《二进大觉寺》。她说:“我的上半生以诗歌的名义犯下的生活之错之最,在下半生的开始即得到迅速的还报,这个果我认。这也是我此番到大觉寺的内在原因,我的下半生在大觉寺确定之后所应承当的欢喜忧愁,都是我理应面对的。”〔6〕难道诗歌之生存真的像安琪所体悟的是一种“以诗歌的名义犯下的生活之错”?她的达观和认同,真的这么义无返顾?她会这么决绝地放弃诗歌?我的臆测是否定的,直到最近她仍然情有独钟于她的随笔《诗歌距离理想主义还有多远》便是明证。她慨叹:“诗歌的力量已经远远大于父母和全部全部现实生活了,已经说不准在哪年哪月,这个女儿在不知不觉中掉进了诗歌的陷阱,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起来。”〔7〕事实上,安琪已经陷进了诗歌的陷阱,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起来。
三
尽管安琪在一些访谈和文章里,表达了远离诗歌而走进生活的决然态度,而事实上,诗歌这根肋骨一直藏在她的身体里、灵魂里,“诗歌英雄”的情结像人性基因一样,在其血液里流淌,她的言语表达与内在的价值定位是分裂的。海子连同他的史诗理想随着轰轰烈烈的80年代的强行折断而骤然熄灭了,无数的后起诗人对于海子予以嘲笑、攻击、颠覆、解构,但是海子情结却一直沉淀在安琪的灵魂深处。诗歌以及诗歌所蕴涵的理想主义已经成为安琪的“肋骨”,或者说,安琪已经成为诗歌的“肋骨”。诗歌和理想主义已经成长为安琪的精神基因,无法祛除,也正如安琪所说:“正是这根骨头使全世界的诗人们彼此相通在某时某刻,使我在不断的失败中不断遇到好朋友支撑着我,一直到今天。”〔7〕
在安琪的诗歌中多次出现著名的诗人或具有诗性的文人,如海子、庞德、杜拉斯、曹雪芹、史铁生等著名文人成了安琪的自我人格的镜像,可见安琪的诗学野心。安琪与他们之间心心相息,构成了文化通约和精神通约,正如安琪所言:“《红楼梦》是我预定的陪葬品之一,我已经看了十几遍了,基本上是每隔几年就要看一遍,好像采气一样。”〔8〕她与海子也可以做互文关系来解读。当年海子曾表达了他的诗歌野心:“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的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2〕安琪也说:“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3〕其诗学理想、诗学气魄,与海子的自我企望多么相像!
在她的诗作里,我们发现一种关于安琪与著名人物的人格镜像之间的深层思维,即巫术思维。如果说,安琪的史诗写作中的巫术思维是模糊多向的直觉思维,那么,最近诗中表达安琪与诗人镜像的关系时,使用的巫术思维便是交感巫术,其内涵是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安琪与曹雪芹的关系、安琪与海子的关系,都往往借助交感巫术思维,加以强化。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里,把交感巫术分为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两类。接触巫术指的是:“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相互远离。在这样一种交感关系中,无论针对其中一方做什么事,都比如会对另一方产生同样的后果。”〔9〕(p57)安琪探访曹雪芹故居、魂游海子自杀地山海关,都具有这种交感巫术的意味。2005年她在海子的忌日写下了《在昌平》:“在昌平,我想到海子的孤独,在昌平的孤独里海子死了/今天是3月26日,海子和昌平一起被我挂念。”在海子生活过的地方昌平,感同身受海子的命运;同日她创作的《曹雪芹故居》同样显示了这种深意。
安琪所流露出来的交感巫术与原始思维中的交感巫术并不相同。原始思维中的交感巫术所体现的更多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而安琪的这种巫术思维,恰恰体现的是她在感同身受的对象身上找到自我的确证与自信,是在某个精神人格镜像上折射并且强化安琪的自我价值,这种强化在深层彰显出安琪自我的天才定位,尽管她是潜意识的。诗歌英雄情结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顿而中断,而是潜藏得更深了。在她把生存的重心转向生活的同时,她内心更认同的是海子的“我必将失败/而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的卓绝的理想主义精神。在她的心中,一直把海子作为价值标杆:“我只知道,我又一次陷入的对理想主义的怀疑需要海子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来安慰自己”〔10〕。诗歌和理想主义乃至英雄主义是安琪的三根“肋骨”,是她的非常顽烈的人性基因。她不是在《死前要做的99件事》中说过吗?——“准备好要带进棺材的东西:一套《中间代诗全集》,一套《红楼梦》,一本《比萨诗章》,一本《奔跑的栅栏》,一本《任性》,一本《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盒莫扎特《安魂曲》,一盒绿茶。”〔10〕
2004年前后的安琪转型了,这只是在外在上表征为由史诗性质的写作转为生活化的短诗写作,而灵魂深处她仍然在延续着基本的人性基因:视诗歌为生命的诗歌英雄主义、诗歌所寄寓的理想主义。只不过由于生活状态的被动转型,这些基因潜藏到了更深层。正由于转型的被动性,她才感受到无奈,这种无奈与其说是诗歌上的,毋宁说是生活上的。她说:“时至今日,我从未对诗歌有丝毫怀疑,诗歌带给我太多了,已经超过了我的命运所能承受的。我唯一必须怀疑的是,我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不能永远坚定不移地扎根在我身上,为什么每次遇到一些选择关口,我的痛苦和无力感幻灭感总是那么深重地折磨着我,使我几乎放弃继续理想主义的勇气。”〔7〕生活的转型对诗人来说是个磨难,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讲,这种转型使得安琪的诗歌写作更加贴近地面,去开掘诗意的深井。从汪洋恣肆的大海转为大地上的深井,对于安琪来说,仍然是个“现在未完成时”。我们希望她会把生活的椎心之痛与铭心的刻骨酝酿为更丰富的诗意。到那时候,安琪肯定不会再像海子一样感叹着:“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1〕李泽厚.世纪新语〔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西川编.海子诗全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3〕黄礼孩、安琪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广州:内部出刊,2001.
〔4〕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5〕胡书庆.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6〕安琪.二进大觉寺〔J〕.高原.2008(1).
〔7〕安琪.诗歌距离理想主义还有多远?〔J〕.诗刊,2008(2).
〔8〕安琪.诗歌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对它爱恨交加〔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557e2010004au.html,2006-06-12.
〔9〕〔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10〕安琪.诗歌距离理想主义还有多远?〔J〕.文学界,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