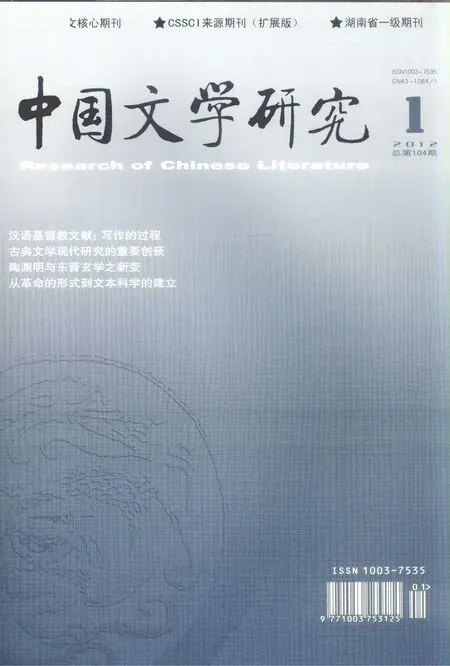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的“图像批评”
张玉勤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品类繁多,形态各异:有文论,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有诗论,如《沧浪诗话》、《原诗》等;有词论,如《人间词话》、《蕙风词话》等;有曲论,如《曲律》、《曲藻》等;有画论,如《历代名画记》、《画语录》等;有书论,有《书谱》、《书断》等;有评点,如《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甚至有著序、题跋,如《画山水序》、《广川书跋》等。其实,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传统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文艺批评形态,即图像“批评”。对于图像人们并不陌生,对于图像具有叙事功能也都基本认同,但鲜有人把图像视为一种文艺批评形态,并从学理角度加以专门研究。不能不说,这是文艺批评的一种缺憾和“遮蔽”。
一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过“图像批评”概念。王宁先生曾认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式将逐渐从文字写作转向图像的表达,而伴随着这一转向而来的则是一种新的批评模式的诞生:图像或语像批评”。〔1〕此处的“图像批评”指的是,当前的文学批评方式已由对语言文本进行批评逐渐转向对图像文本进行批评,进而导致文学批评的方式、媒介、形态等发生改变或走向转型。显然,这一层意义上的“图像批评”是针对文学创作所发生的图像转向而言的。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从传统的文字写作逐步过渡到图像写作,那么相应地传统的文字批评也应该转向当今的图像批评。但本文所提出的“图像批评”却另有所指,它是基于“语-图”互文的一种特殊文艺批评型态,是指用图像形式进行的文艺批评,即图像本身构成了一种批评。
爬梳中国古代的图像“批评”,首先要引出一个概念,即“图文本”。图文本,即语言和图像共存于一个文本之中,二者共享一个文本。“图文本”不同于单纯的图像或文字,前者所确立的理论平台和基本视野是“大文学观”、“整体文学观”,而后者仅局限于图像或语言本身。在“图文本”这一宏观视野下,“图像”与“语言”不再是孤立的、敌对的、各执一端甚至相互抵消的异质媒介,而呈现出交汇融合的新型关系。在传统视域中,人们总习惯性地徘徊于“扬图抑文”或“扬文抑图”的二难选择中不能自拔,这势必会对图像“回到事物本身”式的本质探寻带来一定的干扰。而“图文本”既非“图是文的附庸”,也非“文是图的配角”,既不会因为“语言优先”而对插图无动于衷,也不会因为“图像先行”、图像易为人们所理解接受而弃“文”从“图”。“图文本”之图、文,尽管有媒介表达的不同,却都是文学作品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书之书”的概括十分形象,如果说传统的文字之书是“小书”,那么图文本则是“大书”。“大书”追求的是“文本图像化”和“图像文本化”的交相辉映。既然有“图”可鉴就不望“文”生义,既然有“文”可依就不按“图”索骥。我们完全可以在“读文”和“看图”的双重乐趣中体验图文本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抽象的语言表达不清楚的,直观的图像让你一目了然;反过来,单纯的图像无法讲述曲折的故事或阐发精微的哲理,这时便轮到文字‘大放光芒’了。”〔2〕正所谓“索象于图,索理于书”(郑樵《通志略》),“两美合并,二妙兼全,固阙一而不可者也”(王韬《图像镜花缘》序)。
图像“批评”是基于“图文本”的一种特殊批评形态。也就是说,在图文共存的“大文本”中,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两个“小文本”同时在承担着“批评”的功能,前者以语言实现批评功能,后者以图像实现批评功能。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插图、题画诗等,它们犹如文学评点般,或以图言说,或以图代评,或以图导读,并在语言文本、图像文本之间,在作者、插图者、读者之间,构成某种对话关系。中国古代的“图-文-注-评”本更是集原文、注释、评点、插图于一体,其中注释、评点是对原文的一种阐释,插图同样是对原文的一种阐释,且诸种阐释之间还可以构成新的互文性。台湾学者马孟晶便认为,插图在明代版画中所占的位置,实应同时兼顾图文两者。在她看来,书籍的版式与插绘的设计者可说是文本最初的读者,一如注释或评点者,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形式,正如评点者可以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一般,也可能模塑读者的视觉习惯或观览方式。〔3〕有的学者把图像视为“另一种讲述的方式”(伯格);有的则把图像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借此表白自己对艺术、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悟和姿态,如陈洪绶绘制《水浒叶子》和《屈子行吟图》。传统语言构成批评不难理解,接下来将对古代图文本中的图像何以构成批评予以考察。
二
批评是什么?别林斯基认为,“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作出判断’;因而,在广义上说来,批评就是‘判断’”,“进行批评——这就是意味着要在局部现象中探寻和揭露现象所据以显现的普遍的理性法则,并断定局部现象与其理想典范之间的生动的、有机的相互关系的程度”。〔4〕J.T.希普莱在《形式、技巧与批评》中提出,批评就是“对文学作品的描述、解释和评价,揭示作品所包含的原则和理论,并运用这些原则和理论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对作品进行判断和鉴别”。〔5〕中国古代图文本中的艺术图像虽然不像常规批评那样直接诉诸于语言文字,却同样是在言说,它以图像的形式,形象、直观又含蓄、间接地传达出图像作者的判断与评价,因而是一种“无声的批评”。
1.图像选择体现出图像作者的“视点”。对于图文本中的图像,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入图,对所选择的内容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予以呈现,势必包含着图像作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英国图像学家伯克认为,“如果认为这些艺术家—记者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也就是以为他们的眼光完全是客观的,不带任何期待,也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那也是不明智的。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隐喻的意义上说,这些素描和绘画都记录了某个‘观点’”。〔6〕阿拉贡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当我把别人的、已经成型的思考引入我写的作品里,它的价值不在于反映,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和决定性的步骤,目的是推出我的出发点。”〔7〕鲁迅为了纪念遇害的“左联”五烈士柔石等人,曾在《北斗》创刊号上选用了一幅珂勒惠支木刻画《牺牲》。画面表现的是一位母亲悲哀地闭上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后来鲁迅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说,柔石被害时,“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8〕(p517-518)显然,鲁迅选用这幅木刻画体现了他的特殊用意,是他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批评”。
2.图像转译体现出对语言文本的诠释。在中国古代图文本中,图像常常依附于一定的语言文本,体现为图像对语言的“顺势”模仿。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作品只有通过再创造或再现而使自身达到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不再是一种附属的事情,而是属于它自身存在的东西。每一种这样的表现都是一种存在的事件,并一起构成了所表现物的存在等级。原型通过表现好像经历了一种在的扩充”。〔9〕如此看来,图像作者首先是语言文本的最初阅读者,也是语言文本外化为图像文本的实现者。这个过程是一个诠释(即游戏)的过程,而且这种诠释和游戏的结果参与了语言文本意义的生成,因而是作品之“在”的扩充,同时与“文”成为“共在”。比如,晚清时期的“新小说”家们对于时弊的指摘可谓肆无忌惮,“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10〕,而当时盛行的“绣像小说”则以绣像插图的形式予以诠释性的“时评”,“其意乃借鉴小说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启蒙作用之经验,运用文学的通俗性和普及性特点来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唤醒民众,刷新政治,从而达到除弊兴利、富强国家的目的”〔11〕,可谓图文“并茂”,图文“互评”,图文“共在”。
3.图像解读体现出对语言文本的“发挥”。图文本中的图像虽然“以图为评”,但“图”绝非“文”的附庸,而追求借“图”发挥(说事,表情,达意),凸显“言外之象”、“象外之象”的艺术空间和审美拓展,其本质是一种“言象诗学”。一是图像文本对语言文本的意义溢出。即图像作者常常把对语言文本的意义解读内化于画面中,隐藏于图像深处,做到含不尽之意于“象”内。像《西厢记》中的莺莺像、《娇红记》中的娇娘像等,已不止是剧中人物的肖像描摹,而有更为深刻的符号指涉。二是读者解读对图像的意义溢出。读者既要解读“文之意”又要解读“图之意”,并在此过程中以自己的视域融合与期待视野,实现着作品之在的扩充和绵延。的确,当我们审视陈洪绶所作的《屈子行吟图》时,不难看出人物脸部偏离观者、画面作大幅留白等技术化处理,无疑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直抵文外之意、象外之象的超越空间。
4.图像阐释体现出意义空间的敞开。任何一种批评都有自己的局限,因为它只是提供了特定的阐释视角。在图像文本中,“艺术家不可能完整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因而这便给读者/阐释者留下了可据以进行能动阐释和建构的空间”。〔1〕读者可以通过驻足、观看、凝视,充分调动起自己的艺术体验、审美联想、情感反应,不仅可以领略象内之意,还有可能企及象外之意。这便是图像文本意义空间的敞开所带来的阐释乐趣,也是图像作为一种批评应有的姿态。像《红楼梦》卷首的人物绣像不仅让读者直观地欣赏到人物的外在形象,更引领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像外世界;不仅图像作者的观念、态度、趣味等透过人物的描摹和场景的安排深嵌其中,读者亦可透过图像生发出深邃无限的想像空间。
三
中国古代图像批评传统源远流长。远古岩画叙事、早期的象形文字等,可以视为图像批评的早期形态;到了汉画像艺术世界和魏晋像教思想那里,图像批评已初见端倪。尽管此时的图像批评还很不自觉、很不系统,甚至到了宋元时期出现的大量宗教、科技类书籍插图,依旧没能摆脱实用性、技术性、装饰性的局限,文学、审美、艺术的味道几无,图像批评形态还没有完全形成,但确乎为中国图像批评传统的最终成熟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古代较为成熟的图像批评形态有如下几种:
一是以图入诗的“题画诗与诗意画”。“诗意画”是“以诗入画”,即以诗词文赋为主题,以绘画的语言表现诗意化的精神气韵与哲理思想,在绘画中拓展文学化的内涵,实现诗画一体;而“题画诗”是“以诗补画”,即在绘画的基础上以古典诗词形式诠释、补充画意,以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凸显深意。无论是题画诗还是诗意画,都强调诗画互文、诗画合体。“异质同构”与“互为图底”是其理论依托。所谓“异质同构”,即是指诗画虽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媒介,却可以在诗作者与画作者之间达到内在艺术精神和审美旨趣上的同构相通;所谓“互为图底”,即诗与画一方为“图”(显),另一方为“底”(隐),二者构成图底、互文关系。
二是以图入事的“小说插图”。中国古代小说充斥着大量的插图,而尤以明代为盛。这些插图与小说语言文本一样承担着叙事功能,而且是通过“关键场景的瞬间定格”、“俯视视角的叙事隐喻”、“叙事表现的空间拓展”等形式实现的。明清小说插图一方面“从文本中来”,辞宣其貌,图绘其形,辞所不及,以图绘之;另方面又实现了对源语言文本的超越,承担着语言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叙事功能。“图”因“文”而生,却又产生“像外之意”。于是,图像文本与语言文本、像内与像外、文外与像外等,彼此关联,相互呼应,形成了多重互文对话关系。
三是以图入意的“戏曲插图”。与小说插图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戏曲插图既有以图叙事的共通性,又崇尚闲适情调和文人情怀,追求“曲情文意的绵延激荡”。如果说前者是“故事画”,后者则是“曲意图”。“照扮冠服”的舞台性、“象意相生”的抒情性、“美仑美奂”的装饰性,构成了戏曲图像批评的特有品性。戏曲插图还在戏曲的文人化演变、文人画追求等方面,体现出“以图入意”的诗性特征。诸多戏曲插图作品都成了文人们抒情遣怀之载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12〕
四是以图入史的画报和“绣像小说”。如果说宋代以降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造就了明清时期书籍印刷出版的高峰期以及小说戏曲插图的黄金期,那么西方石印技术的引进则掀起了晚清以《点石斋画报》和“绣像小说”为代表的新一轮印刷出版高潮,使得以“图像”解说“晚清”成为可能。其实,无论是《点石斋画报》还是“绣像小说”,都把“图像证史”诠释得淋漓尽致,郑振铎把前者称为“中国近百年很好的‘画史’”可见一斑。无论是其中的“图”还是“文”,无疑都在“见证”着晚清这段特殊的历史,无疑都在以图像的形式表达着对时事的关注和时弊的针砭。这样,图与文、时与史、时与世等,都在图像批评中走向互文互补、共生共融。
中国古代图像批评的传统不止停留于此,还极大地渗透和影响着后世的文学批评,最典型的莫过于“以图入世”的新文学封面和插图。陈思和先生认为,现代出版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13〕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封面和插图便成为中国图像批评传统中又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新文学观念的一种图像性表达。像鲁迅《呐喊》封面中的红黑色调、隶书字体与“铁屋子”造型,《野草》封面中的蓝白基调、线条变化、“口”字的化方为圆等,都极具匠心和用意,也颇见批评之锋芒。在新文学封面和插图中,图像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成,也融入了当时的文学批评潮流。其实,即便到了今天的图像时代、“超文本”时代,我们仍可以看到古代图像批评传统的传承与革新。
四
文学作品具有“文学性”。古代图像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形态,同样有着独特性的呈现方式、话语风格和表述习惯。“化语成图”的直观表现、“驻足凝视”的审美驿站、“象外之象”的意蕴空间,构成了图像批评“以象入意”的批评特性。
一是“化语成图”的直观表现。图像批评的特殊性在于图像媒介的特殊性,即直观性、形象性。语言是抽象的艺术、时间的艺术、流动的艺术,而图像则是形象的艺术、空间的艺术、定格的艺术。图像以其形象直观的外表吸引读者注意,召唤着读者进入其内部艺术世界。恰如鲁迅先生所说,“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8〕(p28)其实,无论是明清插图还是晚清画报,不仅具有“以象取意”的外在吸引力和感召力,更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震撼力。图像批评是以图像形式展开的特殊批评,它构成了“另一种讲述的方式”:“试图抛开文字,任影像的歧义性发挥作用,使观众获得更大的阐释空间。”〔14〕
二是“驻足凝视”的审美驿站。如果说语言叙事和文字批评是“流水线”,情节、故事、冲突、观点等在时间的线性推进中不断向前发展;那么图像叙事和图像批评则是“观景台”,批评者用形象、色彩、构图等建构一个形式空间和意象世界,读者则可以驻足游览、凝视远望、浮想联翩,走进静谧安详的心灵空间和意义世界。颇有意味的是,图像批评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往往带有“预设读者”或“内在观者”的色彩。中国图像批评传统中的诗意画、文学插图、文学封面等图像形式,始终给此后的读者留下了充分的解读空间,尤其是图像所惯用的俯视视角让人感觉到始终是故意预留的,观者无需调整视角便可直接进入图像解读,图像之眼让位于观者之眼,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主体的视界转换。比如,古代戏曲插图的“观察者”所处位置十分特殊,即“观察者”是站在“表演者”的身旁默默观看的,“这一视角取消了舞台的框架作用和观众通常的远视或仰视的视角,为传播营造了一个近观体验的图像感知空间”。这种状态“使叙事层人物之间形成众多‘看’与‘被看’的流动视角”,从而使叙事传播主体具有“神灵附体般”的观察体验能力。〔15〕更有兴味的是,图像作者始终在以“内在评者”的形式隐匿起来,却不时地在读者阅文读图的过程中站出来与之对话,他以“画外音”的形式“发表”言论、进行评说,对读者进行提示、导引甚至劝说。而此时读者与“内在评者”之间既可能是认同关系也可能是差异关系,认同体现为诠释的一致性,差异则指向意义的分歧。无论是认同还是差异,都构成一种交往对话。正是在这种求同存异式的“对话”状态中,语图之间实现互文和互补。
三是“象外之象”的意义空间。图文本中的图像常常含有“言外之意”,这构成了图像批评的蕴藉性特征。如徐渭《墨葡萄图》,画的虽是葡萄,但画中题诗却充满了抑郁不平的激愤之情:“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笑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而他的另一幅作品《榴实图》中“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的题诗,字里画间则充溢着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慨。明刊本戏曲插图,也常常追求画外之意、弦外之音。比如,陈洪绶不仅为《新镌节义鸳鸯冢娇红记》绘制娇娘像,而且还亲笔题词:“青螺斜继玉搔头,却为伤春花带愁;前程策径多是恨,汪洋不泻泪中流。”从伤、愁、恨、泪等字眼以及娇娘像所呈现出的愁容不难看出,陈洪绶在娇娘身上不知贯注了多少个人感情与生命激情。恰如有的学者所云:“陈洪绶给‘西厢记’、‘鸳鸯冢’作插图,是他不满现实的另一面,体现出他对礼教反抗者寄予深切的同情。”〔16〕显然,这些都是溢于画面之外的,是象外之象的意蕴空间。以“象外之象”追求“言外之意”,是图像批评的深层境界。
应该看到,“图像批评”的两重意指并不完全冲突,它们都是围绕图像而进行的批评,图像的“图像性”是其共同的问题域。随着“语像时代”(an age of iconography)〔1〕的来临,“图像批评”的上述两重意指必将形成新的互文,成为又一个向度上的“共在”,因为“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17〕。
〔1〕王宁.当代文化批评语境中的“图像转折”〔J〕.厦门大学学报,2007,(1):14 -21.
〔2〕陈平原.看图说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
〔3〕马孟晶.耳目之玩——从《西厢记》版画插图论晚明出版文化对视觉性之关注〔A〕.颜娟英.美术与考古〔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643.
〔4〕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574.
〔5〕转引自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79.
〔6〕彼得·伯克.图像证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
〔7〕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7.
〔8〕鲁迅全集:第6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82.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郭豫适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05.
〔11〕万方.封面书影介绍——绣像小说〔J〕.书屋,2002,(2).
〔12〕张建业.李贽全集注:第一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72.
〔13〕陈思和.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44 -49.
〔14〕约翰·伯格、让·摩尔.另一种讲述的方式〔M〕.沈语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75.
〔15〕于德山.中国图像叙述传播〔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206 -233.
〔16〕黄湧泉.陈洪绶年谱〔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177.
〔17〕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