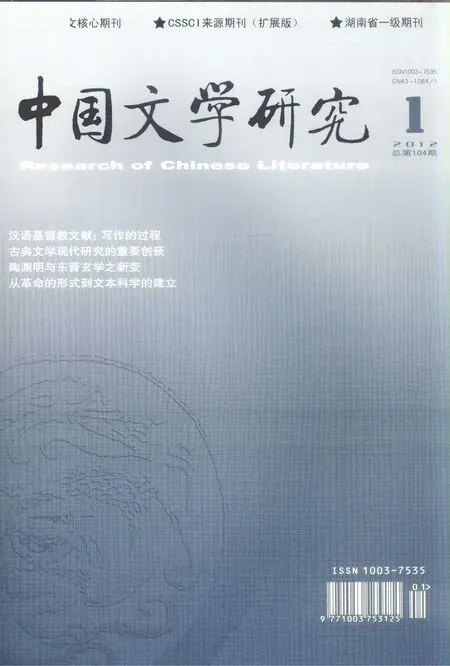苏辛农村词比较
杨 茜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北宋时的“词坛革新家”苏轼以其在徐州任上所作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组词真正开启了农村词创作的序幕,扩大了词的堂庑。苏轼对农村风物的描写还散见于《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望江南·暮春》(春已老)、《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惭愧今年二月丰)等约十首词中。而南宋时的辛弃疾则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革新作风,在投闲置散于江西上饶带湖与铅山瓢泉时也创作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词作十二首如《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春入平原荠菜花),另有散句见于其他十余首词中。
苏轼与辛弃疾均为才华横溢但仕途偃蹇、人生坎坷之人,但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与个人性情、遭际等的差异,他们的农村词也体现出不同的况味,也有少量的相似之处。
一、苏轼常以关心民瘼的地方官之眼看农村,辛弃疾则作为失意英雄从农村中得到慰藉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春,徐州大旱,身为一州长官的苏轼曾前往石潭求雨,得雨解除旱象后,苏轼又赴城外谢雨,他在返途中将沿途见闻尽收笔底,写下了《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组词五首,这是一组真正有意识地叙写农村的组词,为词苑从此开辟了一片崭新的疆土。以该组词其三为例: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阕写的是求雨得雨后的田园风光和村里煮茧的农事活动,下阕中,词人看见拄着藜杖的白发老翁抬起昏花的老眼,将捋下后炒干的新麦捣成粉末聊充饥肠,他忍不住要问一句:“豆类作物要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以便帮助农民度过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一句简单的问询语短情长,朴素动人,与词人在《徐州祈雨青词》中“望二麦之一登,救饥民于垂死”〔1〕的呼吁是一致的,将作为一州之长的词人对民生疾苦的关切之情表露无遗;写于同年夏天的《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的“惭愧今年二麦丰。千畦细浪舞晴空”则欣喜难得今年大小麦将获丰收;写于元丰四年(1081)十二月二日的《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叙述黄州冬日覆盖着的田畦因旱而未返青,作于次日的《浣溪沙·再和前韵》(半夜银山上积苏)说“湿薪如桂米如珠”;以及同为次日作的《浣溪沙·前韵》(万顷风涛不记苏)中想象“雪晴江上麦千车”,诉说“但令人饱我愁无”,只要百姓吃饱,我也便没有什么忧愁了,表现出如同杜甫般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崇高的忧民思想境界。
淳熙八年(1181)年冬,辛弃疾被人罗织罪名弹劾罢官落职,只好退居上饶城郊的带湖住至1192年,1194年辛弃疾因在福州知州及福建路安抚使上的改革弊政的举措又招既得利益者的嫉恨再度得罪被罢职,之后不久徙居铅山瓢泉,再续其退隐农村的岁月至1202年。辛弃疾曾在上饶和铅山的农村居住共计18年,与苏轼相比,辛弃疾并非以地方官的身份偶尔到农村“走马观花”,而是作为被劾罢职的失意英雄长居农村,与农民也有着更多更亲密的交往,因此辛弃疾创作的农村词在数量上当然也要比苏轼的多,“个中人”的气息也更浓烈,并常在此类词中表现出自己归隐田园的闲适。
《水调歌头·和郑舜举蔗庵韵》(万事到白发)中的“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极写农村风物之美与民风之淳,继而感叹:“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辛弃疾深深体味到农村的“闲意态,细生涯,牛栏西畔有桑麻”(《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农村单纯而平凡的生活情调,男耕女织的生活令词人感动与沉醉;再如《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着意寻春懒便回)的下阕:“携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开”颇有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的意味;还有《鹧鸪天·戏题村舍》(鸡鸭成群晚未收)中的“有何不可吾方羡,要底都无饱便休”,他说处于鸡鸭成群、桑麻茂盛的生活环境中有什么不好呢?只要能得一饱,别的也便不用营求,简单的两句对乡村生活的评述可让人领略到词人对复杂官场生活的否定及对古朴自足的农家生活的向往;《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连云松竹)全词为:“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在此词中的辛弃疾不复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英雄,而是一位融入古朴农村的生活圈中的一位“万事从今足”的“分社肉”、酿白酒、于静处闲看儿童偷把长竿偷枣的“老夫”。偶及农村的苏轼只能感受到“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四),而长居农村的辛弃疾当然就能一饱顽童偷打梨枣眼福。
但是要指出的是,卜居田园的辛弃疾也并非能一味忘世,辛弃疾的闲适中有不得已的意味,因为他是一直痛心于“却将万字平戎策,换成东家(邻?)种树书”(《鹧鸪天》)的。辛弃疾闲居农村时经常携酒出游或出门不久即欲寻找青帘(即酒招,亦称青旗)饮酒,如《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春入平原荠菜花)中的“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着意寻春懒便回)中的“着意寻春懒便回,何如信步两三杯?”,《鹊桥仙·己酉山行书所见》(松冈避暑)中的“松岗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醉扶怪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女)中的“醉中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住处”,读者读辛弃疾的农村词不难想象一个失路闲居农村的老英雄的闲适,这闲适中有真闲适的成分,但也有无奈甚至苦涩的成分,比如约1187年作于带湖的《江神子·和人韵》(梨花着雨晚来晴)就是一首丝毫不加掩饰发愤抒情的词作,抒发了心中郁积的深哀巨痛。其上阕云:“月胧明,泪纵横”,作为一个曾驰骋战场、出生入死的铮铮铁汉,伤心极处他不能不热泪纵横,下阕说:“酒兵昨夜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写尽胸中,块垒未全平。”前人都道酒可消愁,如那位狂士阮籍全靠酒来浇灭胸中块垒,可我昨夜以“酒兵”攻“愁城”,却不但没有取胜,反而更加狂态毕露,对现状更加牵情,我只好用笔来宣泄愁烦,即使这样胸中块垒也未全消。该词可谓字字血泪。但不管怎么说,辛弃疾用他的词笔抒写了一个平静祥和的农村,这个农村虽不是世外桃源,但还是能给人以闲适欢悦之情的,农村给辛弃疾这个不得已长居农村的人提供了宁静的精神家园,给他以莫大的慰藉。
二、苏轼的农村词常直书所见、感性直观,辛弃疾的农村词则蕴意更深、含更多理性思考
如苏轼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一上阕:“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藏晚乌。黄童白叟聚睢盱”。短短三句写了晚照下潭水中浮现的游鱼,归巢的乌鸦在浓荫中啼鸣却不见其踪,村民从黄发至垂髫均欢乐无比,“红”、“绿”、“黄”、“白”等色彩字的运用使这首词色泽鲜明,充满活力,也强化了喜庆的热烈氛围。再如这组词的其二:“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蒨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词中写了村姑们匆匆忙忙打扮一番看太守,村民们为感谢上天降雨举行的社祭活动(麦社),祭品引来乌鸦和老鹰盘旋不去,更增加赛神热烈的气氛。路上词人还看见一位老叟醉卧道旁,老叟因何而醉词人不曾明说,但读者自可领略,全词以多个镜头拼接起了一幅“使君与民同乐图”。苏轼的农村词就这样具体可感,读来流畅恣肆、明白如话,无需作太多的深究与猜测。
辛弃疾的农村词中包含更多的蕴意及议论色彩、更多的理性。如《鹧鸪天·代人赋》(陌上柔桑破嫩芽)的末尾:“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初春溪头铺陈的白色荠菜花不畏风雨,已然开放,而此时城中的桃李因畏怯风雨还不曾开呢。词人以桃李与荠菜花这样能兴起读者联想的花儿的神采作对照,然后对读者说出他的感悟:春天是属于生命力勃发的溪头荠菜花的!“春在溪头荠菜花”毋庸置疑地掷地有声,闪烁着一种理性的光芒,清代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说,词之结尾有三种情况:“辞意俱尽,辞尽意不尽,意尽辞不尽”〔2〕,此词结尾便深得“辞尽意不尽”之妙;《鹧鸪天·戏题村舍》(鸡鸭成群晚未收)中的“有何不可吾方羡,要底都无饱便休”也有显见的议论色彩;《满江红·山居即事》(几个轻鸥)中劝慰自己:“若要足时今足矣,以为足时何时足?”同样具有自我说法的理性精神;另有《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柳边飞鞚)云:“宿鹭窥沙孤影动,应有鱼虾入梦”,这两句说夜晚博山道中有睡眠中的白鹭头对泥沙晃动身子,词人猜测是因它在梦里捉鱼虾而睡不安稳。词人对宿鹭观察细致,叙写其情态又涉笔成趣,读者则可将“应有鱼虾入梦”理解为辛弃疾对那些热心名利之人即使梦寐也不忘得失的讥讽。因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3〕(清谭献《复堂词录序》)。
苏轼农村词之感性特色与辛弃疾农村词常包含理性、议论色彩的原因首先是二人所处时代环境不同所致。苏轼所处之北宋虽然积贫积弱,但总的说来还是承平无事的。而辛弃疾出生之时,他的出生地山东便已沦陷于金人之手13年,辛弃疾在23岁时满腔热情地归南宋,希望能实现自己北伐中原、统一祖国的远大政治理想,却毕生不能如愿,还被弹劾投闲置散农村18年,他的心中,实在是郁积着太多的不平与遗憾。正如清代词论家黄梨庄所云:“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4〕因此即使是写恬静的乡村词,辛弃疾往往也会不自觉地或隐或显地袒露自己的郁怀,发一些议论,或自我解嘲自己失意于当世的处境,如《鹧鸪天·鹅湖寺道中》(一榻清风殿影凉)中的“倦途却被行人笑,只为林泉有底忙?”自嘲如今只能为林泉奔忙(却不能为更值得去忙碌的事业奔忙)。
另外辛弃疾的长居农村当然比及苏轼的偶到农村有更多余暇去观察、体味乡村风物,因而也便能发现更多的东西,如:“松共竹,翠成堆,要擎残雪斗疏梅。乱鸦毕竟无才思,时把琼瑶蹴下来”(《鹧鸪天·黄沙道中即事》),赋予松竹以人的气概与情趣,松竹携手与梅斗靓,偏有“无才思”乱鸦将这场“美丽赛事”扰乱,对“煞风景”的乱鸦的“批评”实在是奇思妙想,涉笔成趣。
三、辛弃疾农村词的意象较苏轼的丰富
以自然界之花意象而言,辛词中虽无苏词中的枣花,但却有荠菜花、梨花、朱朱粉粉的野蒿花、还有稻花;苏轼走马农村时只瞥见农家的棘篱门,常信步出游的辛弃疾则看见茅檐低小、旧时茅店、古庙;苏轼听见的唯有鹁鸪的鸣声,辛弃疾则除听见千章云木里鉤辀(鹧鸪)叫外,还有平冈细草里黄犊的鸣声、听取蛙声一片、鸣禽枝上语、宿麦畦中雉鷕的叫声;苏轼的农村词中不曾叙写过乡村的夜晚,辛弃疾的词中则记录了夜行所见的宿鹭、夜空中的明月疏星、明月下的惊鹊、清风半夜的蝉鸣;以人物意象而言,苏轼的农村词里有黄童白叟、醉叟、“旋抹红妆看使君”的村姑、卖黄瓜者、“山中友”,苏轼虽也描绘渔父形象,描绘渔父的饮、醉、醒、笑(《渔父》四首),但令人感受更多的是东坡笔下“一笑人间千古”的渔父太多他自己的身影,具有较多的浪漫主义色彩;辛词中的人物意象则更加具体、真实、鲜明可感,有明月疏星下娉婷的浣纱少妇、青裙缟袂看外家的女子、寒食归宁女、偷把长竿打枣的儿童、扶他入东园吃枇杷的野老、准备好玉友、溪毛苦邀他小饮的野老、卖瓜人、踏水灌田的农人、醉瓜庐行秧马的老农,当然,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还是在那首《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中:“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俞平伯曾云此词:“虽似用口语写实,但大儿、中儿、小儿云云,盖从汉乐府《相逢行》:‘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化出,只易三女为三男耳。”〔5〕
不过无论如何,这首词是一幅清新令人赏心悦目的农家素描。用软媚吴音互相逗乐的白发翁媪、锄豆的大儿、织鸡笼的中儿、还有卧在溪头剥莲蓬吃的最天真无邪的可爱小儿已经定格于永恒的乡村词人物画廊。而如果没有辛弃疾对农村生活的细致观察与信手天成的手笔,这首《清平乐·村居》不可能几近千载以来一直强烈吸引着我们。辛弃疾的农村词中还经常出现“酒”或与酒有关的意象,如青帘,这在苏词中是少见的,这是因为辛弃疾被迫投闲置散的处境使得他常借酒消愁,“细读《离骚》还痛饮”(《满江红·山居即事》),也常携酒出门游览,不曾带酒时就欲觅青帘。
四、苏轼的农村词善用比喻,辛弃疾则常用白描
苏轼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组词其一中道:“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把未见过世面、老实巴交的村民比喻成“麋鹿”,说他们看见官员不免有几分“未惯”,活泼好动的儿童则被喻为“猿猱”,说儿童一听见祭神仪式的鼓声便雀跃赶来;组词其五中的“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雨后日光照于桑麻,其色光泽鲜亮如“泼”,和风送来的蒿艾之气如“薰”;《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惭愧今年二麦丰)中的“千畦细浪舞晴空”说广袤的田野上,麦浪滚滚好像是在晴朗的天空下翩翩起舞;另有《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中的“江南云叶暗随车”,江南在此处代指黄州,像云一样的枯叶悄悄地在车轮下飘着;《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中的“照水红蕖细细香”说荷花宛如美女,以水为镜,顾影自怜。
辛弃疾常用白描手法写农村人物和景致。“浣纱人影”不过“娉婷”而已,“看外家”的“谁家女”着的是“青裙缟袂”,“翁媪”“白发”,写“禾罢稏”、“稻花”,徒香而已,野蒿不过是“朱朱粉粉”的,不似去年发愁的“父老”只不过“眉头不似去年颦”;苏轼笔下的卖黄瓜者着牛衣于古柳下,辛弃疾则干净利落地说“卖瓜人过竹边村”(《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对卖瓜人是一点儿修饰语也没有。但不是说白描手法就淡而无味了,辛弃疾的白描手法没有任何渲染与夸张,但却能敏锐地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比如“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二句写出了回娘家探亲的农家少妇的装束是朴素的黑裙白衣,她回娘家的时间选在趁蚕出生前的空隙,与苏轼笔下“旋抹红妆看使君、“相挨踏破蒨罗裙”的村姑大异其趣;辛弃疾写“茅檐低小”,“低”、“小”区区二字就把握传达出贫穷农家房屋的特征,预示丰年的不是苏轼笔下“舞晴空”的千畦麦浪,而是作者夜行黄沙道中“听取蛙声一片”后知道稻田水分充足,感到了丰年的临近,且这个推论又从稻花的浓郁香味里得到证实。苏轼的形象比喻与辛弃疾深厚的白描功力均为叙写农村词之利器,这两种手法的使用并无优劣之分。
此外辛弃疾的词中更多地写及与农民的交往,这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辛弃疾有18年远离污浊的官场,尽日与淳朴的农民接触,与农民有着真挚的感情。因此农家顽童到他的私人山庄“梨枣山园”“偷把长竿”时,辛弃疾不恼不怒,反而以祈祷的口吻说:“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透露出对偷枣儿童的爱怜之情,当然还有他自己的一片童心;痛饮醉酒后“被野老、相扶入东园,枇杷熟”(《满江红·山居即事》);在《鹧鸪天》(石壁虚云积渐高)中,只有微薄酒蔬可荐的殷勤野老还拄着藜杖到桥头来接词人去家中做客,凡此种种,都向我们揭示了词人与村民的良好关系,生活优裕闲适的辛弃疾也会倾听农民诉说丰收的欢乐:“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如果他与父老的关系不亲近,父老怎么会争相向他诉说雨水丰匀之喜呢?
辛弃疾的农村词中有化用苏轼诗词、受苏轼影响的痕迹。如《唐河传·效花间体》(春水)中的“春水,千里,孤舟浪起”化用苏轼《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诗:“桃花春涨孤舟起”;“一榻清风殿影凉”化用苏轼的《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清风一榻抵千金”;“青裙缟袂谁家女”化用苏轼《於潜女》诗:“青裙缟袂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携竹杖,更芒鞋”语本苏轼《定风波》词:“竹杖芒鞋轻胜马”;“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明显受到苏轼词《望江南·暮春》中“百舌无言桃李尽,柘林深处鹁鸪鸣。春色属芜菁”的启发;“明月别枝惊鹊”化用苏轼《次韵蒋颖叔》诗:“月明惊鹊未安枝”;但辛弃疾在《满江红·山居即事》(几个轻鸥)中说:“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就比苏轼《绿筠轩》诗意更推进一层,该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辛弃疾则谓赏竹与食肉两不相碍,不仅表现出他比苏轼更为达观,也反映了他当时闲适、有“竹”有“肉”的生活。
辛弃疾在清新活泼、充满泥土气息的农村词中也能得心应手地化用苏轼及他人的诗词文赋、并能任意驱遣经史子集,实在是因他胸中有异常渊博的文史哲知识及他作词的大手笔所致,这一切也使得他的农村词简洁而不单调,“横竖烂漫”(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当然,苏轼与辛弃疾的农村词也有些许共同之处。他们的农村词均留存了当时的民俗民风。如苏轼的《蝶恋花·密州上元》录写密州元宵节乡村“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的祭祀活动;《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二中的“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麦社是农家祈雨谢神的社祭活动,赛神是古时一种迷信礼俗,用仪仗、鼓乐、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也叫迎神赛会;另外该组词其三中说:“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根据俞平伯先生的解释:“从前江南养蚕的人家禁忌迷信很多,如蚕时不得到别家串门,这里言女郎隔着篱笆说话,殆此风宋时已然。”(《唐宋词选释》)苏轼也许是在不经意之间,又为我们绘出了一幅风俗画;还有《满庭芳》(归去来兮)中的“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社酒为古代农村风俗,春、秋社神的节日,邻里是要聚会饮酒的,社酒之上加以“鸡豚”二字,又活画出一幅民风淳朴的乡村风俗画。而辛弃疾的“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也叙写祭土地神之社日,四邻集会备牲祭神毕各家分飨其肉,并要饮酒的风俗;“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叙写已出嫁的农家女儿在寒食节回娘家探望父母归来;“自言此地生儿女,不嫁余家即聘周”(《鹧鸪天·戏题村舍》)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古朴单纯小村庄的风俗人情。
苏辛的农村词总体看来是对农村的“赞歌”。他们笔下的农村美好恬静,农民淳朴友好。虽不像范成大、陆游等人那样在农村诗作中暴露社会矛盾、反映农民所受的阶级剥削与压迫,但他们笔下之祥和农村确是他们对农村褒扬之情的真实流露,可说是苏辛肯定农村胜于官场的思想在词作中的反映,并无损于他们农村词的审美价值。
〔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03.
〔2〕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4051.
〔3〕王运熙.中国文论选:近代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325.
〔4〕徐釚.词苑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8:92.
〔5〕俞平伯.唐宋词选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