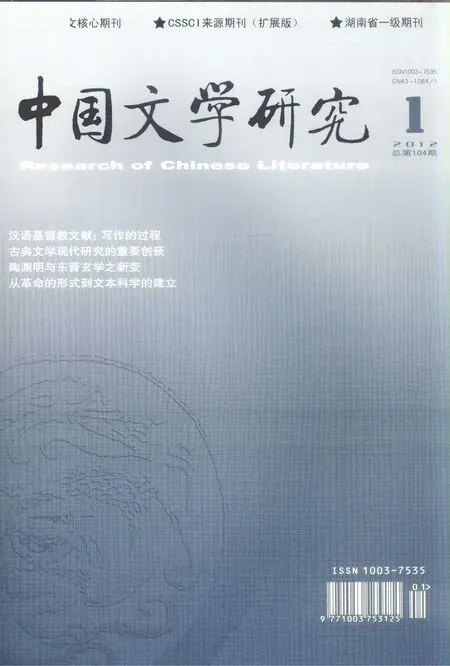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小资”村上与中国大众文化语境
刘 研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文坛正值沉寂期,村上春树横空出世,他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创作中斩获众多文学奖项,近年还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2009年推出的《1Q84》再掀畅销热潮。村上作为日本当代文学、文化转型期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创作、翻译、理论阐述极其复杂,可谓对以往的文学批评范式、包括文学自身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究其实质,村上紧扣时代脉搏,运用各种流行文化样式讲述别具一格的后现代故事。有研究者评价说:“对于我们这些执著寻找纯文学之根的读者,对于那种纯文学的崇拜者而言,拥有异教意味的、通俗小说肉体的春树小说与我们所期待的‘文学’截然不同。”〔1〕同时村上积极寻求与读者的“物语的共谋”〔2〕,正是村上文学的这种“存在”姿态,不同年龄、职业、区域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需求和取向,都可以“重写”文本,使得自己由一个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生产者。所以既有读者将村上文学视为恋爱、冒险、侦探等大众通俗小说,也有众多文学研究者对之展开深入的学理批评。总之阐释多元,受众广泛。
在中国大陆,村上文学因是“小资”的代言而畅销,同时也为中国“小资”提供了精神滋养。因此,“村上春树现象”在中国的接受不仅仅是文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本文将由此出发,考察新世纪以来10年间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中文本意义的变异——“小资”村上的生成原因与过程,从中剖析“小资”村上与中国大众文化独特诉求的内在关联,以及由此引发的“小资”村上对村上文学的误读。
一、媒介文化语境中“小资”村上的生成
村上春树的作品迄今为止被译成四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村上春树现象”被视为消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普遍性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继港台之后登陆中国大陆。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市场化、都市化发展迅猛,社会阶层重新分化重组,大学持续扩招,教育走向大众化,在此社会背景下作为西方新中产阶级的代表“白领”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语汇。虽然中国还远非“中产阶级社会”,也未形成典型的“中产阶级”,西方式“白领”阶层的人数所占比例极小,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收入稳定的都市年轻人对这一阶层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消费品位的向往。于是就有了中国大众文化的特产——“小资”。“小资”们通过自主劳动,尽管经济收入有限,还远达不到中产阶层,但又能保障自己过上相对充裕的物质生活,而较高的文化素质又决定了他们格外重视精神层面上的个性与自我认同。“小资”作为中国的特产被认为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方面:“首先是生活的品味和文化的情趣;其次是向往浪漫,这是一种都市化的浪漫;最后既然是一种情调,一种心境,体现的是文化品味,进而也可以与金钱无关,上则中资、大资,下则平头百姓,都可以包括进来。”〔3〕(P123)
恰值“小资”蓬勃兴起之际,村上文学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中国都市被置于全球化消费语境,文化产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国内出版机制纷纷转型,出版界开始注重图书的市场价值。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界力推通俗文学以迎合读者趣味,占据图书市场。于是,漓江出版社和北方文艺出版社分别于89、90年推出了按低俗色情模式打造的《挪威的森林》中译本,但并不畅销,也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出版社随即改变了营销策略,以畅销书的模式打造市场,逐步形成了研究读者——沟通作者——精心制作——全力营销的策略。不久,漓江出版社推出了“村上春树精品集”五卷本,不仅装帧素雅别致,而且林少华的译本也脱颖而出,这一转换成为迅速向“小资”渗透的重要保障。漓江版的定位为后来译文版针对特定读者阶层——“小资”的销售策略奠定了基础,也为译文版选定了译者——林少华。从2001年译文出版社出版村上系列文集开始,“村上”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鲜明印记的品牌。1999年至2005年中国大陆畅销书前十位排行榜中《挪威的森林》仅次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位居第二位,仅《挪威的森林》从2001年2月到2002年6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已印刷12次,印数高达52.17万册,《读者》、《女友》等时尚杂志频频出现村上春树的名字。
不仅如此,村上文学的流行还与互联网紧密相连,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关于村上文学的文章和链接,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和消费特性使村上文学迅速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百度使用关键词“村上春树”搜索,找到相关网页约4,550,000篇。国内众多知名书评网站都设有村上春树的专门板块,有关村上春树的主题网站也较多,如村上春树的森林论坛、西祠胡同的村上春树、豆瓣·村上春树的网络森林小组、百度村上春树吧等。百度村上春树吧截止到2011年7月18日,村民2428人,百度挪威的森林吧截止到2011年7月18日,“森林旅者”1867人。天涯在线书库、“村上春树的森林”论坛等都可以网上自由阅读和下载村上的中文电子书。“在豆瓣搜索《挪威的森林》共25条结果,包括相关的书籍、电影和音乐。其中在2003年上海译文版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畅销现象研究的《挪威的森林》条目下统计显示共107766人读过该书,2798人在读,12233人想读,共69831人参与评论此书,其中‘力荐’的占27.9%,‘推荐’的占43.3%,‘还行’的占26.1%,并有975篇书评。而相比较之下,另一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雪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仅仅有2818人评价过,相关评价也仅仅只有60条。再以天涯网站闲闲书话板块的搜索数据为例,亦可反映村上春树的‘号召力’:以关键词‘村上春树’搜索共112条主题帖,搜索‘挪威的森林’共90条主题帖;搜索‘川端康成’仅27条主题帖;而搜索‘菲茨杰拉德’——他给村上春树创作带来极大影响——的主题帖只有22条。”〔4〕
虽然网络的世界是虚拟的,但它生成的力量却是无比现实的,甚至会改变现实。很多读者在互联网上交流读书心得,并形成了数量众多、持久稳定的村上粉丝。“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香波的气味,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成为众多村上春树网站、网页的导语。粉丝们纷纷在网上留言,热烈讨论村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小说中涉及的美食佳酿、音乐电影、服装配饰,尤其是村上主人公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粉丝们热烈跟帖、对话,对村上文学做出自己的评说,这种评说又是在相互启发与讨论中形成的。所以他们不仅运用村上文学进行再生产,而且还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持久的社群文化。一时之间“村上春树”的名字被视为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象征性存在,是否阅读过村上文学成为“小资”的认证资格。而中国大陆的“村上春树热”与“今日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小资’”〔3〕(P122)就此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挪威的森林》更是被“小资”们视为圣经。由此可见,互联网促成了“小资’村上的生成,而村上文本也在互联网中获得了各种新的阐发。
由于网上成为热点,因而收集村上小说中的音乐曲目、美食的“宝典”、宣扬所谓“村上式”的生活方式的书籍也随之纷纷出版,如稻草人编著的《遇见100%的村上春树》认为村上在展现现代人在高度消费社会中的孤独与无奈的同时提供给了都市小人物一种不失品位与尊严的生活情调,书中不仅将村上和中译本的两位译者(大陆林少华、台湾赖明珠)塑造成了这种生活情调和处世哲学的实践者,并具体介绍和指导如何实践这种生活方式。苏静、江江编著的《嗨,村上春树》以散淡优美的文字述说着对村上春树作品的自发或自觉的感悟和评说,并声称“村上春树的文字已经写进了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里”〔5〕。
2009年村上新作《1Q84》再次引爆畅销热潮,仅在中国大陆,第一版印刷发行130万册。是《1Q84》自身的文学价值?还是“村上热”在中国经久不衰?也许这两者原因均有,但显然并非是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村上”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品牌效应。
《1Q84》是村上沉寂数年之后再出发的新作,中文版完全依据畅销书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从宣传、发行、营销,体现了一系列成熟的市场化的运作,成功引导了大众文化消费。就营销策略而言,《1Q84》中译先是炒掉了老东家上海译文,夺标的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更是出人意料地换掉了村上的“御用”译者林少华,改用只译过一本村上自传的施小炜。林译、施译孰优孰劣,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新经典还舍重金为这部图书拍摄户外广告,这样的图书宣传力度在世界图书营销中也是很少见的。〔6〕译者为什么大胆换掉深入人心的林少华,出版社宣传说是要还原真正的村上,除却炒作因素,其主要原因是,卖点在“那是村上的作品”,村上写得好坏与否,译者译得好坏与否,都关系不大了,这就是品牌效应。
“小资”村上创造的“媒体神话”、“受众神话”造就了中国大陆的“村上春树现象”。质言之,“小资”村上的生成既是时代历史的产物,又印证了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中传播媒介的重要功能。村上文学不仅在互联网的语境中得到了重新阐发,而且也在此语境中获得了理解和发展定位,并进一步在传统媒介中夺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二、“小资”村上与中国大众文化的独特诉求
众所周知,文化产品的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随着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的畅销,我们越发关注是“谁”“生产”了一个怎样的“村上”,或者说成为“小资”的村上在哪些方面满足了中国大众文化的欲求呢?
首先,“小资”村上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生活方式的潮流之一,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最近五十年来产生了另一种趋势,即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7〕。村上的主人公们听着美国流行音乐,看着好莱坞的大片,乘着波音747,穿着品牌时装,享受着美味的咖啡以及精致的和式、西式餐点。这种全球化的表征或者说新的生活空间深深吸引着向往西方中产阶级生活的“小资”。一时之间,飘渺的音乐、星巴克的咖啡、世界各地的旅游、自我风格的时装、脱口而出的外语,都成为了“小资”的典型符号。
提到村上文学,就必然提到中译者林少华先生,他翻译了32卷的村上春树文集,被誉为“林家铺子掌柜”,也可谓是“小资”村上的始作俑者之一。换言之,中国大陆“小资”们追捧的是林译村上。林译及其解读从90年代到21世纪前5年在塑造“小资”村上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研究者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8〕译文版编辑沈维藩也曾表示:若干技术性误译可以接受,但属于文学性的则不能接受,“林译不能动,一动‘味’就变了。”这其中的“味”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近年随着对村上文学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林译多有诟病,认为他“在文脉的表层舍弃了原作中历史的、社会的前后关联,创造出一个强调情感与美的氛围的新文本”〔9〕。翻译中的错译、漏译我们在学理上当然要予以批评,但问题是林译绝不仅仅是翻译是否准确的问题,而是在中国大陆的现实语境中通过林译重新生产了村上文学。对林译的批评我们应该顾及林译流通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小资”所欣赏的那种恰到好处、刻意求雅的“味”只有林译。据此林译村上构成的话语才成为“小资”的文化资源之一,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文化语境选择了林译。当中国作家没有给“小资”提供这样范本的时候,是林译村上满足了中国读者的精神饥渴。如果将之置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流通中,林译令村上文学得以迅速传播,功不可没。
更为关键的是“小资”村上传达了一种人生体验和人生态度。林少华在《挪威的森林》“代译序”中说:“其实村上作品最能让我心动或引起共鸣的,乃是其提供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人生态度:把玩孤独,把玩无奈。”〔10〕三浦雅士在《村上春树和当今时代》中说,“无论是个人的资质,还是他的思想使然,村上总是将现代人对世界的疏离感作为小说的主题。这一主题也即是对于现实不能作为现实来把握之病,是不能与他者之心相沟通之病,同时这也是自己对自己不能实感之病,是关乎自我之病。同时这病还带来一种优雅,它浸润了村上的文体,形成轻快与暗郁的结合体,直接归结为主题。主题与文体是密切相关的。”〔11〕村上讲述的是都市青年男女的时代病:在现代大都市从事着时尚职业,光鲜生活的背后却有着一种无法摆脱的被格式化的宿命,内心深处时时在追问“我现在在哪里”、“我哪里也到达不了”,深陷于自我迷失的茫然状态。
村上创作《挪威的森林》的八十年代日本青年的生活状态与世纪之交的中国青年不无近似之处。中国大陆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高速运转,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消费文化迅速扩展,导致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组织、价值核心出现了一系列的剧变,意识形态出现了真空,价值观念迷失,社会个体出现了“失败、孤独、迷乱、空虚”等种种心理不适。面对诡谲奇异充满梦幻的都市世界,感觉细腻的“小资”们自然体验到了个体存在的精神危机:孤独、异化、无根、无奈、莫名的不安,期待解脱,期待找到心灵栖息地。村上文学恰逢其时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栖息地。
同时,村上的人物们在对青春的丧失与挫折的低吟浅唱中尽管憧憬什么较为模糊,但却保持了对“期待”的无比坚持的姿态,正是这种期待着却又无所归依的旋律的不断回响令众多村上迷们产生共鸣。“小资”村上突出的那种遗世独立的怀疑与拒绝,是对主导文化的不认同和挑战,但同时“小资”们又无比歆慕衣食不愁生活优雅的新富阶层,极力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在诗意盎然的生活中自我欣赏、自我满足。因此“小资”村上既“祛魅”,消解崇高,解构宏大叙事;同时又“复魅”,执意构想一个完美偶像,凸显自身的精英意识。“小资”们就此把生活方式演变成了一种对生活的谋划,演变成对自己个性和自我意识的确定。
我们知道,“大众”从来都是随着历史语境不断变迁的术语,在全球化大众文化的互动中,中国语境中的“大众”已经“不是革命话语中或革命史叙述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主流排斥或边缘化作为草根阶层的‘底层民众’,其确切所指应该是市场经济下世俗化日常生活中‘涌现’出的特定消费团体。……大众的涵义不断得到确指,并有力地配合了社会结构中一个中等收入为主的新富群体的崛起。”〔12〕这一群体显然在人数上是名副其实的“小众”,但因其占有社会中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是当今的“成功人士”,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甚至成为社会偶像,从精神追求和消费观上又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相对应,而中产阶级正是西方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在西方学术话语中,从“Mass culture”到“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这一术语背后纠结了庞大和繁杂的话语背景和理路走向。而当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旅行至中国的时候,西方话语层面的“大众”在中国语境中以这种“小众”的面目出现却具有影响“大众”的效能。因此“小资”就不单单是诗意的个体追求,更在实质上成为某一特定语境中普遍的和被倡导的价值取向。
由此一来,“小资”村上体现了文学作为商品和文化符号的双重地位,文本的意义在流通与消费中发生着变异。“小资”村上与其说是来自于村上文学的本质特征,莫不如说遵循的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内部逻辑,源自中国消费者的文化消费欲望。它是都市青年自我呈示、表达自身文化诉求、建构一个彼此倾诉、分享的文化空间的重要渠道,其中也蕴含着通过文化消费认同而获得某种话语权的渴望。
三、“小资”村上的错位阐释
一定意义上,“小资”村上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首先是一种人生意义丰富性的发现,村上文学为“小资”们提供了温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以一种都市思考者的姿态显示了“小资”们与庸众的不同,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作为社会区隔标记的优越感在里面。它意味着中国人摆脱政治束缚后走向了个性自由,也意味着在城市森林的挤压中自我心灵的坚守。这样的“发现”正如英国伯明翰学派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年轻消费者在挪用和转变文化制成品方面表现得异常积极和富有创造性。”〔13〕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小资”尽管生动,但仔细想来,却是异常单一和鲜明的,这个“村上”与村上丰富复杂的文本本身相去甚远,而且是去日本味、无国籍化的,也是一厢情愿的。“小资”村上令读者浸润其中,反照出自己的生存,如是而已,“在当前的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通网络而占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14〕如此一来“小资”们的生存姿态只是一场虚假的斗争,逡巡于心灵世界实质遮蔽的是个体面对巨大社会变迁产生的内在焦虑,或者说“村上”成为“小资”释放焦虑的一个无奈的出口。所以有研究者嗅出了“在当代人被官僚主义和消费社会日益‘片断化’的当下还存在着回避现实的危险”〔15〕,“小资”村上沉沦于感官体验、生活情调,沉湎于孤芳自赏,必然遮蔽了现实的苦难与残忍,实际上不仅很难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而且也谈不到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更难以为真正的“大众”代言。
随着村上文学地位在世界文坛的不断提升和研究的深入,仅将其视为一种时尚必然会遭到质疑。林少华对村上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如在《村上春树在中国——全球化和本土化进程中的村上春树》(《外国文学评论》2006/03)指出村上在诸多作品中对存在于日本社会与历史深处的“恶”进行了深刻而执着的揭露,因此强调应该“不再一味把他看成粉色情调的‘小资’作家”,并将村上塑造成了“东亚斗士”的形象,村上能否成为“斗士”另当别论,但正如《1Q84》的中译者施小炜所言,“把村上春树视为‘小资之父’是一场误会。”〔16〕
村上在其文学中确实深刻描绘了“高度资本主义社会”都市现代人的孤独与彷徨,但村上文学绝非仅此一点。他的创作被誉为“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17〕。他在创作中对日本“后战后”时期很多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如东西方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交融,在全球化和东亚区域化之间如何实现身份认同,在引起战争的那些基本要素至今仍未被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对待战争记忆,对“文学”概念如何反思等等。这些问题无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沉思考。
与“小资”村上执着于“自我”的当下体验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村上文学中一以贯之的历史意识。藤井省三指出:“日本自20世纪初以来,就有作家用文学来表达强烈的历史意识。一个是夏目漱石,漱石的历史意识是预感到了日本近代的终结。具体而言,他对日本从上海到朝鲜半岛的入侵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另一个就是村上春树,村上的历史意识则体现在从当代日本返回过去呈现‘历史的记忆’。”〔18〕村上从处女作《且听风吟》开始就潜在或显在地表现了战争记忆或者战争意识,八十年代的《寻羊冒险记》立足追究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进程中的罪恶史,并借人物之口指出:“构成日本近代的本质的愚劣性,就在于我们在同亚洲其他民族的交流当中没学到任何东西”〔19〕。九十年代,“对于‘战争’的日本社会‘封闭性’的‘恐惧’,成为贯穿《发条鸟年代记》的一条主线”〔20〕,2002年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文本深层中交织着作家对天皇制、靖国神社参拜、历史教科书等当代日本乃至整个世界所需要应对和面临的问题的思考,2009年的《1Q84》中则体现了作家对宗教、家庭暴力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的参与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浸淫于“小资”村上的读者们,不仅会忽略村上文学的丰富性,也很难自觉意识到村上文学的复杂性。任何一位作家都必然受到各自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特定心理的制约,许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是作家本人都很难意识到的,因此,村上的创作不但不是“脱国籍”的,而且是附着在自己的民族情境里的,尤其是他的消解一切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更值得中国读者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小森阳一认为《海边的卡夫卡》“采用了将读者一度唤醒的历史记忆从故事内部中割裂出去并加以消除的手法。这是一个对读者的记忆中的历史加以篡改,甚至是消匿历史记忆、使历史记忆最终归于一片虚空的方法”〔21〕,指出村上对读者实现精神“疗愈”的背后实则隐藏着抹杀历史、勾销记忆的话语结构。村上这种似乎“无国籍”的作品中的民族主义欲求,囿于日本民族主义式的历史认知,对暴力、恶充满悖论和宿命论的观点,以及电脑游戏般简单明了地在异界消除恶的方式,一般读者如果缺乏警醒,那么在消遣式的阅读中就很难觉察,并且非常容易在不知不觉地加以认同。这说明我们客观清醒的文学批评做得还很不够,也说明文学批评与大众阅读相距尚远。
随着大众文化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对象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也席卷而来,尤其是大众文化批判成为当今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焦点。中国大陆的“小资”生成,在世纪之交生动地为我们勾勒了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轨迹,为“大众文化”的本土化提供了多样的文化经验。尽管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流通不可能排斥商业化、娱乐化,但透过这一表征,小资“村上”是某种社会需求引发的文化现象,并且大众也以其独特的参与方式,通过话语的流通,实现了“再生产”。“小资”村上提醒我们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文学,简单的精英主义批评很容易造成阐释的错位,我们的批评既要关注生产者与文本,也要注重消费者与受众,我们要追问大众为何有如此需求,何为其需求的内在机理,以及这种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又是一种误读。只有在多维视角下做出价值评判,方能说明如“小资”村上者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意蕴,方能跨越西方理论的话语层面,真正形成直面中国当下的问题意识。
〔1〕〔日〕畑中佳樹.アメリカ文学と村上春樹〔C〕.栗平良樹、拓植光彦編.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ズ.01.東京:若草書房,1999.33.
〔2〕〔日〕村上春樹.村上春樹ロング·インタービュー「アフタ-ダ-ク」をめぐって〔J〕.文学界,2005(4):174.
〔3〕陆扬.大众文化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赵敏:《村上春树作品在大陆的畅销现象研究》〔EB/OL〕.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8-5:17.
〔5〕苏静 江江.嗨,村上春树〔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3.
〔6〕沈利娜.纯文学的迷途——村上春树<1Q84>中文版案例评述〔J〕.新观察,2010(10).
〔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35.
〔8〕王向远.日本文学汉译史.王向远著作集〔M〕.第三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350-351.
〔9〕孫軍悦.<誤訳>のなかの真理―中国における「ノルウェイの森」の翻訳と受容―〔J〕.日本近代文学,2004,(71):149.
〔10〕林少华,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代译序).挪威的森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
〔11〕〔日〕三浦雅士.村上春樹とこの時代の倫理〔C〕.群像 日本の作家26村上春樹.東京:小学館,1997.43.
〔12〕范玉刚.“大众”概念流动性与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文化研究,2011,(7):24.
〔13〕杨玲.西方消费理论视野中的粉丝文化研究〔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1,(7):56.
〔14〕〔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1997.497.
〔15〕王志松.翻译、解读与文化的越境——也谈“林译”村上文学〔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5):121.
〔16〕施小炜.把村上春树视为‘小资之父’是一场误会〔N〕.中国青年报.2010-6-22.
〔17〕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2。
〔18〕〔日〕藤井省三《グロ-バリゼ-ションなかの村上文学と日本表象》,国际交流基金《遠近》,2006年夏季号:162.
〔19〕〔日〕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01.
〔20〕〔日〕黑古一夫:《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秦刚王海蓝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7.
〔21〕〔日〕小森阳一.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78.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