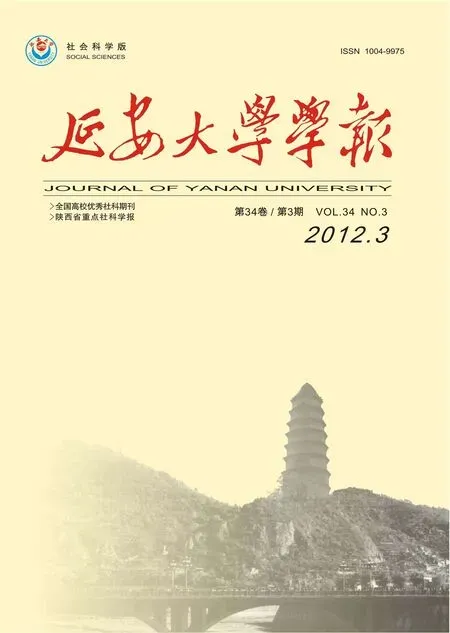工农兵文学服务途径论说
刘 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广西 柳州 545007)
文学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途径,是文学的两个最基本、最根本,同时也是世界上除无产阶级之外的各个阶级和利益集团,最不愿明说或者认为不必明说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却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列宁,他十分明确地说过: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1]166服务,这是指文学的服务对象而言;对于文学的服务途径,恩格斯则十分推崇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指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1]100同时,列宁也说过文艺“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1]162。不过,恩格斯还只是就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方法而论,并非专门地、直接地阐述无产阶级文学独特的服务途径问题,而列宁的“齿轮和螺丝钉”一说,还只能视作服务的原则,如果作为服务途径,却还显得不够具体和明确。
不只是对于服务对象,而且是对于服务途径,阐述得最为明确的还是毛泽东。他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倡导了工农兵文学,深入论述了工农兵文学的服务对象,而且还可以说更为深入地、具体地论述了工农兵文学的服务途径问题。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往往只注意他提出的文学(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即服务对象的问题,而忽略了他对于服务途径问题的重视。这样,也就影响了我们对于工农兵文学的深入理解。也就是因为这点,笔者才不揣冒昧,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所谓工农兵文学,笔者此前有“严格意义”和“非严格意义”之说[2],但其最基本、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以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为服务对象,直接描写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它同其他文学作品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它的思想和感情的底层民众性。由此出发,决定了它在服务途径、服务方式上,要彻底改变其他文学旧有的做法。下面,我们就这一问题试作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一、关于工农兵文学的服务途径
(一)变个人写作为阶级写作
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个人的灵感和体验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操作上的个人性。正因如此,所以文学创作其本质就是个人创作,这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本来是通过个人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去为其对象服务的。此前的文学创作,都是作家表现个人的社会、人生见解,通过潜意识的作用为所属的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检视一下中外文学史,在上世纪40年代工农兵文学出现之前,我们很难发现一部集体创作的文学作品。
然而这完完全全的个人性,往往表现出一种懒散型和飘忽性即不确定性,不能有力地形成强大的力量为某一阶级、集团服务,这样完全由个人写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不能有效地保证工农兵文学服务目的的实现。为此,毛泽东说:“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3]48,又说:”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3]49所以必须摒弃个人的写作,建立工农兵的写作队伍,变个人写作为工农兵的阶级写作。
这一队伍是怎样组成的呢?
一方面,是工农兵群众自己的业余创作队伍。和别的文论家甚至是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不同的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大众的写作,他说:“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3]92-93他批评一些人“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3]93,他还说:“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3]93这就是说,毛泽东把工农兵群众的业余作者看成是工农兵文学写作队伍的成员之一;另一方面,是专门的文学家队伍,这是工农兵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上面所说的是队伍的组成。毛泽东重视工农兵文学写作队伍的组织建设,但更重视队伍的思想建设。他一再强调文学家要同工农兵结合,要和他们在感情上打成一片。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感情不是工农兵个体的感情,而是工农兵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感情。毛泽东说;“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3]88还说:“专门家有责任指导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但并不是只有指导的责任”,“还要学习,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3]94这“养料”,主要就是指工农兵群众的阶级感情。这样,作为非工农兵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工农兵。所以,从本质上说,建立工农兵文学的写作队伍,就是借助政治的力量寻找工农兵的代言人,把非工农兵作家队伍改编为有共同写作主旨的工农兵自己的队伍。而且,这“队伍”中的成员,还要求思想、行动“一致”得像一个人一样。由此,文学创作上的个人在某一特定的意义上也就成了工农兵阶级,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写作,也就成了有组织的阶级的“集体”写作,而且在形式上,工农兵文学的确有不少具体创作的作品,以文革期间为甚。如此,文学创作的个人行动也就变成了阶级的具体行动。之后,又利用政治的力量,阶级的力量,使这支“文化军队”为工农兵即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战斗,从而从总体上实现工农兵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目的。
正因如此,所以工农兵文学突出地体现出阶级的共同性。也因此,会出现如此奇妙的现象:早、中期的工农兵文学,多人描写相同的题材,表现相同的主旨,如早期的《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同描写土地改革的过程,一同表现土改的政策和胜利;中期的《不能走那条路》、《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以及其他好些作品,一同描写农村合作化,一同表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更有大批不同题材的作品,如《保卫延安》、《苦斗》、《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岩》等等,一起宣传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都强有力地表现了工农兵文学阶级写作作为服务途径的有效性。
(二)变灵感写作为意识写作
传统的文学创作,都是源于作家个人的灵感触发,或者说,传统的文学创作,都是灵感写作。这种写作,突出的是灵感的突发性和机遇性,它产生的是作品的个人性和特异性,其个人风格是明显的。但是却又产生了随意性和不可把握性,即有可能“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3]59,这就很难保证工农兵文学目的的实现,即无法保证完全服务于既定的服务对象。所以工农兵文学不能沿着这条路子走。
毛泽东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3]49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3]64这就是说,工农兵文学作家是在熟悉和分析生活的基础上,带着工农兵阶级的思想意识进入创作过程的,并非依靠灵感,而是靠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指引去写作的,这就把灵感写作变成了意识写作。从工农兵文学的创作实践看,那些描写同一题材的作品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洋铁桶的故事》、《敌后武工队》;《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都不是靠个人的灵感触发而创作,而是凭党的指引去创作的。赵树理就说过:“写《三里湾》时,我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就写了这篇小说。”[4]282而“刚一解放,周立波通过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受到启发,一进城,就想了解和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业建设’。”[4]319从而创作长篇小说《铁水奔流》;还有李准也说过:“在写这些小故事(指他的短篇小说——笔者)时,我总是想:‘如果有人能给农民们谈谈就好了’。我的目的就是这样:能够让农民们听听,笑一笑,从笑声中来摆脱他们的落后,从笑声中认识到什么是先进。”[5]282这些都是思想触发创作冲动的最好佐证。就是那些不同题材的作品,如《红日》、《风雪之夜》……,可以说凡是工农兵文学作品,都是由阶级的意识作为创作的出发点的。虽然作家个人有风格的不同,如《荷花淀》、《新儿女英雄传》、《苦斗》、《青春之歌》,但这主要表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主旨、意蕴上(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风格的差别是有限的,因为真正意义的风格差别,表现在题材、意蕴以及表现形式等多方面),笔者曾经把创作动因分为思想动因和情感动因两大类[6],而工农兵文学均属于思想动因,是思想因由文学,它们是由同一的思想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触发而进入创作过程的。这样,工农兵文学也就完全成了表现工农兵思想意识而不是表达作家个人情感的文学,实实在在成了工农兵阶级的传声筒。
(三)变个人掌控为机制保障
传统的写作,其整个写作过程,包括构思,写作、修改、发表(出版),都凭作家自己的主观意图进行,都是个人可以掌控的行为,表现出完全的自主性。而工农兵文学,为了服务于工农兵的革命事业,上述一切都不能由作家自己决定,也就是说,工农兵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建立了一套保障机制。这机制包括对写作进程的规范:写作之前下农村、下工厂、下部队体验生活,学习党的相关政策,然后进入构思、写作的阶段,继而修改、出版、也包括每一进程的审批、推荐的权限和程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正因如此,所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审阅过肖三、欧阳山、艾青等许多作家的作品[3]253-338,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也是在彭德怀的推荐下发表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根据领导的意见经过修改后才出版的。而文化部在1963年下达销毁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决定[4]142,就是上级领导对此作品不再放行的明示。同时,这保障机制还包括文学批评等活动,为此,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以及“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3]74这一批评标准,甚至于,什么作品要赞扬肯定,什么作品要批评否定,都要由某一上级部门审批决定,等等,如延安时期对丁玲《在医院中》等作品的批判,就是如此。也就是这一保障机制,保障了工农兵文学服务于工农兵大众的可靠性。
(四)变口味逢迎为思想教育
传统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那些通俗文学作品。都是从阅读对象即服务对象出发,迎合对方的口味,即欣赏爱好和欣赏习惯的,无论内容情趣还是语言体式,都是逢迎农村、市井的贫民大众,因此,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服务对象占据着主动的地位,可以说,是服务对象牵着写作者的鼻子走;而工农兵文学,其严格意义上的工农兵文学,比如赵树理的小说,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等,也是通俗文学,虽它们完完全全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但却不是迎合工农兵大众的,有人说其“艺术追求是适应工农兵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7]但不可否认,就整部作品来说,其主旨并不是适应工农兵大众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作家(作品)占据着主动的地位。其为工农兵服务,表现为对工农兵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说:“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们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3]50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几十年间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哪一部(篇)不是在对工农兵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从而达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的?《小二黑结婚》等描写婚姻家庭生活的作品,教育工农兵群众要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实行自由恋爱;《暴风骤雨》等描写土改斗争的作品,教育工农兵群众要按政策斗地主分田地;《吕梁英雄传》等描写抗日斗争的作品,教育工农兵群众要英勇、顽强地同日寇斗争到底;《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等描写国内革命斗争的作品,教育工农兵群众要发扬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同国内反动派作斗争;而《创业史》、《山乡巨变》等描写农村合作化的作品,则教育工农兵群众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正是由于工农兵文学充分发挥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把思想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服务途径,所以就能达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
二、关于工农兵文学服务途径的思考
(一)关于它的政治性
经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20世纪40年代由毛泽东倡导的工农兵文学,绝不同于我国此前的任何文学。它是空前绝后的,它是同其他文学决裂的。过去既没有如此的文学理论,也没有如此的文学作品。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8]而工农兵文学,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斗争文学,不但其服务对象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从而显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而且,其服务途径的阶级写作、意识写作、机制保障和思想教育等特点,也无一不表现出阶级和政治的属性。应该说,工农兵文学的创作,就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行为。
(二)关于它的行政性
同是作为政治斗争文学,工农兵文学也不同于前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前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奉行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上世纪的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地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9]其中,“写真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指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写出生活的发展及其趋势。正因为“写真实”,所以党的领导只要加强对文学界思想引导,加强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原则的文学批评就可以达到领导的目的。所以相对来说,它对服务途径的管制是比较宽松的,在发表(出版)作品之前,作家们的创作活动有一定的自主性。而工农兵文学则是尊奉毛泽东“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3]64的创作原则,这一原则所体现的创作思想就是理想化的现实主义,要求作家表现不是生活中存在的,而是理想化了的生活,这并不是作家能够自主做到的,也就是说作家自己并不能够保证达到要求的。所以上级领导必须在创作前、创作中和创作后对作家的创作行为加以约束和限制,必须有一套机制保障:包括只有经过批准,作家才有下农村、工厂、部队深入生活的权利;只有依据党的政策思想才能去构思、写作作品;写出作品后,还要遵循领导意见修改,获得批准后才能付诸出版、发表。然后又必须根据党的思想和当时的中心任务,对作品进行评论宣传,甚而把阅读也当成政治任务,常常组织读者的讨论会,组织发表读后感,借以达到对工农兵群众宣传教育的目的……等等,这一切都是由党政领导来安排的,突出地体现了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的模式,党对文艺(文学)的领导,完全是行政领导,而不是思想领导,应该说,工农兵文学的创作,就是完完全全的行政行为。这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化,从而限制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工农兵文学题材、主题、情节以及表现手法的相似性,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关于它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倡导者独特的文学观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对当年的工农兵文学服务途径的彻底否定呢?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要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某一行为的合理性。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切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0]毛泽东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提倡工农兵文学时,正值我国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这就是当时的“实际运动”的情势。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工农兵群众参加抗日斗争,除了大力进行政治宣传之外,还必须利用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艺的形式对工农兵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这就是工农兵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或者说,工农兵文学就是在这种战争的语境中产生的。所以,对于毛泽东来说,也可以说对于所有的共产党人来说,在大家的心目中,文艺(文学)只不过是一种抗日宣传的形式,而不是文艺(文学)的本身,毛泽东就说过:“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3]15他反对完全从艺术出发去思考文学艺术问题,而主要从政治斗争出发考虑文学和艺术,为此,他极力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3]49如果从纯粹的“文学”的角度出发,这当然是忽视或者说轻视了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特性,但从工农兵的最大利益出发,他那样看待文学,不是没有理由的。当今学术界之所以否定毛泽东的“武器论”,不但是“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切了解”,而且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当时心目中的“文艺”(文学)到底是什么,没有意识到他当时并没有把文艺(文学)当成是完完全全的文艺(文学)的,他的“文学”概念和我们当今或者当时世界上的“文学”概念是不同的。他的“文学”不是本体意义的文学,而是“从属于政治”[3]70的政治中的文学,而我们的“文学”是文学中文学,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既然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观,不同的“政治”观,那为什么就不能有不同的“文学”观呢?而只是因为毛泽东这一政治中的“文学”概念,就决定了工农兵文学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的不同,也决定了工农兵文学会有与众不同的服务途径和服务方式,决定了工农兵文学服务途径的政治性。
[1]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刘江.论工农兵文学的独特样式[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0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82.
[5]李准.我怎样学习创作[J].文艺学习,1956(1):53.
[6]刘江.情感因由文学和思想因由文学[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9.
[7]夏翠柳.论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得与失[J].文学教育,2009(19):103.
[8]刘江.政治文学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2.
[9]王凤.简明语文知识辞典[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189.
[10]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