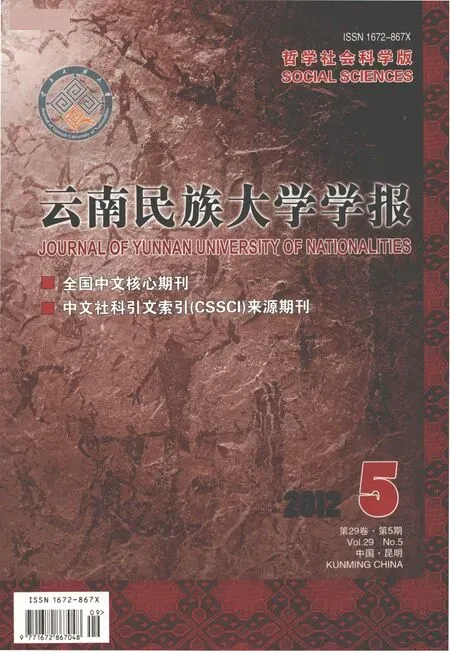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走向与地域文化关联——“现当代文学与云南”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走向与地域文化关联
——“现当代文学与云南”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玉霞,王 琨
(云南民族大学教务处,云南昆明650031)
2012年6月9~11日,由陈平原、夏晓虹、高远东、张福贵、金元浦、汤哲声、贺仲明、郭宝亮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期刊、出版社主编、编辑参加、云南民族大学主办的“现当代文学与云南”学术研讨会在云南香格里拉召开,会议围绕“现当代文学的地域性”、“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性”、“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动力与历史走向”、“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性”、“云南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思考”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一、现当代文学的地域性
陈平原指出:“文学地域性的提出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末的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配合改革开放这一过程进行的;70年代的现当代文学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成果,讨论萧军、萧红、王实味、丁玲等 ,既是文学也是政治文化的思想的问题;80年代的思路是重写文学史;90年代讨论20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标志是在武汉召开的一个由严家炎、陈平原等人参加的文学会议,研讨湖湘文化、江浙文化、两广、东北文化等区域文化如何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地域同时是世界性、全国性、地区性的,某种意义上有一个级别的限制。中国作家在创作上是有着我们自己的区域性的,我们需要的是借助文学创作获得某种自信和自尊,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小地方也可以出大作家。现在我特别关心方言文化的消失,保护小城镇和保护方言文化是同样一个道理,只要一种方言无法进入文学创作、学术语言,就只能进博物馆。方言一旦缺乏文学创作和学术表达,该方言就面临消亡。目前绝大部分的方言只能写歌谣,不能写长篇小说。方言、方言文化、方言文学的保留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文学史,而在于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甚至可以说,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即先留住方言、节日、习俗,留住一些特殊性,然后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才能融入好的文学创作,这个阶段是很难避免的。”
贺仲明认为:“地域性的因素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中,对其地域色彩做特别的强调和彰显;二是在文学批评和价值评判中,地域性因素具有很重要的主导作用,甚至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文学评价的标准产生了直接的、甚至是主导性的影响,如上海因素对文学流行趣味和评价标准的左右。另外,对某些作家地域性的强调,隐含着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姿态。在很多时候,文学的地域色彩成了落后地区作家的一种标识,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胎记。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地域性因素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发展趋向:一是一些作家将地域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目标;二是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刻意地表现地域性色彩,而不是将它们融合于生活,这样会严重限制作家的精神高度和创作深度,结果是作家创作内容、创作风格容易缺乏变化,雷同的、模式化的特点在加深。只有祛除了刻意的地域性,只有融化于生活之中的地域性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地域性,才是深层的、真实的地域性,这样的文学才真正可以进入伟大的文学,才是真正体现地域审美价值的文学。”
张福贵认为:“地域文学是文学史构成的基础,因为它有一种历史事实的支持,不是在刻意地寻找和制造地域文学史。近年来,地域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但由于先天的地域观念,我们对地域文学文化做出了过度阐释。”
二、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多样性
陈平原指出:“最近10年,文学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思路——性别文学、近年来被关注的都市文学……现在我每两年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北京、西安、香港、开封等城市的文化,把文学、文化、考古、艺术、建筑等融合在一起。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的压迫下步履维艰,我们的理想是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并存,但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太强了,致使文化的多样性迅速的消亡了,这种状态不论语言学家、文化学家、文化史家都明显地感到了。今天云南的文化多样性很丰富,可以借鉴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谋求进一步的发展。最近几年各个地方都在修文学史,但深入有困难,一段时间各地方的文学史蜂涌而出,如湖南文学史、湖北文学史,每个省都在写文学史,问题是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使这种文学史的书写可能越来越难。如2011年上海文库的出版将所有到过上海的作家作品收集起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有大批作家聚集在昆明,可以说每个省市的作家队伍中都有大量外来者,若每个省市都将来过的作家纳入自己的文学史,其他城市就面临资源的匮乏或重复。”
金元浦认为:“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性)发展模式对世界各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及破坏,文化消亡、语言消失、风俗消弭,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空间被极大压缩。要把捍卫文化多样性作为与尊重人的尊严一样应尽的义务。如何应对文化多样化或文化多极化的态势,在当代世界存在这样三个历史时期和发展的脉络:第一个阶段是西方主张的文化全球化时代(glocalization),主要特征为文化的全球本土化时期,即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要到各个国家去,要经过所在国家本土的改造,让它们自愿地接受;第二个阶段是本土的全球化时代(localglobalization),是借助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印度等国家借助全球化向世界逐步展示自己的文化;第三个阶段是各国之间民族文化间的文化间性时代(interculturality)。文化间性要解决的是在保证各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基本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来寻找共同的文化共性,其核心是以和为中心,追求沟通交流对话和交往。”
高远东认为:“鲁迅自己没有专论民族问题的文章,但他写的大量的文章和作品当中都涉及过民族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像波兰、印度、朝鲜等这些被压迫民族与中国有共同的现代命运;二是民族和鲁迅思考改造民族性、改造国民性问题相关联;三是民族主义文艺的问题。鲁迅在关于中国怎么样现代化的文明论或文明批判论中,民族问题占据着重要位置,他的思考和对中国、世界的现代关注相联系,涉及到现代人、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改造的许多关键问题。”
三、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动力与历史走向
陈平原指出:“当今中国大家看得很清楚,文学在大踏步的后退,比起‘五四’时期,比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前20年,最近10年文学在大踏步的后退,娱乐逐渐占据主流。今天除了获诺贝尔奖,否则媒体对你的诗集、小说,评论是不会给予关注的,文学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迅速的下降。面对这些情况必须承认,文学在逐渐地市场化、娱乐化的状态下,如何保持发展的未来或者说动力显得十分重要。我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文学的理想,二是文学研究的有效性和可能性,第三是文学教育必须承担什么责任。文学理想问题:文学是作为一种精神探索,作为一种文化创造,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同时文学也作为一种日常生活。这里重点谈文学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文学让日常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一种审美的趣味进入日常生活中。某种意义上,能够成为第一流作家的永远是很少很少的一小部分人,我关心的是一般人喜欢文学,让一般人具备欣赏文学的修养,有文学趣味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获奖不是唯一的,不是最重要的,畅销也不是文学应该鼓吹的主要动力,我们应该做的是文学如何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今天的写作主要看发行多少,有多少人接受,其实写作日后会分化,希望全国人民看你的书那只能做个通俗作家,许多作家都在寻求自己特定的读者群,不寻求被太多人理解,不一定要那么多人来接受,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文学研究的有效性和可能性(留待专文讨论)。文学教育必须承担什么责任:文学教授承担什么责任,如何做才能对得起这个时代,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大学中文系里没有办法培养出第一流的作家,但大学中文系有责任让整个社会的文学欣赏水平和国民的文学修养得到提升。给予喜欢文学的人一般的写作训练。现在越是发达地区,文学越显得不重要,越是发达地区,越是聪明的人越是不太喜欢做文学,而云南昭通有这么多人喜欢文学,很令我感动。”
郭宝亮以评委的身份对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作品作了一些介绍:“参选的176部作品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结,就是对历史叙事的偏好,即所谓的‘史诗’性追求。如此大的比例充分说明作家们对‘历史’的青睐和倚重,也说明‘历史叙事’的的确确成了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梳理。”
曾庆雨对扁平时代的文学精神进行研讨,认为“通俗文学的兴旺是促进文学精进和发展的路径之一,也是文学精神和思想最好体现的实体之一”。
四、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性
陈平原指出;“我们的学科分类是有缺陷的,这导致了学者的趣味、学识、境界都大受限制,也使文学研究很难做广做大。”
张福贵提出:“必须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本质和学术前提,目前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还不够成熟,寻求突破有两个途径:一是认识本质,二是反思前提。对于认识本质,在进入研究领域之前已经在做,对于反思前提往往被忽略。由于我们缺少反思学术前提的思想能力,就使学术创新、文化创新始终停留在一种倡导上,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前提往往是先验的、预先设定的,是不被质疑,更不能被证伪的,这是造成现当代文学学术局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必须建立学科规范和确立学术常识。目前现当代文学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学科命名的问题,二是学科边界和现代文学起点的确认问题,三是现当代文学的独立性和学者尊严与学术品格的确立问题。只有对学术前提加以质疑和思考,才能对现当代文学的许多问题提出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金元浦认为:“学科建设和学科的发展是处在一个变动的转型期的,范式的转型期意味着学科会有巨大的变动。这种转型的启示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常态的范式固定的研究时期还是一个剧烈转型的学科构架的时期,这个确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学科建制一定晚于并滞后于学科自身的发展。同时学科制度是为了我们社会发展、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服务的。”
五、云南现代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思考
(一)汤哲声对“云南现代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思考”进行阐述。
云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有三点: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创作的集中地之一,是中国少数民族创作成就标志性的省份;云南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的避难所、歇息地和战斗的阵地,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文字和极为感性的战争体验;云南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最热、创作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文学创作成为一个种风尚。云南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大省,有20多个民族。云南本土作家的创作当然离不开云南的本土特点。民族风格、底层生活、方言写作、原生态呈现是云南本土作家创作的总体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的云南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是本土作家系列。1920年10月25日创刊的《滇潮》被认为是云南的第一份新文学期刊,之后又有《翠湖之友》、《云波》等杂志。云南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主要有李乔、李纳、马子华、李寒谷等人。其中彝族作家李乔影响力最大。他1929年到上海,描写云南个旧锡矿工人生活的处女作《未完成的斗争》参加“创造社”出版的《现代小说》杂志“无名作家处女作征文”获得头奖,为当时的上海左翼文坛增添了边域矿工生活的题材。1949年以后,李乔发表了不少长篇小说,影响最大的是《欢笑的金沙江》。“十七年”云南文学特色突出,有太多特色鲜明的作家,这里就不一一历数。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所提及的作家有白族的景谊,景颇族的岳丁,佤族的董秀英,彝族的李骞、黄玲,哈尼族的存文学、哥布、艾扎等。当下中国文坛云南文学创作相当的繁荣和活跃,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彭荆风、雷平阳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李骞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黄玲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而夏天敏、雷平阳、李骞、黄玲都是昭通作家。据统计,昭通的文学创作者有数千人之多,昭通的中国作协会员就有十多位,昭通的文学创作状态被中国当代文坛誉为“昭通文学现象”加以扶持和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云南的另一条发展线索是创作云南生活的外来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较全面写滇地生活的作家大概是艾芜,他从四川到达昆明,然后进入缅甸,他的《南行记》和《漂泊杂记》主要记载这段时期的生活。外来作家的滇地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当然是抗战8年,此时的重庆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此时的云南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身处昆明的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巴金、沈从文、朱自清、汪曾祺、冯至、穆旦、施蛰存等写下了很多关于中国命运思虑及其对祖国边地昆明美好河山赞颂的文字;作为远征军的黄仁宇、孙克刚,战地记者戴广德、乐恕人、谢永炎、萧乾、范长江、谭伯英等人用纪实的文字写下了滇缅抗战的纪实报告;而用文化的视角写出这个时期云南的民风民俗的作家作品有曾昭抡的《缅边日记》、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等。滇缅边域的自然环境和独特民风、战争状态下的心灵和体验、文化考察中的乡土理念是这些外来作家创作的总体特征。
与历史的辉煌比,云南文学的创作仍存在三点不足:一是缺乏大视野;二是欠缺深思考;三是缺少名作家。
1.大视野。现代文学上的云南文学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当时的云南正处于战争的前沿,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加之西南联大的南迁,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抗战时期的滇地作家及其赴滇作家的创作成就高,是他们起点高,不止是生活的行走,而且是理念的行走。还应该关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大事和文学的创作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创作本民族的文学作品。
2.深思考。民族文学作家当然熟悉和热爱本民族的生活,他们在写本民族的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时极有穿透力,那种文学的感悟非本民族作家没法体悟到,很多优秀的作品也就产生在这些极有感染力的文字中。但是,过分的集中就显得表现力的狭窄。在当下云南文学创作中应该提倡写民族的转型和变化,这样的转型和变化是是生活层面上的,也是心理层面上的,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生活的岁月和外来的影响究竟怎样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或者沉淀了民族生活呢?写民族的转型和变化要比写民族的特性要难得多,因为它需要作家更为深刻的思考,不仅要有民族的思考,还要有中华民族历史的思考;不仅有生活形态的思考,还要有厚重的文化价值的判断和分析。
3.名作家。和其他省份比较起来,云南的名作家还是太少了。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我们需要埋头创作的作家,但是作家要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绝不仅仅是埋头,网络的关注、影视的介入、评奖获奖是作家成名的重要途径,当下社会的成名及其影响无不是在综合因素的合力中完成。
(二)会议对“现当代文学与云南”展开研讨
现代部分:专家对鲁迅、巴金、沈从文、艾芜、李广田等作家与云南的关系作了梳理与回顾——马旷源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鲁迅与陆晶清、柯仲平、马子华、张天虚、雷溅波、李乔等人的交往过程及交往方式;张昆华系统地介绍了巴金关于云南个旧的创作《砂丁》;张志平探讨了自由主义和李广田的教育思想及相关实践;李跃红认为西南联大精神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和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楷模,作为西南联大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其学术巅峰时期作品《贞元六书》,深刻体现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实质;和勇分析了艾芜《南行记》与云南的互相成就关系;汤亚平探讨了沈从文《云南看云》的语言艺术。
当代部分:专家对张昆华、于坚、海男、雷平阳、黄玲、黄立新等云南当代作家的创作进行了研讨——黄玲认为海男诗集《美味关系》探寻女性生命与存在的意义,在超越性别的基础上思考人的困惑;杨玉梅评价了张昆华散文的艺术特色,认为其散文独树一帜,在少数民族散文创作中更具有独特意义;昂自明、刘红分别对黄立新的《日暮乡关》、《沉香》做了评价;杨洁认为隐没在雷平阳诗集《云南记》诗行之中的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的对立、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交叠,以及诗歌叙事与个体言说之间的断裂,无不映衬着诗人肉身在世与精神历练的矛盾艰辛;张云徽分析了云南作家黄玲小说语言的地域特色;王晶指出了于坚在散文中所持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
专家们希望今后能对现当代文学与云南这一命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给予更多的更有深度的呈现。
(本文根据“现当代文学与云南”大会发言录音整理、综述。)
(责任编辑 丁立平)
I206
A
1672-867X(2012)05-0157-04
2011-06-12
刘玉霞(1973— ),女,云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副教授,文学博士。
王琨(1982— ),女,云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