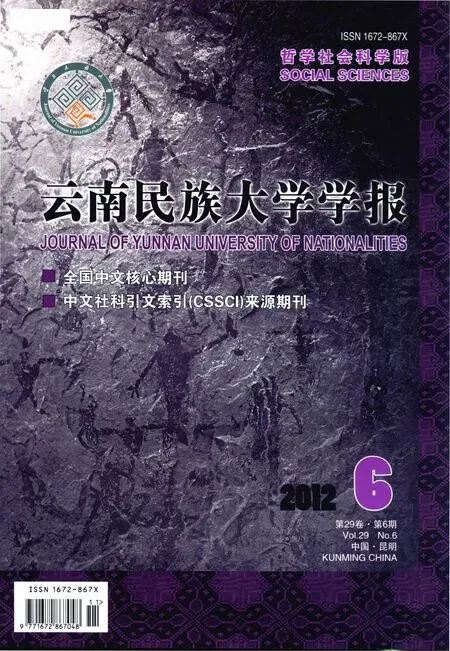明清时期的怒族社会
古永继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怒族为云南特有民族之一,元代以前记载稀少且内容含混,明清时期资料增加而渐清晰明朗。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挖掘、耙梳,从明清时期怒族的族名与分布、经济生活及民族关系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探讨。
一、族名与分布
我国史籍中与怒族有关的记载,始见于唐代樊绰的《云南志》。其云:“高黎贡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1](卷2《山川江源第二》)此处的 “怒江”,为水名指称,元代将其与族名挂钩。元《混一方舆胜览》载滇西镇康路景致: “潞江,俗名怒江,出路蛮,经镇康与大盈江合,入缅中。”[2](《云南行中书省·镇康路》)怒、潞、路,三字乃同音异写。两书中反映的山名、水名、族名、地名、方位,与今滇西高黎贡山下的怒江最后进入缅甸的走势及怒族分布,基本情况一致。
明代开始有确切的怒族之说,称“怒人”或“弩人”。明初洪武时奉命出使麓川、缅甸的行人司行人李思聪、钱古训二人,返回后各自所作《百夷传》中均有提及,两《传》篇名相同而文字有异。李云:“百夷即麓川平缅也,地在云南之西南。……其种类有大百夷、小百夷,又有蒲人、阿昌、缥人、古剌、哈剌……怒人等名……。怒人,颇类阿昌。蒲人、阿昌、哈剌、哈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余则居平地或水边也。言语皆不相通。”[3](卷10李思聪《百夷传》)钱云:“百夷在云南西南数千里……俗有大百夷、小百夷、漂人、古剌、哈剌、缅人、结些、哈杜、弩人、蒲蛮、阿昌等名……。弩人,目稍深,貌尤黑,额颅及口边刺十字十余。”[4]两者对当时麓川即今以滇西瑞丽为中心一带地区各族的分布、生活环境与习俗,作了大致描述。钱氏称怒族为“弩人”,为怒族史料中所罕见,或因其持弓射猎的特点给人印象深刻而被用作族名。其后,随着人们对边疆民族了解的加深,有关怒族的记载逐渐增多。
明中后期嘉靖时杨慎编辑《南诏野史》载:“怒人,居永昌怒江内外。其江深险,四序皆燠,赤地生烟。每二月,瘴气腾空,两堤草头交结不开,名交头瘴。男子面多黄瘦,刚狠好杀,射猎或采黄莲为生,鲜及中寿。妇人披发,红藤勒首。”[5](下卷《南诏各种蛮夷》)明末天启时刘文征撰 《滇志》云:“怒人,男子发用绳束,高七八寸,妇人结布于发。其俗大抵刚狠好杀,余与磨些同。惟丽江有之。”[6](卷30《羁縻志·种人》)两书比前更为细化,对永昌、丽江两地怒族的生存环境、体质特征、服饰装扮、习俗特点、生产生活等均有反映,清初史载多沿其说。
元明时期的“潞江”、“怒江”,在水名之外多与地名及行政区挂钩。元代的永昌、腾越之间有怒江甸 (今保山市西南潞江坝),元初隶柔远路;致和元年 (1328年)五月,曾有“怒江甸土官阿哀你”侵犯相邻诸寨,被云南行省派兵讨捕的记载。[7](卷30《泰定帝本纪二》)明永乐元年 (1403 年),怒江甸内附,设潞江长官司;九年,潞江长官司长官曩璧遣子入朝贡马献方物,升其地为潞江安抚司,隶属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不久改隶云南布政司。宣德八年 (1433年),改金齿永昌千户所为潞江州,隶云南布政司,以千夫长刀珍罕为知州,潞江安抚司仍同时并存。[8](卷315《云南土司列传三》)此期间,统治者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以夷制夷”的土官土司制度,永昌辖下,无论怒江甸还是潞江司、潞江州,其出头露脸的上层人物均为“百夷”(傣族)土官,作为诸族中世居偏远而发展落后的怒族则尚未受到社会关注而被大众普遍知晓,故明清两代对潞江与怒族的关系也另有不同说法,如“潞江,讹云怒江……”,[3](卷6《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山川》)“怒江,今在腾越。江之波涛涌如怒也;作 ‘潞江’,非。”[9](卷11)“潞江……本名怒江,以波涛汹涌而名”之类。[10](卷113《云南一》)怒族与怒江之间的天然联系,因人们了解的不多而一度被忽视及误解。
清雍正时,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雍正元年(1723年),废除丽江木氏土知府,改设流官;五年,于丽江府辖区内置维西厅,将鹤庆府通判移驻维西,下设土千总、把总等职,分管阿墩子、奔子栏、其喇、康叶各寨,对原有陋规杂派饬行裁革。新设流官通判陈权清明能干,治理有方,对辖下各族“约束抚绥,颇有条理”。此时的怒族,散居高山密林,刀耕火种,食尽迁栖岩穴,社会发展落后,被外人看作是喜欢“劫杀抢掠”的“久居化外”之人,而实际上却势力弱小,常受外族欺负。随着改流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布于维西边外靠近西藏擦哇陇等地屡被古宗(藏族)、傈僳侵凌而抵抗乏力的“怒子”,对官府“群生感激”,于雍正八年相率到维西衙门求见,以黄蜡、麻布、羊皮、山驴皮、麂皮等物充贡,“求纳为民,永为岁例”,愿意接受官府管束而获得保护;官府同意其请,亦于每年纳贡之时赏盐三百斤以为犒劳。[11](《文录》卷10鄂尔泰《奏陈怒彝输诚折》)[12](《夷人》)[13](卷15《云南·种人》)
从此,怒族与内地交往增多,“流入丽江、鹤庆境内,随二府土流兼辖”。[14](卷184《南蛮志三之三·种人三·怒人》)人们对怒族与怒江的关系及其分布状况的了解也更多见于史册,如:“怒人,居怒江边,与澜沧相近。……其最远者,名曰怒子。”[15](上卷《官师略·种人》)“怒人,在维西澜沧江外数百里崇山峻岭,有江曰怒江,环江皆怒人所居,故名。”[13](卷15《云南·种人》)“怒夷界最广,凡怒江以西,西北接西藏,西南接缅甸孟养陆阻地,东与丽江及大理府云龙州毗连皆是。”[14](卷106《武备志三之一·边防上·丽江》)“潞江在澜沧西……江之外为怒夷,故名怒江。……入保山乃名潞江。南流迳潞江安抚司。……出滇境入缅甸。”[16](卷80《地理志二十七·西藏》)等等。
清末以降,分布于怒江、澜沧江中上游一带之上帕 (今福贡)、菖蒲桶 (今贡山)、知子罗 (今泸水)、泸水、兰坪等偏远地区怒族的生存状态亦进入人们的视野,民国时期的《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征集菖蒲桶沿边志》、《知子罗属地说明书》、《泸水志》等书中,对此均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此不赘言。
于此可知,明清时的怒族,有怒人、弩人、怒子、怒夷等名,但均为掌控话语权的汉族文人笔下之“他称”,且不乏大汉族主义封建正统观念主导下的民族歧视之义。今怒族主要分布在云南怒江州的贡山、福贡、泸水及兰坪县,另外迪庆州维西县及西藏察隅县有少量分布。这与明清时期以怒江两岸为中心,涉及丽江、维西、鹤庆、云龙、永昌边外,及怒江、澜沧江以西缅甸北部某些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而略有差别。
二、经济生活
明清时期的怒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低下,经济以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
明初时麓川即今云南怒江、保山与缅甸东北部一带的怒人,同蒲人、阿昌、哈剌、哈杜等族杂居一起,“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3](卷10李思聪《百夷传》)在山区从事粗放的农业生产,以荞麦为主食。明中期,居永昌怒江内外条件艰苦之下的的怒人,有“男子面多黄瘦……射猎或采黄莲为生,鲜及中寿”之载。[5](下卷《南诏各种蛮夷》)至明末,从其 “男子发用绳束,高七八寸,妇人结布于发。其俗大抵刚狠好杀 …… 惟丽江有之”的 记述 来看,[6](卷30《羁縻志·种人》)分布于今丽江西部即维西、兰坪、福贡、贡山一带的怒族中,农业、手工业已有一定发展,但“刚狠好杀”之类原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野蛮习俗尚较浓厚。
清代,人们知晓的怒族分布区域不断扩大,各地发展存在一定差别且呈现不同的特点。
居丽江府怒江边而与澜沧江相近的“怒人”,“人结麻布于腰,采黄连为生。茹毛饮血,好食虫鼠”;[15](上卷《官师略·种人》)稍好者, “以麻布裹身,不成衣制,倚岩结草庐而居”;[13](卷15《云南·种人》)两江外更偏远地区而同俅人 (独龙族)、生熟栗粟杂居的“怒子”,则被称为“远于人类,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之风”;[17](上卷《人部·丽夷》)腾越州者更为落后,居于山巅,与其他民族言语不通,被描述为“略似人形而已”。[18](卷11《杂志》)生产水平均十分低下,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过渡发展阶段。
居怒江边靠内地者,则农副产品较为丰富,“常负筐持囊劚黄连,亦知耕种”,粮蔬有黍、麦、薯、芋等类;平时生活中,男女“首勒红藤,麻布短衣。男著裤,女以裙……覆竹为屋,编竹为垣”,且“精为竹器,织红文麻布,么些不远千里往购之”。[12](《夷人》)[14](卷184《南蛮志三之三·种人三·怒人》)在衣食、居处、器用等方面均大为改观,食物种类增多,利用当地植物资源苎麻建房织布、制作家具等,手工业技术已具相当水平,其产品受到其他民族的喜爱。有的富裕者并积累起自己的产业,雇用俅人 (独龙族)从事家内劳动,丽江府外俅江边的俅人,就“常为怒人佣工”;有的蓄奴户并干脆采用暴力手段,直接到俅人地区,“夺其子女为婢仆”。[14](卷185《南蛮志三之四·种人四·俅人》)[13](卷15《云南·种人》)
另外,自雍正八年得到官方的接纳认可后,“猎禽兽以佐食,无盐,无马骡”的维西“怒子”,每年以“黄蜡八十斤、麻布十五丈、山驴皮十、麂皮二十”为贡赋标准,且常以当地特产黄连入售内地,官府专门“犒以砂盐”。其他民族“多负盐至其地交易”,当地怒人则商品交换意识淡薄,对入己地商人“敬礼而膳之,不取值,卫之出”。[14](卷184《南蛮志三之三·种人三·怒人》)[12](《夷人》)即便相邻丽江盐井而与傈僳、巴苴 (普米族)、俅人杂处的怒人,也“买卖不惯用钱,米粮柴薪惟盐可换”。[15](上卷 《财用略·行盐》)①直至民国时期,中甸、维西、知子罗、菖蒲桶等地仍无大市集;兰坪营盘街,其交易物品多为黄连、贝母、漆、牛皮、香菌、木耳等各种山货。(见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一·市集》)各地并有“知 敬 长, 凡 进 食 尊 辈, 率 跪 以献”,[13](卷15《云南·种人》)以及村寨中 “无盗,路不拾遗,非御虎豹,外户可不扃”的习俗,原部分地区怒人“刚狠好杀”的特点,在接受官府的管理约束而“知法度”之后也逐渐消失,以致乾隆时期的学者竟认为,以前志书中的此类“好杀”记载,属于不符实际的夸大之说。[12](《夷人》)但在有的地区,某些野蛮行为实仍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如:清末时维西的“怒子”,即有“拉人勒赎,烧杀抢劫,习以为常”的记载,被人们看作是“夷类中之最凶悍者”,直至民国初年当地政府加强治理后,此类行为才 “陆续敛迹”。[19](《种类》)上帕“怒子”,亦常往澜沧江一带滋扰,当地人民被迫上纳“三脚铁锅、锄斧、刀矛等项铁器,名为铁金,每年由怒子派人前往德溪一带征收”,民国纪元政府派兵开辟怒江将其征服,才开始改观。[20](《征收》)
溜索渡江,长期以来就是怒江两岸人民往来过江的主要交通方式。清代维西金沙江、澜沧江边对溜筒渡江的使用已较普遍,乾隆时张泓的《滇南新语》、余庆远的《维西见闻记》对此均有记载,但未确指哪些民族在使用。民国时的记述对此稍详:“阿墩、泸水、菖蒲桶、维西等数处江流湍急不能行船者,即以溜索渡江。盖用竹为绳,削木为邦,借其倾斜滑溜渡过,故曰溜渡。人畜货物通运困难,交通中之最原始者也。”[21](卷57《交通考二·津渡溜渡》)民国时的菖蒲桶 (今贡山)之地怒江两岸,即设有溜索渡口十五处、大木挖空成舟之猪槽船渡口十三处。[22](第十《交通》)阿墩子、泸水、菖蒲桶等均为怒族聚居地,而溜索渡江仍在今天的怒族生活中保持着顽强生命力。可以说,在明清时的交通条件下,溜渡已然成为怒江两岸怒族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可知,此时期的怒族社会,狩猎、采集在其生产生活中仍占相当比重,人们为维持简单的生活条件而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虽出现一定的剩余产品,但交换多限于以物易物,尚未产生实质性的商品贸易;因所居地不产盐,食盐成为怒人接受官府贡赋回馈及平时交易中的重要物品;在艰险的自然环境下,溜索渡江为怒族民众出行所必需。整体来看,清代部分地区怒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并不太大,人们的生活尚处于原始淳朴的社会环境之中,而在部分地区则分化明显,出现了家长奴隶制;清中后期,随着对官府认同感的加深及与其他民族交往增多,人们的行为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之中不断改变。
三、民族关系
明清时期怒族的分布,涉及丽江、鹤庆、大理、永昌等府辖内的部分区域,而主要集中于丽江;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使其与相邻的纳西、傈僳、俅人 (独龙族)、古宗 (藏族)等族在各方面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与不同民族的交往中体现了不同的特点。
(一)与纳西族的关系
清雍正以前,丽江长期被纳西族土知府木氏所统治,怒族多远居怒江边外,仅少部分靠内村寨为木氏土府直接管辖。改土归流后木氏衰落,随着大量怒族从边外流入,官府对其总体上仍实行“羁縻”之制,经济上每年仅收取怒族自愿上缴的土产黄蜡、麂皮、麻布等物折征之银一十二两四钱二分,历年造册报部在案;政治上则通过相关地区的土司头人进行间接管理:鹤庆府辖维西境内怒江两岸,“怒子、傈僳夷民一百一十一村褰,分隶维西康普千总禾娘管束”;原隶木氏管理的丽江府属怒江两岸怒子、傈僳58村寨,则“令浪沧江烟川保长和为贵就近管束”。[23](P275)女土千总禾娘、保长和为贵,均为当地纳西族土官。禾娘之后,其媳禾志明及头人王芬、王芝、禾品、王永锡等先后继续实施管辖权。但至乾隆时,纳西族土官因循土府旧规,擅自提高贡赋标准且改为私收,按人口征收山租实物,并勘丈田亩新增赋粮等,迫使“丽境怒傈夷民”在逢年过节之时携带盐、布等货,前往更弱势的俅人地方放债取利,折收黄连甚至人口子女带回康普,“或抵给土弁头人作为额规,或辗转售卖以偿资本”。此事违背官府善待怒族的既定政策,无端增加负担而滋扰民间,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最后惊动省府官员查处。乾隆十八年 (1753年),康普怒子准折带回的俅人男女58名、丽江怒子准折夷男女72名被责令遣返送回,而头人王芬、王芝、禾品、王永锡,保长和为贵,催头和可清、和志宏等被“各枷号一个月,满日责四十板”,“康普土千总名缺,永远裁革”。
怒族与纳西族的关系,更多的是通过双方征缴赋税即统治与被统治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底层民众之间,则不乏你来我往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交流,如前述怒人精制的竹器、红文麻布深受各地青睐,“么些不远千里往购之”,即为突出一例。
(二)与傈僳族的关系
傈僳族先民,早期分布于金沙江两岸及今四川西南木里、盐源、盐边一带,明代时因不堪战乱及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压榨,在头人木必扒的带领下,渐向云南西北部的澜沧江、怒江一带迁徙。清代散居于丽江、大理、永昌、姚安等地,而以今怒江、丽江境内为主,与纳西族、怒族、独龙族等相混杂居。民国时的菖蒲桶 (今贡山),即有“怒子系土著,傈僳由上帕及沧江搬来”之说;[22](第十五《氏族》)上帕 (今福贡)同样如此,“人种原为怒子,后渐始有傈僳,由沧江、六库一带移来杂居其间,名虽归丽江府管辖,其实则怒、傈自成部落,亦无土司统属”。[20](《沿革》)怒族与傈僳族,两者交相混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物质生活及精神文化方面,相同相似之处甚多,史籍中常常“怒、栗”并称,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但傈僳族的社会发展程度比怒族要高,分布区域更广阔,至清中后期,一些地区已进入家长奴隶制或封建地主制阶段,且在长期艰苦的自然环境及与其他民族的争斗中培养出极强的战斗能力,其“善用弩,发无虚矢”的特长为他族所忌惮,被称为“诸夷中最悍”者。[14](卷184《南蛮志三之三·种人三》,)[24](卷2《大理府》)怒族与傈僳族之间,因力量悬殊而致其地位不平等,“强者为酋,弱者为仆”,[22](第四《舆地》)怒族常被奴役和掠夺;“性怯而懦,傈僳侵之”,[25](第13《志蛮》)成为时人给部分地区怒族贴上的习惯性标签。雍正八年,维西边外怒族辗转归附流官官府以寻求保护,其原因之一就是 “常苦栗粟之侵凌而不能御”。[12](《夷人》》)故在清嘉庆七年 (1802年)维西傈僳恒乍绷领导的起义中,官府重兵镇压,恒乍绷失败后逃往怒地躲藏;在官军的威逼利诱下,即出现“怒子等不特不肯依附”恒乍绷,“并欲齐心协拿,先将恒乍绷之表妹擒献”,继而“怒子前引”为官军带路追剿恒乍绷的现象。[26](卷117、卷119)当然,两族间关系的主流仍是友好共处、相互交流和提高,而傈僳族在各方面的影响则比怒族大得多。如语言,清末民国时的贡山一带,属民“分喇嘛、古宗、怒子、栗粟、曲子五种”,而语言仅有古宗语、怒子语、傈僳语三种,其中均为藏族的喇嘛、古宗系古宗语,怒子、曲子 (独龙族)系怒子语,傈僳通古宗、怒子语者绝少,傈僳语则“全境通晓,尽人皆知”。[21](卷70《方言考五·怒子古宗栗粟语》)上帕与其类似,在怒子、傈僳、拉马 (白族支系)三种属民中,语言仅有怒子、傈僳两种,拉马语仅沧江一带有之,移来帕地者概从傈僳语,怒语惟怒子使用,傈僳语则“全境通用,尽人皆知”。[20](《语言》)揆诸历史和现实,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弱及影响大小,无不与其语言在相关地区使用和通行范围的广狭成正比。
(三)与独龙族的关系
怒族与独龙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在历史、语言、文化、生产生活习惯等方面关系紧密。元代始见独龙族记载,谓丽江路有蛮八种,其中之一的 “橇”,[27](《丽江路·风俗形势》)即为后来清代时的俅人、俅子、曲子、曲人、曲夷之先民。明代相关史料缺略,清代复见记载,谓:“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外,系鹤庆、丽江西域外野夷。”[28](卷7)“俅人,居怒江大雪山外俅犸地方。原系西域野夷,今或偕怒人抵维西。”[13](卷15《云南·种人》)可知维西俅人同怒人一样,原居于怒江、澜沧江边外,乘雍正改流之风进入内地。整体上俅人多与怒族、傈僳族、白族等为邻,分布于今怒江州贡山西部的独龙江、北部的怒江两岸、维西县以及西藏察隅县等地。清前期,俅人社会发展缓慢,有“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者,有居山岩中“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者,[28](卷7)性格柔懦,不通内地语言,亦无贡税,尚未脱离原始社会阶段。但俅人“地与怒地接壤,不敢越界,怒人暨西域蛮夷率夺其子女为婢仆”,[13](卷15《云南·种人》)两者虽居住接邻,俅人却不敢随便越出自己的部落或族群界线,且常遭受怒人及其他民族的人口打劫之灾,在与诸族的交往中处于劣势之最底层而常居被动地位。清中后期,怒人不时对俅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及控制,居俅江 (独龙江)外已知务耕植的俅 人, 即 “ 常 为 怒 人 佣工”;[14](卷185《南蛮志三之四·种人四·俅人》)而当怒人在受到纳西族土司头人的经济盘剥时,则往往把负担转嫁到俅人身上,前述怒人到俅人地区放债收利折扣人口带回顶替赋税上缴之类,即说明了此问题。上帕地区俅人,每年还必须“上纳铁器与怒子,图免滋扰之患”,而“怒子管俅子”之语,民国时期仍在当地流传。[20](《管辖》)另外,怒人与俅人同样使用怒语,相互间较为熟悉,使其成为外界进入俅人地区办事的重要助手。管理菖蒲桶地区的喇嘛寺僧,每年向曲人收取钱粮山货时并不亲到其地,而是从怒人中选择“熟习曲道者一人派充曲管”,每年令其至曲地代为收缴;光绪末丽江府分驻阿墩子弹压委员兼办怒江事宜夏瑚考察怒江、独龙江时,也先后招募“通晓曲语、熟习曲道”的怒民多人作为翻译、向导及传达号令者,对完成任务提供了极大帮助。[11](纪载卷23《清十二》夏瑚《怒俅边隘详情》)另纹面习俗,明清时的云南仅怒族、独龙族所特有。怒人有“额颅及口边刺十字十余”、“男女披发,面刺青文”之载;[4][12](《夷人》)夏瑚在独龙江,亦见俅人女子 “头面鼻梁两颧及上下唇均刺花纹”。此习俗在怒族中后渐消失,独龙族中至今则仍可见。
(四)与藏族的关系
明清时云南境内的藏族被称为“古宗”,在不少地区与怒族相邻杂居,丽江、鹤庆特别是靠近滇藏边界地区尤多。清代维西边外的怒子,界连西藏之三艾、擦连冈、擦瓦陇等地 (今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一带),常被藏族土司掠夺骚扰。乾隆五年(1740年),云南总督庆复即向朝廷奏报:“古宗人等进至怒地,若见怒子人众,则以贸易为生;如见怒子人少,或遇打柴割草之男妇,即行掳掠。因而怒子不敢散居,或四五百家,或二三百家,于山箐深邃之区,自成巢穴。”[29](P26)类似事件甚多,怒族起而反抗,双方不时交兵仇杀,以致官府多次协调,甚至出兵堵截藏族土司,下令各地官员约束,防止事态扩大。咸丰、同治时的菖蒲桶 (今贡山)地区,古宗所奉红教喇嘛习性强横,势力甚大,“地方之公务、夷人之诉讼,均由喇嘛处理审判”,[22](第一《沿革及设治》)怒子、傈僳、曲子等只有服从,栽种还须交纳租粮。但一般古宗与怒子之间仍友好相处,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了不少共同的习俗爱好。如:菖蒲桶的傈僳、曲子,每届春季,听雀叫即种苞谷;古宗、怒子则习惯一致,春季樱桃开花种苞谷,秋末胡桃落叶种青稞、小麦。所居房屋,曲子、傈僳四面无墙,因无人会做泥工;古宗、怒子则四围筑土,尽系自筑,人能为之。傈僳、曲子无集会习俗,古宗、怒子则于每一村中建一公众房,每月十日在公众房办会,各醵酒肉盐物,请喇嘛念经后群相会食。[22](第十一《农政》、第十二《工业》、第十七《礼俗》)
另外,怒族与汉族之间也多有交往,主要体现在平时与官府各级官员的联系、战事中与官军的接触、经济生活中与汉人商贾及相邻汉族居民的往来,等等。此类记载不多,实乃当时外界了解怒族社会的重要窗口。
余 论
近年来,有关怒族的研究成果斐然,但多为田野调查或以近现代时期为研究背景;明清两代虽是怒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却因资料匮乏而使研究的深入显得吃力。笔者在涉及怒族古代历史的研究中,感觉有限的资料尚未被人们留意和充分利用,有的资料变换一下角度或又可显现出新的价值。故在所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于此三方面着手,立足基本史实,尽量少作空泛之言,便于人们了解明清时期怒族社会发展之中相关事件的大体脉络,希望能从新的视角,给读者提供点不一样的启迪及感受。
[1][唐]樊绰.云南志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元]刘应里等.混一方舆胜览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3][明·景泰]陈文.云南图经志书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4][明·洪武]钱古训.百夷传 [M].江应樑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5][明]杨慎编辑.[清]胡蔚订正.南诏野史 [M].光绪刻本.
[6][明·天启]刘文征.滇志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7][明]宋濂等.元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8] [清]张廷玉等.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明]诸葛元声.滇史 [M].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
[1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民国]李根源.永昌府文征 [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12][清·乾隆]余庆远.维西见闻记[M].《丛书集成初编》第314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清·乾隆]谢圣纶.滇黔志略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14][清·道光]阮元等.云南通志稿[M].道光刻本.
[15][清·乾隆]管学宣等.丽江府志略[M].丽江县志编委员会办公室翻印,1991.
[16] [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 [清·乾隆]吴大勋.滇南闻见录 [C].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 (卷12)[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8][清·乾隆]屠述濂.腾越州志 [M].光绪刻本.
[19][民国]屈知春.云南维西县地志全编 [C].李汝春.唐至清代有关维西史料辑录 [M].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1992.
[20][民国]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 [M].怒江州旧志整理班子据民国二十年钤印钞本标点,1998.
[21][民国]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22][民国]征集菖蒲桶沿边志 [M].怒江州旧志整理班子据民国九年钤印钞本标点,1998.
[23]李汝春.唐至清代有关维西史料辑录 [M].维西县志办公室,199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民族类139号载乾隆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云贵总督硕色奏折.
[24] [清·光绪]刘慰三.滇南志略 [C].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 (卷11)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5][清·嘉庆]檀萃.滇海虞衡志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6]清仁宗实录 [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7] [元]孛兰肹等.元一统志 [M].北京:中华书局,1966.
[28][清·乾隆]朝官编绘.皇清职贡图 [C].徐郦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 (第一册) [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29]怒族简史编写组.怒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 [C].怒族简史 (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