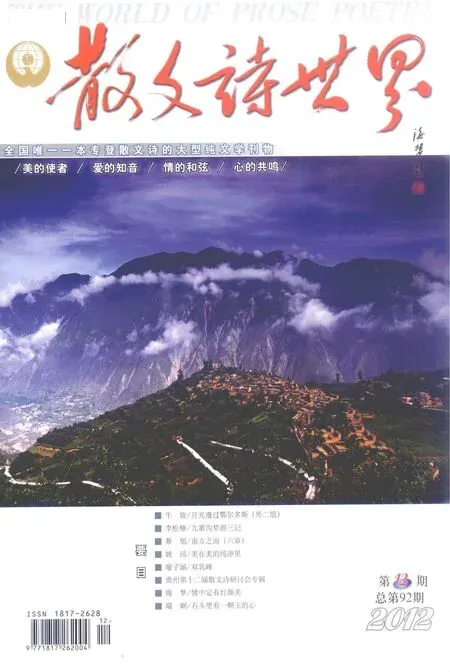为苏北写诗(十章)
江苏 黑 马
故 国
当我再一次返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国,回到那梦中细小的河流,坐看停靠在湖对岸漏风漏雨的船只,以及树杈上空空的鸟巢。
远处,含苞的春天盛开。湖面的月亮跳起了舞,映着恋人的影子。一列运煤的火车驶过思想的村庄。
亲爱的故乡啊,至此,我写下的诗词有了流水的节奏。
极目远眺,田原确有野性之美,我多想为家乡写一首深情婉丽的诗啊,而恋人的琴已铮铮然响起,正穿过北国入冬来的第一场大雪。
北国的诸神业已安睡,只有风,还在吹。
朗 诵
我要朗诵悲悯中的苏北,眸子里的深意,和被大风翻阅过的心情,民歌的肺活量辽阔着我们卑微的一生。
风是从地下吹出来的,身披露水的人,入土为安的人。煤炭是工人阶级的心脏,在乡间林阴路上晃荡着体内的磷,像一群燕雀,像一把锈在黄泥中的铁钉。
煤情,用黑暗制造心灵唱片的神,把青灯捻得比夜还长,泪光中的村庄,比梦还轻。
夜晚,火车的轰鸣把我的沉睡唤醒,把梦搬上火车,像火焰,像奔跑的雨滴。
今夜,顺着月光的梯子爬上去,用煤炭的手,祖国的指纹,朗诵我忧伤的诗篇。
秋的颂词
大师的手指在月亮上舞蹈,芬芳流进我的灵魂。
我呵护的灯盏啊,在苏北的宁静中旋亮,聆听细雨、布谷和芦笙。
秋天的枝头挂满了梦想,露水在上。雨对雨的复述中,展开了新的方程式,倒叙的村庄,简单地爱着,你的笑是村庄最亮丽的部分,云朵在流泪。
寂寞啊,这旷世的离愁,豪放的词牌,谁的眼泪背叛了秋天,和秋天之上的星辰。
闪电如此高远,秋天空旷,鹰和胡琴,铜和琵琶。
为苏北写诗
带着麦子的讯息返乡,在绿色的窸窣中,我整晚地旅行。
童年那些快乐的歌谣,是否响彻了宁静中的一座小小村庄。月亮还活在李白的金樽里,坛子在发光。朴素的苏北令我泪满衣襟。
从一粒麦穗里醒来的是子规的余韵,层层叠叠的叶子上住着神的花朵。我仿佛看清了新的图腾,从一棵庄稼到另一棵庄稼,从一片秧苗到另一片秧苗,谁替我把风喊住,把村庄的白云喊住?
月儿弯弯,照耀我的苏北。
现在,请允许我再为苏北写一组诗,用大风中的一杯浊酒,用泥土深处一粒最轻的词汇,用我这一个世纪辽阔的爱,用漂泊的灵魂,用这村庄空洞眼神中最后的一盏烛火。
忧 伤
秋天的石头在思念中发芽,我像一粒微尘,在飞翔中有了一个坡度。中途遇见一封乌云写给湖泊的情书,沉甸甸的满是泪水。
我的骨头里有了轻微的哀伤,苍凉的大地和天空,突然蓝了一下。
仿佛,一场秋雨,注定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来临,我开始转身火苗在银器中闪亮,天地旋覆,神的翅膀低了又低。
一个草地上的少年爱上了薄暮黄昏,他的呼吸细微而广阔。
一个人的乡村
一个人的骨头,装着一个多么干净的时代。
打麦场上空还飘荡着湛蓝色的钟声,谁的泪水凝成了石头。
民歌在筑巢,爱情在写墓志铭,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太阳穿着黄金流苏的嫁衣,每一座村庄都可能饱含几代人的眼泪。
一个人装满五谷,泥土一样躺下,而露水,下了很久。落叶和闪电慢了下来,苍鹭在叫,哦,这被遗忘的疲惫的一生。
这柔软的苦艾酒,一直下到秋风浩荡的底部。
秋风彻底锯破了木头里的雨水和虫鸣,把一个人的黑发吹成泛白。
苦 旅
一粒鸟鸣,埋葬在秋天的大海。
在清风里我抓起明亮的阳光大口咀嚼,简单的行囊,微笑的脸。大地空荡荡的,野草风风火火长起来了。
大地葳蕤,野草最有事业心。
大雁卸去了途中的离愁,黄河流啊流啊,芦花在秋天里就要出嫁,谁的哭泣被秋风搬进了耳朵。
草色如火,大地包容了一条河流桀骜不驯的内心。
黄昏收住彩云的翅膀,我读到一只柔情的蝴蝶,和一颗悲壮的雄心。
彩云去了远方,远方到底有多远。一个苦旅者的背影,穿过大片飘摇的芦苇荡,渐行渐远。
芦苇荡
芦苇荡,下起了雪。
村庄在通往蓝天小小的途中,苏北平原上空的风一直没有停止过,疲惫的蛙鸣,一片连着一片。
这泪水浸泡过的乡村,我的思念是苇叶上清醒的水滴,焕发着蔚蓝的光芒,和湿漉漉的记忆,在怀里。
炊烟挽着黄昏,火红的乡情在宁静中扑面而来。
在低回的蝉鸣中饮茶,饮思乡之水,这思乡的名字啊,人生故土,在水一方,渐浓渐深。
祭 祀
那些把雷声背在身上的穷乡亲啊,能不能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好让这温润的土地能托起发芽的巢,托起心头小小的幸福。
多少希望,和多少隐忍的时光,被春天劫掠去了。帆影,稻穗,火苗,进入薄薄的梦乡。
那些美丽的花的种子,正撒向浩瀚无垠的乡间大地。
岁月啊,请给乡亲们一件梦的衣裳吧,慰藉那一颗颗柔软的心,那披着夜之孝衣举着苦难火把奔跑的人,像是村庄头顶掠过的一道道闪电。
北国之秋
北国之秋,带着疼痛入眠,在泥土的辞令里,打坐的果实,仿佛在参禅悟道。
不问前生今世,地上是否落花如雪,潮湿的心灵总有一种光芒。照亮黑夜,脚下紧握的是根啊,那是祖先的神经。
从不疲惫的,浅吟着的,诗或者歌,那是神的低语。秋天,甚至不需要马匹和献辞,伸手却能抓一把鸟鸣。
北国之秋深处的芦花飘摇,酒和太阳,村庄和我,和故乡的未知部分。
河流在闪烁,教堂的钟,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