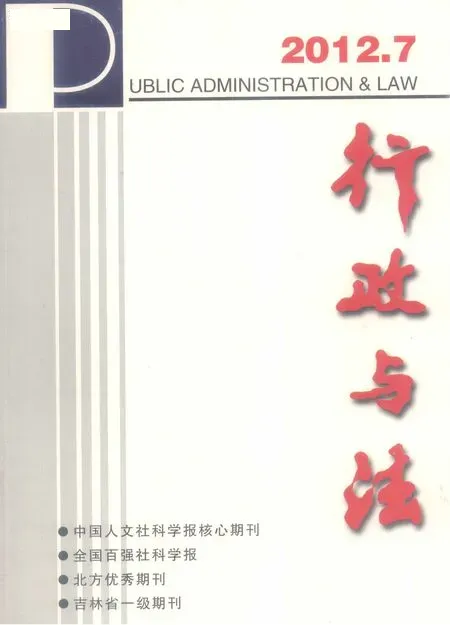我国地方立法权扩张的政治后果分析
□罗干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我国地方立法权扩张的政治后果分析
□罗干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本文以建国以来中央——地方立法权限演变的历史说明地方立法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市场化发展和民主化改革是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动力,并以事实和数据剖析了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现状,从社会影响角度分析了地方立法权限扩张的政治后果,从保证中央立法权威、党政关系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证了目前我国立法分权的发展还不能影响到国家的单一制结构形式,因此,应将注意力从关注 “到底放不放立法权”的问题转向 “如何放好地方立法权”的问题。
地方立法;中国立法体制;国家结构形式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孙中山曾说过“立法权的行使状况标志着政治的运行状况,立法权作用的充分发挥是政治昌明、法治发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伴随着各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是地方立法的日益活跃。因此,分析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原因、发展的趋势,以及发展的政治后果十分必要。目前,学界大都把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限的历史演变分为“分散,集权,分散与集权相结合”三个阶段,而本文要做的就是从中央——地方立法权限历史演变中;从当今中国的国情中去分析目前地方权限呈扩大趋势的原因;从地方立法实践中分析其发展趋向;从地方立法的适用上分析其政治后果,并由此证明地方立法权限的扩大并不会使我国的单一制度陷入危机,不会使国家产生分裂的危险。
一、问题的提出:地区多样性的国情需要立法分权
从建国至今,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从建国到1954年《宪法》颁布期间,是立法权相对分散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立法权主要属于中央,但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享有拟订法令、法规和条例的权力。立法主体的多元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直辖市、大行政区辖市和省辖市的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以及民族自治机关,都拥有相应的立法权。二是从1954年《宪法》颁布到1979年《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颁布,是中央立法高度集权时期。地方立法萧条并陷入低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只能依照授权制定单行法规或者修改不适用的法律条文。各地方国家机关的立法权被取消,只有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有权依照当地社会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并且须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中央立法机构也并未发挥太大作用,1966年5月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举行过一次会议,国家立法工作几乎中断。三是从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至今,是立法权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时期,地方立法逐渐恢复并呈现雨后春笋之势。1986年12月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对 《地方组织法》的修改决定,规定了省会城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各自拥有相应的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权力,而2000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对我国地方立法主体进行了再一次扩充。《立法法》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被升列为“较大的市”,这样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以 “较大的市”的身份获得了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范围,壮大了地方立法队伍。[1]
通过对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历史的了解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立法权限的划分往往是这个国家政治变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写照,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比如建国初期,之所以赋予众多主体以立法职权,形成分散立法的格局,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革命和建设都需要秩序和规范,但由于彻底废除了国民党的伪法统,单依靠中央很快制定出能够满足和适应形势发展所需要的大量法律法规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是完全基于当时新老解放区的情况差别而确立的,对新解放的地区,不论其为省级或县级,都有必要给予立法规的权力,以便因地制宜地实行各项改革,建立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当今我国国家立法实行的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模式,同样是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同样是历史的选择、国情的需要。
二、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发展:推动地方立法权不断扩大的动力
面对地方立法权限不断扩张的现实,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其内在原因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民主化趋势要求地方立法权的存在并适当发展。因为民主治理需要的是分权而不是集权。分权可以分担治理的责任,而且治理上的一定自主权具有激励制度创新和竞争的功能。以历史的角度观之,任何国家都必定存在某种形式的纵向分权,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配置不同的治理权力,这是解决国家具体问题的需要,因为国家不可能随时随地事无巨细深入到地方各个角落去解决各种地方性问题。地方立法的存在正是这个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实行较高程度的分权很可能会产生地方割据、分裂甚至战乱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并不是由于分权,而是因为对于分权的“度”的把握,即我们要探索的是如何分好权以及怎样分权,才能既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同时又保证国家的完整统一。
第二,国家权力在配置过程中需要合作与沟通,这里的合作不仅指社会成员间的合作,而且包括国家机关之间的合作。各国家机关都享有相应的权力,它们间的权力分工是必要的。中央和地方立法权力的配置实际上是在法制统一原则下的分工合作,“法律与执行法律之间缺乏协调就会导致政治的瘫痪”。地方要遵循国家法律并执行之,中央立法本身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决定了其“框架式立法”的特点,但地方不应消极而应积极地“执行”中央立法,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予以细化或变通,在不断地调适中贯彻国家政令并平衡利益冲突,最大限度地寻求利益一致。正如庞德所言,“今后法学思想的道路,似乎是一条通向合作理想而不是通向相互竞争的自我主张理想的道路”。[2](p67)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机关也需要在长期合作、交流和妥协过程中,寻找二者关系的切合点。
第三,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需要地方立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很大原因在于国家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经济行为者在自利的动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无可厚非地成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各个利益主体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然而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是无法满足多元利益诉求的,于是就需要能够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地方立法发挥作用。而且,沿海城市、经济特区、民族自治地区、“一国两制”特区的独特性,使我国以前的单一立法体制不能适应时代变化,因此必须在立法上适当放权。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恰好证明了立法分权的正确性:国家适当给予沿海开放城市以特殊的优惠政策和自主权力,结果是当地经济的活跃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其中不能忽视的是地方自主立法的可行性,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改革的成果,并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
第四,地方立法适应了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在各地方立法的实践中,“先行立法”的出现给国家立法工作注入了活力,并且成为了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一个亮点。“先行立法”是地方立法中的创新,既填补了国家立法的空白,切实保障了各项社会活动都有法可依,同时也为中央立法的制定和完善起到了 “试验田”的作用。如深圳市1994年颁布的《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就在我国城市物业管理规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开了先河,也为2003年《物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奠定了基础。
总之,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治理方式的民主化都需要立法分权的推动,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地差异的存在,也需要地方立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侧重于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改革开放后地方立法现状分析
响应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各个地方都紧抓经济不放手,相应地,地方立法也在这方面有着充分的体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方面的立法经过了由活跃走向成熟的阶段。其有关经济技术开发方面和引进外资方面的立法占据了地方立法的主导地位。如1992年—1999年底,深圳市制定地方性法规144项,地方规章120项,其中90%是有关市场经济和城市管理的立法;1993年—1997年浙江省制定地方性法规157件,其中经济方面的法规占立法总数的50.3%。[3]

1992年-1994年各地地方性法规数量比较[4]
可以看出,经济比较落后的宁夏、海南立法数量较少,而且经济性法规所占比例要明显多于其它省市,如果把海南比作中国在地方立法发展阶段的 “过去”阶段,把上海比作地方立法已取得一定成效并日渐成熟阶段的话,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经济起步较晚或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其立法重点仍在于经济立法,当经济已经取得一定发展,其立法重心会相应偏向于社会管理方面的立法。这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不再仅仅盯着“经济”这一条标准来衡量社会的发展,而是更多地关注起社会管理、治安等社会性事务来,地方立法因而有了新了发展趋向。

长春地方立法比例统计(1992年-2001年)[5](p108)
由此表可以看出,在长春市,1992年到2001年十年间,社会性立法总数占年度立法总数比例中,最低的一年是1998年,尚且达到34.5%,而最高的一年即1997年竟达到了58%。表明地方立法越来越多地关注于社会性事务。这也体现了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理念。
四、地方立法权扩张的政治后果
地方立法权限不断扩张造成的主要社会影响是权限划分不明的问题。一是不少地方在实行立法的过程中存在着越权现象,对本来应属于中央立法范围的制度(民事诉讼制度、刑事处罚)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比如,《福建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暂行规定》竟规定了刑罚,“阻挠女适龄儿童入学的父母或者抚养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按照虐待妇女儿童罪论处。”[6](p62)二是各地方人大与政府间立法权限的不明。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地方性法律被称为地方性法规,而地方人民政府所制定的叫规章。正常情况下,地方规章的依据应该是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地区的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的效力要低于地方性法规,然而从我国地方立法实践来看,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并非全部真正掌握在地方人大手中,有的地方人大并没有发挥好其立法权力,反倒是被当地政府“抢了风头”,使得规章数量大大多于法规数量,而且甚至还存在不少由地方政府部门草拟地方性法规的现象,使得政府代行了人大的立法权,让政府部门利益披上了合法外衣。这种现象是因为长期以来,地方立法项目建议主要由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然后综合平衡形成立法计划或者规划,这样,行政部门具有全面掌握本系统、本行业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资源优势,而地方人大代表是兼职,是“业余”的,只是在开会期间才聚到一起,并没能发挥其“收集民声”的作用,在信息上就失去了“先机”,最终导致一些立法权被政府部门“抢夺”。[7](p67)三是地方立法争权、弃权现象屡见不鲜。被争夺的立法权是宪法或者法律明文规定属于中央的立法权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使的立法权,大都是一些有关收费、罚款方面的项目,而地方立法的弃权却和争权恰恰相反,多是那些“无利可图”且比较麻烦、琐碎的管理事项。
此外,地方立法中存在的混乱和差异现象也对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地方立法是对本辖区内的人和事产生调整作用,这就难免出现这种情况:在某一地区从事某活动是违法的,而在另一地区却是被允许的;某一地区的公民享有这样的权利,而另一地区的公民却不享有这项权利。比如,2002年11月开始实施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一法规的出台在当时我国各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广东省、四川省有关部门都表态不可能效仿吉林省开放 “未婚生育”。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发展极不平衡,就在吉林省讨论“单身女性生孩子”事情的时候,有些偏远省份可能要解决当地人越穷越生的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混乱,就不免会出现一些为了生孩子而特地落户到吉林省的现象。[8]
在出现以上问题的同时,不少人对中央越来越多地下放立法权的做法产生这样的焦虑:地方立法权限的扩大是否会推动我国国家结构形式向着联邦制度的方向发展?是否会动摇国家的统一性?
通过本文以上对于我国地方立法现状的分析就可看出,地方立法虽然貌似包罗了地方事务的方方面面,但却没能涉及到国家根本属性问题。《立法法》限定了地方立法的范围,有些事项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只有法律才能做出规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能涉及;有些事项属于中央的专属立法权,地方性法规不能加以规定。比如,有关国体、政体的法律规范,有关司法制度、刑事制度的法律规范,有关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的法律规范,有关与世界组织规则相衔接的法律规范,如此等等都是地方立法的“禁区”。而地方立法多是关于经济、社会管理的,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目的的。由此看来,目前我国地方立法的发展尚不会对国家的单一制产生威胁。
在我国,强调中央权力在立法上的权威性仍然是立法体制中不可动摇的原则。笔者不对中央立法权限一一列举,只对中央专属立法权的事项加以明确列举。所谓“专属”,即只能由中央立法,地方不能立法。凡属于中央专属立法权范围的事项,不管中央是否已经立法,地方均不得进行立法;凡中央专属立法权范围以外的事项,在中央立法以前,地方根据实际需要可先行立法,但一旦中央进行立法,地方的立法不得同中央的规定相抵触。[9](p66-67)这些都十分明确地保证了中央立法的权威性。
考察中央地方间关系,必须理清党政关系,因为党政关系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基本入口。我们考察国家结构,不但要理解宪法上的规定,更要解读党章上的规定。[10]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一府两院”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的职权之一是 “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以上表述说明了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中的单一制性质。同样,对于党章,每一个党员耳熟能详的规定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为了确保“全党服从中央”,党章及其相关文件规定了党委制、党组制、归口管理制以及党管干部制度和原则。根据1998年中共中央颁布的 《中共中央管理干部职务名称表》,所有副省级以上的干部均由中央直接考察和管理,地方主要正局级岗位的干部向中央备案。其目的就是遏制地方主义,加强中央权威,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可以说,在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时刻没有忘记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以保证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立法权的下放不会影响到国家单一制结构形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经济方面。虽然以分权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但是经济生活中,中央政府的计划性调配权力仍无处不在。主要就表现在对国土资源的直接管理上。比如中央政府对矿产资源享有直接的计划性质的调配权。而且,中央对项目投资同样有直接管理权。当投资项目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都需要国家发改委的批准。虽然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从80年代的以行政手段为主变为了以经济手段为主,但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有效作用时,中央则会毫不犹豫地运用强制性权力。江苏的“铁本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五、基本结论
西塞罗曾说过:法律创设的目的在于公民的安全、国家的防务以及人类生活的安宁与幸福。那些最初制定这种法律的人要人民相信,人民的意愿被写进了规则并使其生效,一旦规则被接受和通过,将会使人民过上尊严和幸福的生活;当这样的规则得以制定出来并发生效力的时候,人们就把这规则称为“法律”。地方立法也是国家立法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央立法的延伸,是以其灵活性和变通性起着规范当地人们生活并保障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多元化发展,都需要地方立法发挥其整合国家、社会的作用,然而其作用的有效发挥还有赖于国家更加合理更加深层次地下放权力。可以说这是一种双向推动的关系,即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地方立法发挥其功能,而地方立法的良性发展也会推动国家的发展。
总之,目前我国的中央地方间的立法实践可以说是“形散神不散”,地方立法要做的就是紧紧围绕中央立法的意志以及精神,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立法权力的下放,仍然是现在我们国家发展民主政治、保障经济活力的不二选择;关于地方立法权的问题不是放与收的问题,而是如何放好的问题。当然,立法权的下放也并不意味着地方拥有的立法权力越多越好,权力越大越好,而是应该本着充分发挥地方立法自主性、以权力行使适应经济发展并增进社会福利的心境继续探索并取得完善。
[1]刘鹤挺.新中国立法体制的嬗变及发展[J].攀登,2003,(03).
[2]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3]崔卓兰,赵静波.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7卷,第2期.
[4]孙琬钟.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性法规汇编:1992-1994[M].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95.
[5][6][7]崔卓兰,于立深,孙波,刘福元等.地方立法实证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8]案 例 来 源 于 http: //health.sohu.com /16/92 /harticle17269216.shtml[EB/OL].
[9]胡建淼.公权力研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10]杨光斌.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新论——理论、现实与政策[J].学海,2007,(01).
(责任编辑:徐 虹)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Expansion of Local Legislative Powers
Luo Ga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central-local legislative authority,to illustrate that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Local Legislative to be exist.It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oriented and the democratic reform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local legislature's expansion,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tion of the local legislative by facts and figures.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local legislative authority's expansion are analys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mpact,and the result is that it will not be a threaten for the nation's single structure because of central legislative authority,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ensur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entral issue should be “how to delegate the legislative power”,not “whether decentralize the legislative power or not”.
local legislatve;legislative system of China;state sructure
D920.0
A
1007-8207(2012)07-0094-05
2012-03-09
罗干 (1988—),女,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