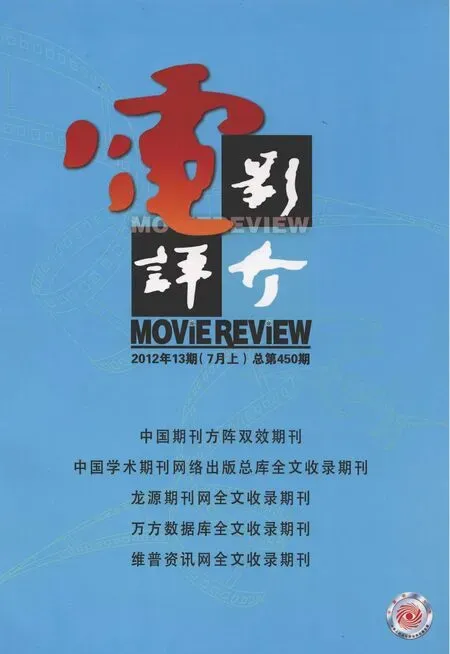影视小说:中国文学的畸形儿
在《小说评论》二零一零年第五期“彭学明专栏”中,作者发表了一篇题为《影视小说:中国文学的新生儿》的文章,对影视小说的“出现与定位”、“特点与长处”、“弱点与出路”进行了逐一分析后,认为“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影视小说前途无量”,“这种影视与文学共生共荣的局面,将越来越多地被作家和出版家及影视工作者所接受和追捧,并将形成中国文学泱泱浩浩的盛世景象。”
诚然,近年来伴随着一部影视剧热播、同步推出根据影视剧改编的影视小说的现象出现,电影电视从来是从文学台本中脱胎换骨的传统被逆转。作者首推“影视小说”概念的敏锐程度无可置疑,其期待“中国文学泱泱浩浩的盛世景象”的热诚之心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新生儿”的价值有多大,生得是否健康,能否延续文学的生命甚至传宗接代,其长处是否真正为“长处”,其弱点是否真正可“克服”,其是否能满足作者“盛世景象”的期待,作者笔下的“网络文学”、“博客文学”(笔者认为“博客文学”应当属于“网络文学”的一个部分,二者并非平行概念)、“影视文学”的飞速发展,“在挤兑了纸质文学的生存空间后”,是否真正能够“更多地拓展了整个文学的空间,丰富了整个文学的内涵,给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都仍值得商榷。
追根溯源,首先从娘胎说起。影视小说的诞生究竟是文学品味使然,还是商业利益驱动?从影视小说紧追蹿红影视剧的步伐中可以看到答案显然为后者。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不是关键,无论由何种动力所催生,影视小说照样体现了“英雄结,儿女恨,生死别,烟火味,世俗情”[1],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那么再看一下影视小说的发育情况。
影视与文学各有其文化品格与审美特征,也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向怀林对影视与文学作出如下分析,“影视是当代高新技术与社会文化心理的产物,它以逼真动人的直观形象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仿真世界,让我们在真切、直接地把握世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文学难以企及的视觉愉悦;而文学则源自人类的自觉精神与诗意情感,它以丰富可塑的思维形象为我们营造出自由联想与心灵驰骋的诗意空间,让我们在朝向心灵自觉与精神超越的同时,也将我们引向影视艺术难以达到的审美高度。”[2]可见,影视与文学虽然有共同点,但仍是各有侧重的。
反观影视小说,它作为文字印刷品,夹杂着多幅彩色或黑白的男女主人公剧照,囿于文字的局限性,脱离了导演、演员、美工、音乐、摄像等集体的艺术劳动。而影视的审美价值很大一方面体现在“技术之美”上,也就是说,技术是使其负载的审美意蕴得以尽显的手段,影视艺术离不开所依附的技术场。而影视小说恰恰是脱离了这个技术支撑,使影视艺术不复存在。而在此基础之上所建立的“再现之美”和“感官愉悦”更是无从谈起。由此看来,影视小说仅仅是附丽于影视创作的外壳,作者所谓的“完整地体现了影视的特色和优点”之说没有足够的依据。
但是彭学明对影视文学在文学方面的欠缺性做了很好的阐述,如“大多数影视小说虽然注重了情节的设置与好看,注重了人物的刻画与塑造,但却忽略了文学其他方面的艺术元素,特别是忽略了语言的质感和叙事的美感,从而损害了文学的艺术品相。语言缺乏灵性,叙述缺乏绵密,是影视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和克服这个弱点,作者并没有提出一个好的方案,只是举了毕飞宇的《玉米》为成功案例以供参考。问题是,毕飞宇的创作并不是作者所谓的“影视小说”。毕飞宇从成名之作起就受到了影视文学的潜在影响,具有一种潜在影视创作情结,“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形成惯性就很难说了。”[3]即便我们在这里肯定了毕飞宇,肯定的也是他具有影视情结的原创小说对影视创作的推动作用。作者将其作品与自己在文章开篇定位的“根据影视改编过来的小说”混为一谈着实不妥。尽管“毕飞宇的语言叙述,为影视小说提供了榜样和蓝本”,但是细想开来,一部影视剧的热播后影视小说必须马上跟上,趁热打铁,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市场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火候等待众写手们的“细细酝酿”?莫说“十年磨一剑”,“一年磨十剑”都可能一不小心来个赶不上而成了明日黄花。粗制滥造似乎成了必然。
丁帆没有明确“影视小说”的概念,但是他对影视小说存在的合理性作出了判断,“当下的中国文学仿佛进入了一个怪圈,正因为视觉艺术的冲击力是巨大的,所以才屡屡出现先生产电视剧,然后回过头来再改写成小说的这种违反文学创作规律的事情来,这种‘次序差’虽然违反艺术规律,但是它却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因此,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4]虽然影视小说可以满足书商的利益需求,可以满足大众消费群体中的一次性文化消费,但这都掩饰不了它以市场利益为推手,由影视与文学杂交而成的“怪胎”身份,这样一个既背负经济压力、又欠缺文学内涵的“畸形儿”太过孱弱,它该怎么去完成“形成中国文学泱泱浩浩的盛世景象”的巨大使命?不得而知。
不否认作者所认为的影视与文学可以共生共荣的观点。“影视剧的热播,往往会给小说插上腾飞的翅膀,让小说走进更多人的心中”(当然,这里的“小说”,我认为应该指的是原创小说),而且“电影文学剧本和电视文学剧本,融文学性和戏剧性为一体,具很好的文学品相与戏剧品相,为影视的再现提供了最好的蓝本”,这些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作法有助于影视与文学形成积极互动的良好关系。具有良好思想内涵、普世价值导向、高尚审美价值等积极因素的文学、影视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认可并带来经济效益——这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理想且美好的局面。
但是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商品化的时代是讲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文学创作也同样不能避免,这一个对文学来说是致命打击的灾难。”[5]消极影响的其中之一便是影视小说这种快餐式作品的大量复制;其二是使部分作家形成习焉不察的“屏幕情结”、“影视情结”。“创作中的画面感强化了,而矛盾冲突和任务性格相对弱化了,屏幕情结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集体无意识’”,“当下,几乎是很多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受着市场的辐射和影响。举例而言,有许多作家在描写性的时候、在描写小说场景和任务细节的时候,都会潜在地考虑到将来的影视画面的效果与视觉冲击的效果,因为他们要二次出售,要寻觅电影与电视的市场需求”[6]。这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文学创作的本来面目。无怪乎学者痛心疾呼:“他们消灭的是文学经典化创作过程。延伸,延伸。……不断地延伸;拉长,拉长。……不断地拉长,文学的叙述性文本在这个时代里和电视剧那样为了追求利润而浩浩荡荡不断地复制着,我不敢说它们大多数是垃圾,但是,我敢说它们当中很难产生出传世的经典之作。我们在不断地呼唤着大师的时代,然而,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大师死亡的时代!作家靠的是作品,而一旦作品成为商品,它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7]
“当代文学正在呈现出一种既缺席,又在场的吊诡命运。” [8]一方面文学作品的阅读者大幅减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畅销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动漫、网游,成为视听文化的内容和‘脚本’” [9]。当代文学产业化的趋势也初见端倪:葛红兵在上海大学牵头成立了“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致力于为“图书出版业、动漫产业、影视产业、报刊业、新媒业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文学创作者和创造性文案的撰写者”;郭敬明和他创立的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功运用市场模式运作,成为青春文学产业的佼佼者;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建立“盛大文学有限公司”等等。一夜之间,80年前宣称的“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诗意时的消遣的时候”又回来了,文学的消遣与娱乐功能重新被挖掘。但是,经济效益的日益彰显并不代表文学又成为公共舆论的重要话题,文学创意产业的繁荣实质也不是文学的繁荣。新世纪文学面临的困境仍然需要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中解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强大的文化领导权诞生了,作家被纳入革命机器队伍,政治元素在文学中越来越突出,文学与生活应有的距离消失并随之覆盖整个公共领域,被赋予政治教科书、历史教科书、道德教科书的性能。这种情况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告以结束,其间横亘长达四十年之久。“所谓‘物极必反’,曾让社会敬畏、仰视并且耗费太多精力的文学,今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地被社会所冷淡以至轻蔑。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技术层面和作品水平,相较以往总的来说一直在提高,可是社会对文学的兴趣反而一直在下降。” [10]白烨用四句话对文学与文坛的实情作了一个基本描述:“传统在坚持,类型在崛起,资本在发力,格局在变异。” [11]观察者们也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无论如何,新世纪文学要想真正摆脱异态,归复常态,崛起一个“泱泱浩浩的盛世景象”,还有不短的路要走。
[1]彭学明:《影视文学:中国文学的新生儿》,《小说评论》,2010.5
[2]向怀林:《视觉愉悦与诗意空间——也谈影视文学不同的品格特征与审美功能》,《当代文坛》,2010.5
[3][4][5][6][7]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当代作家评论》,2010.5
[8][9]杨玲:《当代文学的产业化趋势与文学研究的未来——以青春文学为例》,《文艺争鸣》,2010.9上
[10]李洁非:《“超级文学”——认识一种文学形态及其影响》,《小说评论》,2010.5
[11]白烨:《新世纪文学的新风貌与新走向——走进新世纪的考场》,《文艺争鸣》,2010.6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