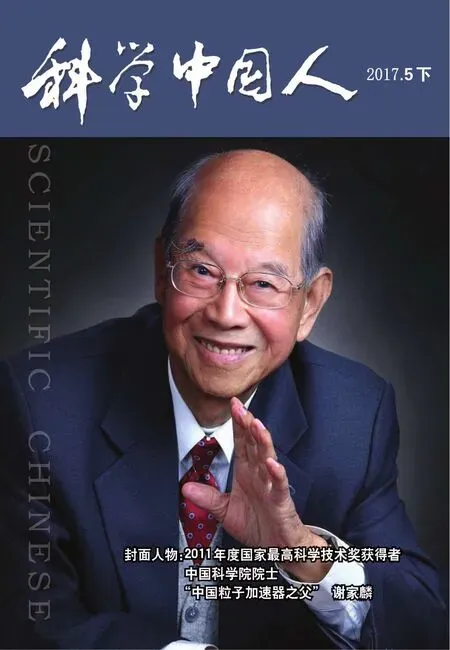我观当今中国高等教育
王义遒
我观当今中国高等教育
王义遒

专家简介:
王义遒,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波谱学和量子频标领域知名专家。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1年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早期在波谱学研究中发现了晶体和溶液中核磁共振化学位移的一些规律。后研制成我国第一台原子钟。他主持研制成的铷原子钟是我国唯一批量生产的钟。他的著作《量子频标原理》和《原子的激光冷却和陷俘》在本领域有重要影响。
教育是人间最有意思的事业,因为它的对象是人。人是世上最宝贵、最复杂、最活跃、最不可捉摸、最各不相同的。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保持人类的延续和发展,使下一代人活得比上一代人更美好、更幸福。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文化传承和创新,把上一代人的知识、能力、道德、信仰、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传递给下一代,并有所发展创新。这种传递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依靠下一代人自己的重构,其中还需要创造。这种重构能力是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秉性。但是,这种能力需要开发,是在一定条件下诱导出来的。这就是教育的使命。教育的极致是使人的天赋潜能充分开发出来,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教育的直接效果及于个人,通过个人,及于群体、社会,乃至全人类。这样,传承文化的教育具有功利性:使个人和社会、国家、人类受益。但是,人的个体和群体、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之间是有矛盾的,不都是协调一致的,因此,教育目标着重于个人还是社会,在具体实施教育过程中是有所不同的。在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上,这一直是有争论的,表现为“以个人为本”还是“以社会为本”,即“人本”和“社本”之争。主张“社本”的强调个人在整个社会机器中的“螺丝钉”作用,把人看成是社会发展、国家强大的工具。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他们比较重视专门人才的作用,因为这些人才可以被有组织地、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发挥“工具”作用。而主张“人本”的则偏爱人的自由发展,认为这样才能发挥人的潜能而更好为社会服务。两种意见此消彼长,往往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形势而变化。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看:清末初创时期,虽曾标榜“造就通才”,实际上看重“专才”,以服务于国家的坚甲利兵、救亡图存的目标;民初引进“科学、民主”新思潮,高等教育转向以“人本”为主的“通才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通才教育”思想遭受批判,“专才”教育大行其道;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狭隘专业教育的弊端显现,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应运而起。
以这样的背景来考察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看到,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我国已是世界上学生人数最多的高等教育大国;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近年来教育质量在逐步提高,尤其是随着科研条件的改善和有研究经验的导师增加,研究生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虽然还很不平衡。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将阻碍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的甚至会对将来造成严重影响。我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以下八点。
一、高等教育必须兼顾教育的人性和社会性
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界通过教育思想观念的讨论,复习了经典大学的理念,否定了那种过分功利、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树立了尊重个性的人的发展的观念,使教育从“制器”回归到“育人”的本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近年来正滋生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有的高校,完全从学校自身的发展出发,盲目求大、求全、求高层次,很少考虑社会的需要、与社会发展水平相衔接。他们重视了个性和“通才”,在注意“通识”的同时,却忽略了学生毕业后要适应社会人才市场需求的必要的专业训练,以致毕业后难以直接进入职业岗位。这是造成当前社会上“找博士易,求技师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高校毕业生太多了,而是“适销对路”的太少了。高校的办学定位、层次、类型、专业和培养目标还是必须面向社会,适应人才市场需求,而不能光顾自身发展需要,教育的人性与社会性要结合起来。
二、不能把教育看成是信息传递
教育通过传授知识、锻炼能力、养成素质使人得到发展。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包含了树立正确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思维方法等为人之道,和发展办事能力、处世技术等安身立命的本领。但是,知识要靠学生在获得大量信息的基础上自己构建,能力则是从实践中锤炼出来的。这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辅助、引导学生找出自己的学习门道。有的学校和老师以为把一些信息传递或通知给学生,学生就能掌握知识和能力了,这是误导。一些名师,如北大的黄子卿、复旦的陈建功等都是靠自己的学术与人格魅力启发学生思维和智慧来取得出色教学效果的,而不是靠他们能给学生“讲懂”。
三、要让所有学生都发挥主动性
人是多样的,教育不能用一个模子打造所有学生,学校要提供环境,让各种各样的学生都有发展成长的余地。这就要给学生以多次多种的选择机会,不能管得过死。实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转系、转专业就是一种提供选择的制度。现在有的学校规定,只允许本专业功课优良的学生才能转系、转专业,这里虽有些“苦衷”,但却是本末倒置的,本专业能学得很好的人至少也有一定兴趣,何必让他们转出去呢!学校的课程设置与讲授当然要面向大多数学生,但也要给少数学生留有充分发挥才能的余地,使他们早日脱颖而出。对于少数拔尖人才,应该让他们在崎岖道路上用特殊负荷的方式磨练出来。沿着学校精心设计的简捷道路,无障碍地“一帆风顺”出来的,只能是廉价文凭的拥有者,而不是能做出杰出创造性成就的人。为此,学校必须具有早期识别学生的能力。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都是在前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理学院叶企孙等名师早期发现,打破陈规在特殊道路下培养出来的。在目前中国大学教学条件下,这样的人能出得来么?
四、高等教育的结构、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要以质量为先
毛泽东曾多次严厉批评现代中国教育,崇尚书院式教育,这有一定道理。但现代教育是规模化的群体教育,要重新回到书院去,实行师傅带徒弟式的个体教育,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确互有矛盾。班级规模大了,老师不认识学生,也难以组织讨论,更难做到“因材施教”,杰出人才容易被埋没。上面说到的叶企孙先生办清华物理系,就规定每年招生不超过14人,却是人才辈出。现在高校以规模求效益,过度扩张,万人大学成为“小大学”,五万、七万有的是;班级规模动辄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同年级学生还不认识,遑论教师识学生,更不用说不同院系师生互相交流了。不同面向学校合并,说是为了学科交叉、文理兼容、资源共享,实际上学生在人海中遇到的基本上是“同类项”,院系馆舍相距甚远,“交叉”谈何容易。貌似先进的办学理念在不切实际的运作中化为乌有。从这个角度看,前些年大学的合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些学校规模扩得太大,标榜“学科交叉”的“综合”,却由于规模过大而妨碍交流,并造成管理“尾大不掉”,成本激增。
五、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比较专门的事,应由懂得教育的人来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现在不仅高校校长欠缺办学自主权,就是教育部也没有多少办教育的自主权。教育的重大决策并非来自教育部,不少要经过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经费划拨部门首肯。财政部的人不懂教育情有可原,具体到管高等教育,处长而已。但因重要专项经费出自财政部,他们就有权决策。比如,当前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引起国家领导和社会的关注,出台了“质量工程”专项经费。这本是大好事。但提高教学质量是非常细致的事,各校应根据自己情况,深入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如果财政部出了钱就有权干涉,“质量工程”必须在他们的审核下实施,追求有显示度和标志性的成果,这样的“工程”就不能不成为让各校申报,可以“量化”的“申报工程”、“数字工程”和“面子工程”。从长远来看,这反会摧残教学质量,因为当前教学质量的最大问题正在于学风和教风。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日益严重,成为高等教育的首弊。高校教师与学者成天忙于应付各种会议、申报、评审,以致没有充分时间来备课、做研究,影响教学质量;学术不端、学风败坏等事例层出不穷,都与此有关。
六、高校定位和多样化问题
多年来我国高校定位的高层化和趋同化倾向始终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与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和学校的举办者和办学者模糊不清有关。对于带有专门教育性质(即使对标榜为“通才教育”性质的高校而言,也可看成是专门教育的一种类型)的高等学校,笼统地把自己定位为“满足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明确自己的服务面向(全国、省区、行业、部门、领域等)、办学层次(专科、本科、研究生)、类型,在此基础上确定学科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等,使其毕业生适应人才市场的不同需求。根据人才需求的自然规律,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培养解决这些问题的精英人才的学校是少数;大量毕业生应当满足不同部门对专门人才的多种需求,以支撑社会的日常运行和发展。这样看来,把原来由各业务部委举办的高等学校通通收为教育部或地方举办的学校并非明智之举。这也使大学特色黯淡,变得越发趋同化。现在高校分成副部、正司、副司、无级别等不同行政级别,其政治与经济待遇又按级别、层次的划分而有巨大差别,自然就会鼓励高校不断升级上层次的趋向,极大地妨碍了大众化阶段最关键的办学多样化的实施,并且加重了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和衙门化。
七、大学的文化引领作用
从根本上说,高等学校是文化机构,具有教化作用。历史上,中国高校在引领民族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外来的科学、民主思想在高校虽然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却并未占文化的主流地位,继续高举这两面旗帜,使之真正贯彻仍然任重道远。这里还有一个与本土文化结合的问题。科学、民主思想无疑是建立于尊重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基础上的,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怀抱社会担当精神,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恢弘气度,崇尚“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了这种精神。这与科学民主精神两者是否矛盾,能否统一?应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包含中华元素、体现中国特色的新的世界文明,和如何构建这样的文明,是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文化任务,这是中国大学为世界文明做贡献的重要途径。
八、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迅速、变更动荡之剧烈与多端,为世界上绝无仅有,有丰富的经验和严酷的教训。这里有动机就错误,因而后果恶劣的,也有初衷合理而实际行不通的;即使在像“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荒唐的环境下进行的“教育革命”,由于有能思考的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参与,这里也有正反两方面的东西值得总结,而不可一概抛弃。教育教学改革学习外国固然必要,向自己的历史和实践学习,更为实际。新中国成立60余年了,我们应该认真总结60余年来的经验教训,使今后的高等教育改革走上更加坦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