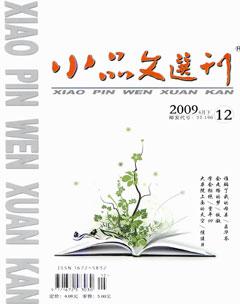鸟语浸染的村庄
浇 洁
腊月,流浪在树梢近一年的叶子,早已飘然落地回了家。寒霜瑞雪从天上飞来,给躺在地上的叶子酝酿着缤纷五彩的梦。鸟儿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从一户人家飞到另一户人家,雀跃鸣唱,像回魂的叶子延续着树的梦想。
如果说村庄是一棵树的话,那么村人就是携带着叶子灵魂的鸟儿。那一个个老人,就是腊月蜷着身子、坐在屋檐,无奈地望着同伴飞翔闹腾的倦鸟。
人有多少种,鸟就有多少种。乾坤宇宙总是先有鸟后有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鸟的痕迹在大地生存。也许有一天人没了,鸟还在天空继续着我们人类如歌如梦的行走。大部分人像平凡的鸟一样,只为觅食、养儿育女,奔波忙碌了此一生。村里的菜婶感叹道:“人这一世要过几样的日子。小时候在娘边撒娇时一样,出嫁后生儿育女时一样,如今老了又是一样。”鸟也如此,春夏秋冬的日子各不相同。
村里常见的鸟儿有:布谷、铁雀、麻雀、喜鹊、燕子、翠鸟、猫头鹰、鹁鸪、鹊鸲……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它们用不同的叫声,告诉村人许多生活的常识。过了清明,布谷鸟就“布谷……布谷……”地催促着村民撒谷播种。初夏时则昼夜不停地叫唤,那是引爱占巢,繁育后代。由于它的叫声在半夜听来,凄凉哀婉,“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似诉说着乡思,故民间有“杜鹃啼血”(布谷鸟,学名杜鹃)之说。翠鸟,俗称“栽禾鸟”,羽毛翠绿,喙长而直,生活在水边,爱吃鱼虾,故又称“鱼骨鸟”。每当农田犁耙水响,一片忙碌时,翠鸟便追在犁后翻转的泥土上啄食泥鳅、蚯蚓,高兴了,跳跃在田埂枝头用家乡话欢唱:“家家栽禾”“阿婆爬土旁”“勺子打汤”。原来它是在用歌声描绘生活的场景哩:栽禾时节,客帮邻助,壮劳力都下田劳作,家中只留年老的阿婆洗衣做饭。半上午,阿婆做好香软的汤圆送去田头。村里吃汤圆时兴“打豺狗”——见者有份。故常有阿婆爬田土旁送汤圆、众人争抢着“勺子打汤”的热闹场面。形如麻雀的铁雀,翎子有红、绿、黄几种,喙尖如三角铁钻。早出晚归时,“哆来咪嗦”地歌唱着,根据它的叫声,一般人都能写出谱子。斑鸠的叫声和鹁鸪相似,鸽子似的“咕咕”响,只是鹁鸪的叫声很有规律,并有“一咕晴,二咕雨,三咕发大水”之说。猫头鹰,家乡人称为“斗米鸟”,就是说它很能吃,一口气能抓食几只老鼠。它用七种不同的叫声,表示七个不同的时辰。拂晓时,用“啷啷啷……咕咕”的叫声告诉我们天亮了。近傍晚时,“哇……哇……哇”叫声凄厉,宛若婴孩啼哭,砍柴没下山,一个人听了,格外毛骨悚然。鸟是这样的灵异,常让我有人不如鸟之想。
在家乡赣东农村,最忌讳的不是乌鸦叫,而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喜鹊叫。它尾巴上翘,黑身的背和腹部间有白色。“洽~洽~”“洽洽洽……”叫声急促,尖锐响亮,拖得老长。据村人说,人将过世或遇有灾祸,喜鹊几天前就会在他家屋顶或门前叫唤,人一断气或灾祸已过,它的叫声便嘎然而止。它能闻出死亡或悲哀的气息?预言是照在暗处的灯,但村人宁愿在暗中摸索,也不需要这种晦秘的幽光。所以村里信奉的老人,只要听到喜鹊站在屋顶“洽洽”尖叫,便立马接声应和:“好事叫来,丑事叫去!”或用咒语驱赶:“乱铳打的!”“多嘴婆!”以此来禳灾祛祸。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命运有多少受预言支配?就像卜筮打卦,明知迷信不得,但还是爱听暖人的吉利话,趋附报喜不报忧。好话听了,甜滋滋的;丑话一出口,如谶语,钉子似的牢嵌入心。“不怕故意哇,就怕撞口话”,为此,村中还流传着这么一个典故:有一对夫妻,丈夫要出外,情急中老公穿了老婆的鞋出门。玲珑的老婆看见老公穿了自己的花花鞋,忙笑着祝福:“男人穿了女人鞋,今年一定发大财!”果不出所料,这一年,丈夫应了妻子的吉言,财源滚滚来。村中另一个男人知道了羡慕不已。第二年正月要外出做生意的时候,大清早故意穿了老婆的花花鞋出门。没想他老婆见了,张嘴就骂:“你死瞎了眼,病亡了神!”也巧,这个做丈夫的也应了他妻子的丑话,一年来病得卧床不起。可见,人脆弱的心是多么需要找个点来依撑,哪怕这个点只是一句美言。当这个点异常强大时,人便开始盲目地顶礼膜拜。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们这些诗人,总喜欢在宁静中沉湎于永恒的幻影,因此那些迷信的征象,也就和内心的感情有了共鸣。不仅是诗人,普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尽管喜鹊报忧,村民们又和又赶又骂,但他们仍相信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记得村中有个闻名遐迩的老中医,他号脉如神,深得祖传,只要他把药交给你,说一句:“吃这一剂,你不用再来了!”你的病便能如期痊愈,所以村人都叫他“号仙”。号仙家世代为医,祖业丰厚,当年被划为地主。他生有三个儿子,小名一蠢、二蠢、三蠢。他的三个儿子全坐过牢。三蠢帮生产队放牛,二头牛斗架,一头牛滚下垄,跌断了一条腿,因破坏生产坐牢。二蠢一次和几个伙伴比赛投石子,唯独他掷中了高高的喇叭,队里讲他对社会不满坐牢。大蠢老实忠厚,低头做人,二十七八好不容易定了一门远亲,挑了个一年中最喜庆的黄道吉日,农历二月十二——花轿日结婚,这是个种石头都能开花的好日子!可结婚前二天,喜鹊不时地在他家房前屋后叫唤。他奶奶惶恐不安,一听到喜鹊叫便对着它张嘴开骂,拿石子砸,提竹篙打,以求避祸。可等到花轿日张灯结彩办喜事,新娘接来,爆竹喧天,准备开席时,警车还是“突突”开来把他抓走了!原来村里有一头牛因吃红花草里的斑马虫胀死了,村人一致指认是地主号仙的大儿子阴谋害死的。谁叫他号仙那么有钱,看病不一剂见效,忽悠我们贫下中农呢!最可气的是,我们种田人扶犁打耙节衣缩食的时候,号仙还养有一只八哥,喂它喷香的鱼肉!那八哥被号仙调教得异常伶俐,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八哥不用笼子关养,号仙走到哪,它跟到哪。看完了病,号仙伸出手掌,叫一声“四喜”,它便“扑愣”一声跳上他手掌,用号仙的嗓音说一句:“天下太平。”号仙笑呵呵地摩挲着它的羽毛,珍爱如宝。大蠢出事后,村人对喜鹊能预言祸患越发深信不疑。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实行计划生育,明福才站出来为喜鹊说好话,说喜鹊能报喜。一九八九年的一个清早,明福夫妇还睡在床上,关门闭户的,不知从哪飞进一只喜鹊,绕着他厅堂“洽洽洽”欢叫。原先可从没有过!中午,他老婆就帮他生了一个胖小子。过了二年,他老婆保胎扎,挺着大肚子的时候,又有一只喜鹊像上回那样到他家欢唱。明福当即高兴地和老婆说:我们今天又要生儿子了哩!果然,当天晚上,他又抱了个胖儿子!明福他家可是几代过继单传啊,独独在他手上喜鹊送来了二个儿子。他能不笃信吗?
村人一致认同的报喜鸟,是鸦雀。鸦雀黑翅白肚,形如乌鸦。如若它在你面前,“吓吓吓”地欢叫几声,你家就有喜事临门。我母亲听得更仔细,说鸦雀一叫凶,二叫喜,三叫福。如果清晨开门,母亲听到鸦雀喜气洋洋地欢叫,她这几天都是笑嘻嘻的。人,谁不是跟自己的心情过日子呢!鸦雀是一种很灵性的鸟,看它的巢,我们能提早知道天气。鸦雀爱把巢筑在村头高高的枫树上,冬天的枫树光秃秃的。如果巢低,说明今冬有大风暴雪;如果巢高,则风和日丽。鸦雀虽个小,却很勇敢,二只鸦雀能斗过一只老鹰。只要见到老鹰偷村里的小鸡,邻近树上的二只鸦雀发现了就会赶来,“啊,勺勺勺”鸣叫着,冲过去,非常默契地一边一只钳住老鹰,老鹰居然不敢动,只得放下小鸡逃跑,而此时树上的乌鸦就会“哇哇哇”地评判。村人感激鸦雀,说老鹰是贼,乌鸦是清官,鸦雀是侠客。尽管事实上它们都为争抢食物而来。
在所有鸟中,只有燕子和人格外亲近。不知从何时起,燕子和人形成了一种相互信任的亲情关系。燕子是家鸟。燕子是村人的女儿客。村人不养鸟,更无闲遛鸟,因为整个村庄的鸟都是他们的,抑或说,偌大的一个村庄都是鸟儿们的。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是鸟的娘家。可不是么?每到花轿日,(家乡人把二月十二称为头花轿,二月十五称为二花轿,二月十八称为三花轿,一年中,这三个日子最适合婚嫁迎娶。)燕子就像坐着花轿的新娘子准时来到我家,“叽叽叽叽”带着新春的气息,绕着厅堂鸣欢筑巢,它的叫声细细听来宛若童谣:“不借你的油,不借你的盐,只借你家梁上产个卵。”从二月十二头花轿来,到七月二十七白露离开,燕子有近半年时间在我家早出晚归,生儿育女。我吃饭,它喂食。我说话,它叽喳。它占据我家厅堂横梁,在上面吃喝拉撒。有时我端了个碗吃得好好的,一不小心,一撮白屎拉到我头上甚至我碗里。我火了,骂它赶它,拿起棍子要捅它的窝,母亲见了就会笑着责备:燕子打老远赶来,辛苦走啊!捅了窝,它到哪安身?你再捅,来世变成燕子没有屋住!有时在气头上,即便捅了它的窝,它好像知道自己错似的,又悄悄在屋梁一侧搭起了家。实在拿它没办法,父亲就会拿竹篾在燕窝下搭一个平台,这样既可以挡住燕屎,让我们安心吃饭,又能让燕子回家站在平台上栖栖脚。燕子一家老小张着嘴叽叽喳喳叫得更欢了!
村人和鸟儿和睦相处,故村里一年四季鸟声鸟影不绝。他们相信,如果你虐待、逮杀了一只鸟,四里八乡所有的鸟都会知道。一个农人家里,如果没有燕子做窝啁啾,这家人多半不怎么景气,连村里小孩都不愿到他家玩耍。
村里的鸟儿是村人的兄弟姐妹,相处久了,各自的脾性皆心中了然。村人为了教育后代,编排出许多有关鸟的故事来警示后人。我印象最深的有二个。一个是规劝儿媳孝敬婆婆的。那个用蚯蚓冒充泥鳅煮面给瞎婆婆吃的刁妇,一命归西后变成了田间山边常呼“苦哇”的鸟儿。而吃了蚯蚓煮面呕吐不已的瞎婆婆,知道真相后,伤心气绝,第二年成了村头树上老叫“吐哇”的小鸟。另一个则告诫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人。从前,有位拐脚、驼背又独眼的残疾人学打铳,半辈子也没打到一样东西。一天,拐子扛着铳,看见一只山鸡在田里吃瓜,端起铳来打。不料山鸡开口讲话:“你打了半辈子铳都没打到什么东西,今天料你也打不到我!”拐子听了火冒三丈,拿起铳用力一扣,结果连山鸡的毛都没打着。这下可把拐子气坏了。第二天他很早就躲在暗处,等山鸡一下山,对着打了一铳,把山鸡脑袋打开了花。山鸡不服,魂溜到阎王那告了一状,说拐子暗害它。阎王把经过听了一遍,拍案骂道:“你这该死的鸟!拐子,驼背又独眼,他都看见你,你还没有看见他,还有何理来告状?”
回想起这些故事,脑中每每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孩子像故事中的山鸡似的追着村里的王癞子,一边嘻笑,一边喊唱:“癞子壳,扁担砍,砍出油来炒豆壳!豆壳喷喷香,捉到癞子打一枪!”王癞子忿然地望着这一群孩子,只得无奈地摇摇头。而村中王细毛的妈仿佛吐哇鸟的样板。细毛刚生下不久,父亲就不幸去世,细毛的妈含辛茹苦把儿子养育成人,并给他娶了媳妇。没想细毛娶了媳妇便忘了娘。老屋拆后细毛盖了栋新瓦房,媳妇不让妈住。老人没地方窝身,只得睡在猪圈里。前几年,听说细毛的媳妇得了一种怪病,发起病来就躺在猪圈里。村人背地里议论,这是活报应!
像猫头鹰、喜鹊、鸦雀、鹁鸪、翠鸟等犹如村里的精英或另类。他们是村庄的精魂,赣东大地的先知先觉,精神高地卓尔不群的寂寞者。村里最常见的鸟儿就是尖嘴麻雀了,从早到晚、一年四季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它老实、本分,却不乏农人的狡黠,村人俗称“奸雀”。小孩在一起喜欢这样唱它:“奸雀崽,捡择大,二十七,才想嫁:嫁屋顶,它嫌冷;嫁树梢,怕风摇……”它们怕孤独、爱扎堆,常一大群一大群,此起彼伏地起飞、降落,吃谷粒、啄菜叶、扒虫子。偷吃东西时,它们像人一样,也有探路、留守、望风。它们多像村里比邻而居的村民们。劳作了一年,腊月农闲的时候,他们好不容易被升到窗前竹篙上的太阳催醒,磨蹭着懒懒地爬起。扯了屋旁现成的茅草引火,“叭叭叭”引燃。吃好热乎乎的早饭,生好热炭炉,把饭菜捂进稻秆扎成的笼箱里,裹好旧棉絮捂严,中午一餐就可吃现成。空下那么多时间,他们便叽叽喳喳地围着火炉晒着太阳,扎成一团张家长李家短地唠嗑。
这一天,太阳绕过屋壁,红红地趴在每个人的脸上。霜风乖巧地藏在村后背阳的山坡里。话茬子像笼里的炭火,暗了一会又被谁撩起,隐隐地亮着。菜婶说,前二天到县城,看见一个拉二胡卖艺的瞎子,很像多年前坐牢便消失的大蠢。那二胡拉得韧啊!你走出老远,心还被它牢牢地牵着,怎么扯都扯不断。菜婶放心不下,来来去去硬丢给他十块钱。
当年斗地主的花样可真多:挂牌游街。戴高帽开批斗会。把二个大拇指夹扎在一截细木棍上,用锤子往木棍上狠狠地加尖。让号仙等几个地主跪成一排,提一双破鞋,照脸上“啪啪啪”一溜响过去……大蠢被抓不久,号仙在难以承受的悲苦中,吞下自己熬的中药安静地去了。二天后,号仙出葬的日子,他养的八哥也绝食而去。
斗过号仙的后生,如今的老人们,被如烟的往事笼住,冷灰似的静静晾起了话题。不知谁耐不住沉默,从炉边站起嘟哝了一句:好久没听到燕子叫了。
是啊,腊月一过,一晃,花轿日又该到了!
选自《天涯社区·散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