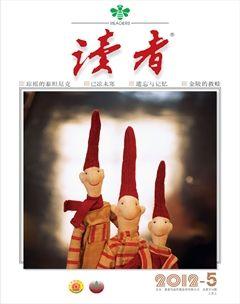和你在一起
素猫

一
感谢今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还原了真相。
7月26日,我从出差地北京回广州。因为没买到直航的机票,又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
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长沙。从长沙飞往广州的飞机,等了足足3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外面暴雨如注,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妈去。
到家时,担心老妈已经睡了,我直接掏了我的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地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漂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
一个人在外面又苦又难觉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老妈的这句话,像她说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在了脱鞋的动作上。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灰白夹杂,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曾经年轻的她总是要揽着我的肩膀,带点嘲笑地指指我的头顶,说还够不到她的下巴呢。她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瘦小单薄了呢?
屋里潮湿又黏腻,大概是出了汗,她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墙壁上那只模样老旧的石英钟在走,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她惊了一下,转过身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接着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
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成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
二
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
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怕老妈无聊,特地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500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的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欢声笑语。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发现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
我走上前,拍拍妈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感觉到主任有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七八千元一下子减到了两千多元。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氣,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爸爸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样欲盖弥彰地放大了声音说:“不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2000块钱,我给她的那500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一起住过。不过,自从从广州回去,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电话打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每次听到她在电话那端快活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她说,她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要把以前亏欠的日子给补上。我举双手表示赞同。
可是,在这个因大雨滞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妈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吗?
三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
“吃吧!”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
我给她打电话:“走了。”她嗯了一声:“走吧。”
9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我的行程安排,我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10点,她去了菜市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市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市场,她就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猎猎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
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随儿女举家迁去了沿海或发达城市,她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越来越少。我怎么就能轻易相信她描述的那些生活呢?
中午1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驼起。风吹起来,她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在风里像一把稻草。
这时老妈终于起身活动。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很多。她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啊说,我远远地看着她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她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她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
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
四
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说话的人都没有——原来什么都没有。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哪!”我塞给她一张20元的钞票,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你怎么没走呢?”“你看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啊?”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说:“唉,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参加活动,但就是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劲。”
我陪她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我看着墙上的钟,它还是滴答滴、滴答滴地走着。这一刻,我和她就像是站在时间的两头。我正年轻,她却已经老去,一点点地,老得像一个懵懂的小孩。
那天晚上,我陪她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地,跟她回忆以前的事情。她睡后,我偷偷打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打定了主意,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在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地隐瞒和思念。
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她一万个不愿意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她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快,提着,跟我走!”
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时间一点点地找回来。
(辛普摘自《女报》2012年第1期,张 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