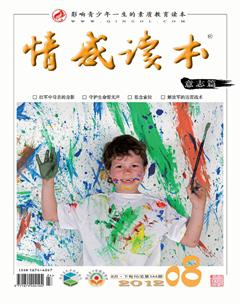浦稼祥有颗很大的动画心
王京雪
前几年,浦稼祥应邀去大学讲课,介绍他的人说:“土地公公来啦!”他听了颇感有趣,如今再想起来,脸上也还带着笑意。
动画片《大闹天宫》里,土地爷是个出场时间不多的小人物,但浦稼祥让他被人们记住了。
1952年,20岁的浦稼祥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动画科毕业,开始了其专注一生的动画事业。从1955年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到被誉为开中国民族风格动画片先河的《骄傲的将军》,再到后来的《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葫芦兄弟》……他参与过众多影响了一代人的经典动画的动画设计,也导演了《松鼠理发师》《老虎装牙》等不少片子,并以精于动画角色塑造、尤其是小人物及反面人物的塑造为业内人士所称道。
2012年,80岁的浦稼祥还在忙,刚从上海赶来北京开了一天会,又和老伴匆匆奔赴青岛,应已为人师的学生所邀,准备去给动画专业的孩子们开一个月的课。他乐于跟爱动画的人讲这些年来自己的成败经验,讲他对中国动画的思索和期待,热情而直率。
他画了一辈子小人物,却有颗很大的动画心。
小人物何以能刻画得活灵活现
在浦稼祥看来,没有能随随便便画的角色,即使是小人物,其一举一动也都有道理所在。
在动画片《骄傲的将军》(1956年)中,浦稼祥塑造了一个跟在大腹便便的将军背后,弯腰塌背,手执折扇,善于阿谀奉承的食客形象。为刻画这个人物,他考虑再三:“食客是什么?是专门拍拍马屁捧捧场的小人物,做了这个定位,人物动作就出来了。比如走路,他和挺着肚子、骄傲得很的将军是两码事,”他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比划,“两脚一弓腰一弯,他是这样走路,完了小扇子一扇,捋捋胡子,一张嘴:嘿嘿嘿嘿嘿嘿……他是这样的人物。”
由食客开始,浦稼祥相继在多部影片中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形象。
到动画片《大闹天宫》时,他负责画的几场戏有孙悟空与管御马监的马天君冲突、孙悟空斗哪吒、孙悟空回花果山自称齐天大圣、孙悟空蟠桃园遇土地、孙悟空72变鏖战二郎神……刻画了其中的孙悟空、土地和一众天兵天将等角色。
其中,看守蟠桃园的红鼻子土地公公尤被观众们喜爱。无论是从土里拽着拐杖出来,还是一张嘴说话先要打个喷嚏,或是看到孙悟空要摘树上的蟠桃,又急又怕地窜上自己的拐杖头,手摆得似拨浪鼓……这个小老头憨态可掬,举止可爱,令人印象深刻。
回忆《大闹天宫》的几场戏,浦稼祥说:“画打戏我画得好累,画完了,自己蛮得意,后来问人家喜欢哪段,他说喜欢土地公公,这给我一个反思,为什么土地公公人家喜欢,打,打得我很累,我感觉很精彩,人家却觉得没什么。”
浦稼祥分析,刻画土地时,他是从分析人物着手,“土地是个小人物,孙悟空是大人物,小人物出来迎接大人物,他这里的心理活動生成什么动作和态度,我是从这方面考虑的。”
土地一说话就要打个喷嚏的动作,其设计也有来由。常年生活在地底不见阳光的土地从土里出来的感觉,让浦稼祥联想到,生活中有人看见太阳,头一抬就要打喷嚏,“那时我们住在华亭路,晚上睡觉听到有个人老打喷嚏,一打七八个,这是我的生活,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放在土地身上,让他见了阳光打好几个喷嚏,这很有趣吧?”
人们对土地这个角色的喜爱,让浦稼祥深刻感受到把握人物性格对塑造动画人物的重要,“什么是性格?人物的出身、职务、年龄,他在社会上碰上的种种事情形成了他的性格。设计动作就要考虑这个人的性格,要想入非非一点。”
唯唯诺诺的土地、傲慢无礼的马天君、被孙悟空打掉一个风火轮一瘸一拐狼狈逃走的哪吒……这些人物常常是出场的第一个动作,就让人感觉到角色的鲜明特色。
浦稼祥认为,想明白人物的性格,动作就能顺理成章地出来,以动作表现人物性格,人物也就活了起来,而这就是动画人物塑造的精髓所在。
不是只有水墨画才是民族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中国动画学派由肇始至辉煌的日子,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手段的应用为特点的中国动画,曾经享誉世界。
今天,民族化依然是国产原创动画的关键词之一,也是近年来一些国产动画频频遭人诟病之处。
作为中国动画学派建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浦稼祥非常重视民族化问题,他不断强调一点:“不是只有《大闹天宫》这样的作品才是民族化,也不是只有水墨画才是民族化,所有东西都可以为我服务,民族化是随时代发展进步的,现在有现在的民族化。”
“所有民族的东西都能为我所用”,对这个观点,浦稼祥举了自己给《大闹天宫》中神将六丁六甲从天庭下来所做的动画设计为例。这些神将由天而降只有两个镜头,“你猜不到我这个动作设计是从哪里来的,镜头很短,一下就过去了。但这个动作我是吸取了殷墟甲骨文里文字的形象,甲骨文有它的动作,我觉得很奥妙,就用在我的动作上,张牙舞爪得很。”
剧情、音乐、美术、人物的动作和性格……浦稼祥认为这些都是在动画中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重要元素。
尤其是动画人物的动作,他提到美国动画《功夫熊猫》,“你能说这是民族化的吗?它是利用了很多中国元素说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但它里面人物的动作是美国人的动作,不是中国人的,它的幽默也不是咱们的。再搞多些中国元素,它的人物也是外国的。”
一个道理,浦稼祥说,今天的中国动画也完全可以用新的绘画技术去画各种现代社会里的东西,画高楼大厦手机电脑,“但我们的人物始终是中国的人物,我们讲究人物性格,要刻画到人物内心里面去,与主要讲究动作的夸张的美国电影不一样。只要有这些民族化的元素,再怎么用新的方式画现代的东西,出来的也还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民族化是个课题,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东西研究不够。”尽管民族化一直是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的热词,浦稼祥仍然觉得再不好好地提提这个词,可能就要晚了。
一辈子的动画心
8、9岁时,浦稼祥第一次看动画片,看见银幕上出现一个大炮,本该向前打炮弹,炮筒却自己掉了个头往后打,这个简单的画面把他逗坏了,有动画片之前,他怎么也没想过大炮还能往后面发炮。自此开始,浦稼祥爱上了动画,去学了动画,最后一干干了五六十年的动画工作。
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退休下来,对动画的爱没跟着退休,尽管嘴里说着“年纪大了,动画这些事我就不去管啦”,浦稼祥还在关注国产动画的发展。
他看过一些片子,感到担心:“太浮躁了,这是个主要问题。”他回忆中国动画曾经的辉煌,说:“我们那时都觉得自己是搞艺术的,是搞艺术!不是为了钱。”
那时候,为给《大闹天宫》做动画设计,他和一群同事被送去京剧院和戏曲学院听戏学武打,蹲点蹲了3、4个月,从中体会出气氛和感觉,再用到动画里。那时,他们满怀热情,天天加班,疲惫不堪又乐此不疲。有一晚,浦稼祥下了班边骑自行车边琢磨动画人物,眼里看着路口的交通灯是红灯,却直直骑了过去,之后继续边骑边琢磨了一段路,才突然察觉:呀,自己刚闯了个红灯。
市场经济时代,十年磨一剑、细工出慢活的动画生产方式的确已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今天阻碍国产动画事业发展的最大绊脚石是重量不重质的趋利和浮躁。
浦稼祥说国产动画发展的另一个阻碍是动画教育。他去过不少有动画专业的学校,发现很多教动画的教师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又看到一些学生并不具备合格的基本绘画功底,这怎么行呢?他觉得这也是个大问题,应该多呼吁解决。
现在,浦稼祥每天都在写东西,每晚都写到十一二点。他想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都写下来,希望给年轻的动画人以启发。他曾经专门为做动画导演工作的人写了本工具书,出版社明确告诉他,这种书买的人很少,他们不愿意出。辗转多时,才终于被一个学校的出版社接受。
“我现在不管那么多,写下来再说。”他想写的东西还有很多。
如果今天,再让浦稼祥来拍动画,他会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我想从民族传说、民族故事里找能打动人的拍,我现在想拍艺术性比较强的东西。”其实这些年,浦稼祥一直没完全离开动画第一线。2002年,他根据古典民乐《月儿高》做了个动画短片,获过中国视协动画短片学术奖的动画音乐电视片优秀奖及导演奖,和2006年度中国动画学会奖优秀动画短片奖。
摘自《文化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