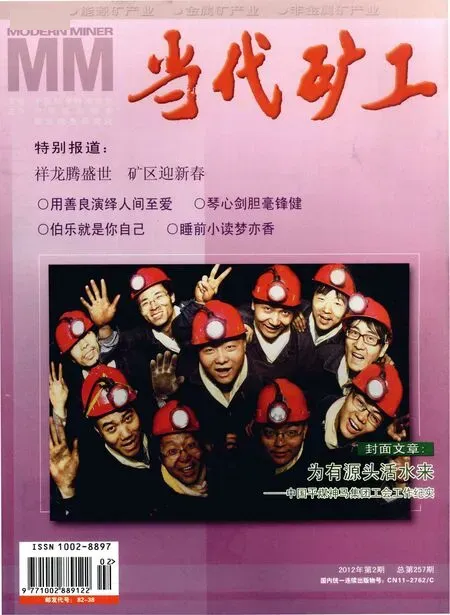纳西阿里里
□许翼鹏

两个水车,一大一小;两种速度,一快一慢。
它们是钟表上的分钟和秒钟,流水鞭策着它们,沿着时序的轨道,记载着岁月的年轮。
它们是银河中的两个星座,一个在顾盼有情地等待;一个在奋蹄撒欢地追逐。重合是玉龙雪山留下的童话,只有一米阳光将它们的剪影粘贴在一起,圆了它们耳鬓厮磨的梦想。
它们是纳西的象形文字,切割在水下的是月亮;抬起头,抛珠撒玉,挥汗如雨,难道不是对太阳的摹画?它们是歌赋中的长短句,让清亮的丽江水,在舒缓的基调上植进了明快的节拍;水获得了力量,像青春的常春藤,沿着茶马古道,亲密地攀缘、上升。水卷起了遥远的记忆,它们昭示着宇宙的秘诀: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水车们叽叽嘎嘎地对话:既如此,我因何匆忙,为谁忧伤?
水追寻着雪山的倒影,水车周而复始地诉说着古老的传说,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是谁承载着亘古的诺言?是玉龙雪山!她是纳西的保护神,她是生的源泉,她是死的归宿。不是吗?纳西人说:“有松树的地方,就有玉龙雪山;有泉水的地方,就能看到玉龙雪山。”无论远景、近景,无论不经意地一撇,还是深情地眷顾,她就在那里,她都在那里,她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诺言。看着她,心里踏实;守着她,生活充满阳光。“火把节上的阿里里,我会跳给谁?”丽江古城的广场上,夜夜都是火把节,人人都是阿里里。
音乐如初融的雪水,汩汩的,柔柔的,汇聚成小溪,流淌似激流,越来越明快,越来越欢畅,撩拨着每个人的心田,唤醒了每个人青春的热血。丽江的水受到音乐的激荡,奔涌到广场上,千万人成了旋转的水车。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人是坐标上的一个点,拉起手,坐标点成了水车的辐条,支撑起一个巨大的圆,阿里里的节拍搅动出音乐的风暴,巨大的漩涡风狂雨骤,潮起潮落,一层层,一圈圈。一会儿,你位于风暴的中心,一会儿你舞动在漩涡的边缘。
拉手,我们亲密无间;撞臀,你我没有尊卑。它们组成纳西舞蹈的基本元素,成为一个古老民族仍然鲜活的标志。雪山庇护着每一个生命,雪水滋养的都是生灵。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是大自然开出的美丽花朵,撞臀的语言,既是力量的宣誓,也是两个人才能领会的密码。象形文字记载着大自然的训示,没有对淫邪、污秽的会意。东巴文明像丽江水一样清澈透明,像大小水车一样各循其道,运转有序。洁白的雪山滋润着洁净的雪水,简约的思想孕育着快乐的种子。于是,歌舞就是纳西人的生活,或者,生活就是歌舞。
丽江的音乐,热烈奔放;纳西的舞蹈,激情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