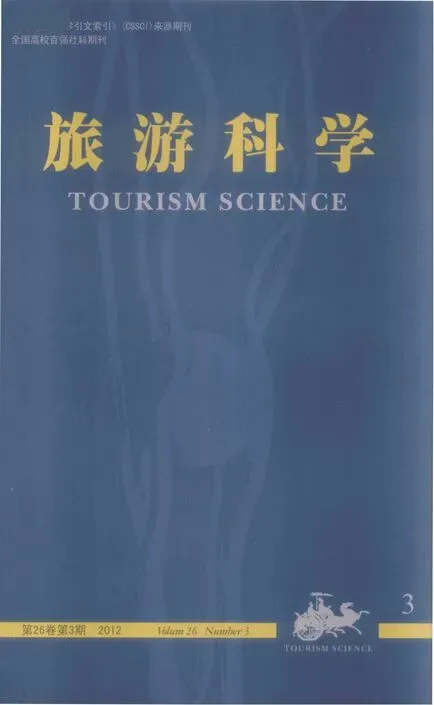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
王亚娟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1 引言
上个世纪末,中国旅游研究者在做目的地规划时,不再将关注的焦点局限在路线和基础设施的布置安排,而是将目的地居民也纳入规划的范围,将当地居民提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并指出其对旅游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保继刚,孙九霞,2003)。同时,社区参与的理论也被引入到中国的旅游研究和规划实践中。研究者提出,社区参与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发展规划的制定层面,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分配中,并且提出具体的利益分配方案,包括增加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社区居民优先被雇佣的权利及旅游商品尽量采用本地原料等。在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中,社区参与更多地被当做一种经济或技术过程,研究者普遍忽略了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而取得某种控制权的政治过程(刘纬华,2000)。在探讨社区有效参与的问题上,研究者们还忽略了有着自身独立利益的政府,当其自身的效用函数与居民的利益不是激励兼容的情况下,社区参与是无效的(左冰,保继刚,2008)。要让社区真正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就要改变居民的初始资源占有情况,改变他们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权利意识和管理技能而处于被排斥的无权状态(左冰,2009)。
增权理论的引进使旅游研究者将社区参与从经济、技术层面推进到政治层面。增权的最终目的是让社区获取权力并导致社会力量对比发生改变。Scheyvens(1999)明确指出旅游增权的受体应当是目的地社区,并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等4个维度的增权理论。在他随后出版的《Tourism for Development:Empowering Communities》一书中,他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第三世界的旅游社区,强调了政府、旅游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组织在旅游社区增权中的作用(Scheyvens,2002)。Sofield继承了斯切文思的4个维度的划分,但指出社区增权主要与社会维度和政治维度有关。Sofield强调,法律的增权比传统的增权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意义更大。旅游增权的目的在于增加社区福利,为社区产生社会资本,以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并建立起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合法权利框架(Clark,et al.,2007)。
中国的旅游增权研究开始较晚,保继刚与孙九霞(2008)在对雨崩社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指出: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增权,一旦有外来旅游企业进入,原来取得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将会被破坏。只有在制度层面上确立社区的权力,进行制度性增权,才能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确保雨崩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左冰认为在中国要真正实现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增权必须通过正式制度的供给,与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产权制度在中国发育不完全。在我国旅游开发中,资源所有权存在法律上清晰与事实上模糊的矛盾,产权问题造成社区在初始资源分配上的先天不足,这也成为制约社区参与旅游的最大障碍(左冰,2009)。只有从国家政治或法律层面上建立一套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支持性制度,才能切实保障社区参与旅游的权益。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增权主体在社区层面的推进,国家的宏观制度增权就有可能流于形式,只有在权利意识较强但其权利难以保障的社区,才考虑制度供给或制度优化(翁时秀,彭华,2011)。
制度性增权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现阶段社区参与旅游的实现明晰了政治努力的方向,但是相关研究停留在概念提出阶段的实践探索,并未形成系统的制度性增权理论,这使得相关研究难以突破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的框架,难以提出具有中国旅游实践特征的理论体系。
本研究首先需要明晰几个相关概念:制度、制度性增权、制度性增权的基本类型以及制度性增权的主体和受体。
2 制度性增权的相关概念
2.1 制度
美国经济学家道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到,“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杨瑞龙,1993)。制度被制定的目的,是通过提供一种行为准绳,为个人行为指引一个特定的方向,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North,1990)。制度界定了社会和经济的激励结构(North,1994)。
Ostrom对制度的定义较为全面,他认为:制度是一组运行规则,用以决定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中,谁有资格制定决策,什么行为是被允许的,什么行为是受到限制的;在决定什么样的规则可以被采用时,遵循的程序是什么,需要或者不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应该如何为个人的绩效制定相应的支付条件……规则应包含允许、禁止或者要求怎样的行为以及结果等条件。当个人在选择其行为时,依据的正是这些规则(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2006)。
制度被理解为一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以及保障规则被执行的实施机制。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是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等级结构;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周玮,2011)。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自身演化的能力。正如Popper(1957)所说,“你不可能构建出一个完备的制度”,因此在尽量更好地将它设计出来后,还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调整。因此制度是不断演进的,持续地改变着我们在行动中可能的选择(North,1990)。
制度的含义远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正式的成文法律法规丰富得多,它应该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设计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以及一般性契约。非正式约束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道德观念、价值信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行为规则(North,1993)。这种丰富性使得我们对制度性增权的类型进行划分时不得不考虑两种情况:正式制度的增权和非正式制度的增权。
2.2 制度性增权的4种类型
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增权的形式也并非是单一的,按照王宁(2006)的研究,“制度供给型的消费者增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还是间接增权的划分标准是,某项政策或法律的颁布是否以提升消费者的权力或权能为首要目的。由此我们可以将制度性增权划分为4种类型:

表1 制度性增权的4种类型
(1)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通过正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社区参与旅游并从中直接获利的权利。如加拿大的班芙国家公园就规定,只有原住民可以开设家庭旅馆,而外来购房者则不允许;迪拜则作出明确的限定,在当地开设公司和外来投资必须和当地人合作,使本地人从中受惠(杨晓红,2011)。这些法律都从正式制度层面确认了社区对当地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强有力地保障了社区在参与旅游开发时的权利,而我国目前并没有类似的法律法规。
(2)正式制度的间接增权
1998年通过的《村委会组织法》进一步尝试规范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调整了权力机构,规范了选举程序,对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筹资方式作了原则性的说明。这项制度虽然不是直接赋予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权力,但是因为村民在自治过程中有决定本村事务的权力,而当旅游开发涉及村集体利益时,村民有权力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村集体利益的村委会与旅游开发企业进行谈判,在中国目前缺乏村民经济组织和其他类型的合作组织的前提下,这种村民自治组织能较为有效地团结村民个体力量,形成合力参与谈判,因此作为正式制度的《村委会组织法》间接保障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权力。
(3)非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
香格里拉梅里雪山周边雨崩藏族村的旅游开发案例中,“轮流制”能够取代在牵马送客和家庭接待出现之初的“单体家庭行为”,成为村民们在参与旅游业过程中的规范和村民旅游经营、旅游产品交换、获取经济收益并进行分配的准则,正是因为雨崩村的村民对其藏族身份的强烈认同以及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共生共存”的普遍价值观,成为全村参与旅游服务认同的“普遍真理”(郭文,2010)。“共生共存”的价值观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其约束下形成的“轮流制”,避免了“单体家庭”在旅游开发中由于争夺旅游资源和利益导致的社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直接实现了社区集体旅游收入的增长。
(4)非正式制度的间接增权
我国的旅游开发多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乡村进行,由于长期以来的传统和政治现实,农村缺乏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合作组织,农民大多处于“散众”状态(陈志永,杨桂华,2011)。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社区组织,才能增加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间接地增强社区在参与旅游过程中与其他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力量。在宗族村落中,由传统精英组成的老人协会,作为宗族权威组织,往往具有与由政治精英组成的村两委抗衡的力量,在与政府和旅游企业博弈时,更能代表村庄的利益,通过发动和组织村民,更大限度地获取旅游开发的利益。
2.3 制度性增权的主体和受体
制度性增权的主体和受体都不是单一的。在我国,从国家权力机关到各级人民政府都有制定规章制度的权力,但是不同主体供给的制度的法律效力大小和约束的人群范围不同。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同盟或协作,领导或跟随,对抗或中立等不同的关系定位(黄少安,1999)。
作为制度性增权受体的目的地社区,其内部由于原有的权力关系,经济实力大小,文化水平的高低以及对旅游开发的态度等的不同而形成多个利益共同体(翁时秀,彭华,2011)。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制度需求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很大的矛盾和差异,因此在分析制度性增权时,有必要分清增权的具体针对部门或者群体。
增权主体和受体的多样,使得我们难以简单直接地衡量一项制度性增权的效果。
3 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必要性
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是通过制定规则改变社区在旅游开发中初始资源的占用情况,由此带来社区在与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中权力大小的变化,最终改变旅游收益分配情况的政治过程。而目前我国决定社区初始资源占有的相关制度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制度的缺失导致的“无法可依”;一种是虽然有相关法律条文,但执行手段不配套,或者由于增权主体之间利益构成的复杂,导致执行过程中的“有法不依”或者“执法不严”。前者对应的是制度短缺引发的制度性增权需要,后者对应的是制度失灵引发的制度性增权需要。
3.1 制度短缺引发的制度性增权需要
缺乏对土地、森林、水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我国社区在参与旅游开发中难以获得直接的利益分配的最大障碍。我国现有的法律条文,对土地、矿产、森林、水等自然资源的产权归属做出了明确规定,自然资源的全民所有和部分集体所有的产权属性不容动摇①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
但是,在将自然资源开发为旅游产品的过程中,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已经发生了改变,原来的产权安排并不包含这部分增加的使用价值(产权制度往往是针对某一资源某一阶段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所作出的权力安排,无法穷尽这一资源由于技术革新等原因导致的价值的所有变化),因此基于原来的产权安排基础上所进行的交易并不适用于新的价值体系,也就导致了交易的不平等。
以河流等水资源为例,河流过去所承载的功能主要包括提供饮用水和运输,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河流的运输功能逐渐弱化,让位于其他的经济功能。旅游的发展,使得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河流河岸资源被开发为旅游观光景点,如漓江、三峡等。出于保护河流景观的需要,渔民被迫上岸,改过去传统的捕捞方式为种养方式,两岸种植的经济林被强制改造成景观林、水源林等非经济林。社区所获得的补偿,依据的是河流和土地等作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的标准,远低于资源的旅游功能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河流的使用和管理权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通过自主开发或者拍卖租赁等方式转让使用权获得收益,社区则只有使用河流作为交通通道的权利,没有使用河流作为景观资源参与旅游开发的权利。事实上,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已经成为河流景观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对于这部分居民创造的旅游附加产值,社区居民却无权从中分享利益。
目前我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对附着在土地、河流、森林等自然资源基础上的旅游吸引价值的使用权利作出规定,社区作为这一价值的重要创造者之一,没有获得相应的法律主体地位,因此也就无法获得与这一价值相当的补偿。
3.2 制度失灵引发的制度性增权需要
制度失灵是指某项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因为制度本身的模糊或者执行人的故意曲解,造成制度实践的失效。在我国,制度性增权的主体并非单一的,而是往往存在多个增权主体。因此在某项正式规则被制定出来后,由于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利分配和利益分配的差别,导致了增权主体对正式规定的执行不力。
我国2006年12月开始执行的《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申请设立风景名胜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在报请审批前,与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充分协商”,“因设立风景名胜区对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风景名胜区的门票收入和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应当专门用于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以及风景名胜区内财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损失的补偿。”①《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十一条、三十八条.http://www.gov.cn/zwgk/2006-09/29/content_402732.htm
《条例》虽然明确指出了应对因为景区开发而受到利益损失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进行补偿,并且对补偿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做了规定。但是没有制定具体的补偿标准,同时也缺乏对补偿是否落实的监督体制。而目前,执行这项《条例》的主体,本身是景区开发的获利集团,补偿金额和比例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执行主体的利益,这直接导致了该《条例》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对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补偿不到位,或者低于其所出让的资源的实际价值。
如在漓江风景名胜区,桂林市政府通过游船经营权的拍卖收取漓江资源使用费,2001年新增11艘游船的经营权共拍得2023万元②桂 林面向全国拍卖游船经营权[Z/OL].http:∥www.gmw.cn/01gmrb/2001-02/09/GB/02%5E18687%5E0%5EGMA4-012.htm。漓江旅游船票210元/张,其中100元为漓江景区门票纳入桂林市政府财政收入,以每年150万到200万游客量计,门票收入一项即可达到2亿元/年(廖广斌,2009)。按照《条例》要求,游船经营权的拍卖所得和景区门票收入应该专门用于资源保护和管理以及对景区内因开发而导致利益受损的人的补偿。而目前漓江两岸农民每年从保护生态阔叶林得到的补偿只有4.75元/亩,这是国家依法给的生态公益林补贴,地方财政并没有从漓江风景名胜区门票或者出让游船经营权所得的资源使用费中抽出专项资金,提供配套补贴。沿岸公益林、凤尾竹林、基干林、观赏林等其他林业资源也并未纳入生态补偿的范围。政府也并没有考虑沿江居民在这些土地上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所得,并将这些损失换算成补偿款③据2010年7月笔者对漓江沿岸村民访谈资料整理。。
桂林市政府作为一级增权主体,本身又是获利集团,在缺乏监督等相关执行手段的配合下,《条例》这项正式制度所规定的补偿条款很难获得真正有效地执行,陷于失灵状态。
制度缺少了可操作的具体规定,便缺少了有效的行动指南,是不完整的,无法实施的,往往陷于失灵状态。因此要以类似的制度为依据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增权,必须明确地方政府的具体行动安排及监督体制。
4 制度性增权的实现途径
不同的制度性增权类型其增权的主体、受体和增权的具体内容都是有所区别的。正式制度增权的主体是以中央为核心的各级政府,受体是目的地社区;其增权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非正式制度增权的主体则是社区精英,受体是目的地社区内部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其增权的途径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增权”。正式制度的增权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上要优于非正式制度的增权,然而由于多个增权主体的存在,使得正式制度的增权往往出现“有法不依”的局面,非正式制度的增权直接产自社区内部,更容易获得社区成员的认可,但是社区精英的个人利益目标和个人能力往往限制了非正式制度增权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4.1 非正式制度的增权途径
非正式制度的增权在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可行的,非正式制度的增权主要体现在能将处于自发参与状态的社区居民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体认同组织起来,并且在组织内部建立基于共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牢固的利益同盟,形成集体的合力与旅游开发的其他利益相关主体进行利益的博弈。这种集体力量增大了交易成本,使得政府和旅游企业在制定旅游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维持交易所需要的履约成本,且旅游开发所需要的专项投资越大,履约成本越高,非正式制度增权的效果就越好。以修建游船码头为例,如果社区组织不让游船停靠或者游客上岸,政府和企业必须考虑使用潜在暴力手段的成本,包括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
但是当旅游开发产生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时,处于权力关系强势地位的地方政府和外来投资的介入,可能导致原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下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的失效。以雨崩为例,基于族群认同和共同的宗教信仰,雨崩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减少了村民在参与旅游开发初期进行合作的协调成本,从而可能在只有较少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共同受益。但是当游客大量涌入,地方政府意识到像雨崩这样的旅游地的巨大市场潜力后,有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参与到对其的开发中去。如迪庆藏族自治州拟建的“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正好置雨崩村于该公园规划和开发的核心位置。按照相关部门“交通优先”的推进战略和“政府主导、企业社区参与战略”的开发理念,未来藏民通过提供马匹和向导等较初级交通条件的参与方式有可能被“交通优先”战略和投资带来的新的交通方式所改变,其在旅游开发中的自主地位和收入分配机制也会随之被迫作出调整。
在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中,非正式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通过这种制度供给方式发生的增权在面对政府的公权力时往往失效,最终只能通过正式制度的确认才能保障社区通过非正式制度增权获得的成果。
4.2 正式制度的增权
正式制度供给的途径目前在我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一种是“中间扩散型”(杨瑞龙,1998)。“自上而下”的增权途径,是由核心权力部门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矛盾进行制度安排,实现社会稳定发展。这种制度安排的途径,增权主体是中央权力机关,保证了制度的合法性和强制性。但因为增权受体如“全民”在法律上的确定性和事实上的模糊性,使得地方政府等其他增权主体在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对“受体”的所指进行按需定义,导致了增权效果的地方差异和不均衡(左冰,2009)。
“中间扩散型”的制度增权途径,其增权主体是地方政府。在充分尊重地方差异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由地方政府将属地内的制度需求以及由此引发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上报上级政府,由上级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将非正式制度变为正式制度。这种增权途径,多发生在旅游开发的成熟阶段,地方政府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的职能转变,不再以旅游资源的所有者、使用者、管理者和受益者自居,将旅游资源的使用和收益权交还给社区,只着重行使管理权。在观察属地内旅游资源分配的需求的前提下,将已形成的符合当地发展的权利分配和资源分配制度上报中央,获得正式制度的认可。以土地为例,各地的土地类型不一,旅游开发中所形成的对土地使用的方法和利益分配的需要也不一致,一刀切的土地分配模式不适应各地旅游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各地特色,形成地方制度,再上报中央,获得认可。
“中间扩散”型的增权途径充分考虑了地方差异,其增权主体是地方政府,可以部分克服“自上而下”的增权过程中其他增权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对制度内容故意地曲解和执行不力。但是这种增权途径难以避免过于注重地方利益而导致对全国利益的侵犯。
5 研究结论
本文是基于旅游实践的对社区参与有效性的一种理论探索。“制度性增权”是改变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缺权状态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使得这项理论的实践面临多重困难,必须从理论的深层结构出发,寻找实践的突破点。
(1)制度性增权中的“制度”概念包含了三层含义:制度产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某个集体的某项共同利益;制度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制度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某个特定人群产生约束力的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实现必须有与之配套的行动安排。
(2)根据制度的含义和增权的内容可以将制度性增权划分为4种类型: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正式制度的间接增权,非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和非正式制度的间接增权。
(3)我国目前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制度供给主要面临两种困境:制度缺失和制度失灵。前者对应的是规则的缺失,后者对应的是与规则配套的行动安排的缺失。因此制度性增权应该分别从这两方面进行。
(4)“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增权途径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条件下因为缺乏地方增权主体的配合而往往在实践中无法真正实现。“中间扩散型”的制度性增权途径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地方利益的协调者,能够直接观察到属地内的制度需求,在充分衡量其作为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和作为代理人的政治责任后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获得上级政府和核心权力的认可。非正式制度的增权,其增权主体是社区精英,受体则是社区内部的各个利益共同体,其增权的途径本质上是“自我增权”。非正式制度的增权在面对政府公权力时,丧失了合法性,社区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供给型增权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则改变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初始资源占用情况,使得社区获得排他性产权主体地位,由此带来社区在与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中权力大小的变化,社区的需求可以直接通过谈判和交易在市场上实现,最终改变旅游开发收益的分配体制。这种增权方式目前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其真正实现取决于各级执政者能否转变观念和政府职能,将社区民生的改善作为旅游发展的目标。制度性增权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有赖于研究者对更多实践案例的发现和总结。
[1] Clark D,Southern R,Beer J.Rural governance,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A case study of the Isle of Wight[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7,23(2):254-266.
[2] North D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 North D C.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3):359-368.
[4] Popper K 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M].2d ed.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7.
[5] Scheyvens R.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J].Tourism Management,1999,20(2):245-249.
[6] Scheyvens R.Tourism for Development:Empowering Communities[M].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2.
[7] 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8.
[8] 保继刚,孙九霞.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研究——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J].规划师,2003(7):32-38.
[9] 保继刚,孙九霞.雨崩村社区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J].旅游论坛,2008(4):58-65.
[10] 陈志永,杨桂华.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热带地理,2011(2):216-222.
[11] 郭文.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J].旅游学刊,2010(3):76-83.
[12] 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兼评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假说”和“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9(1):68-74,81.
[13] 廖广斌.以科学发展观促进漓江水上旅游[J].中国水运,2009(7):18.
[14] 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0(1):47-52.
[15] 王宁.消费者增权还是消费者去权——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重新审视[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100-106,124-125.
[16] 翁时秀,彭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增权研究——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J].旅游学刊,2011(7):53-59.
[17] 杨瑞龙.论制度供给[J].经济研究,1993(8):45-52.
[18]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经济研究,1998(1):5-12.
[19] 杨晓红.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立法探讨[J].旅游学刊,2011(3):9-10.
[20] 周玮.制度供给差异对中国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作用机制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5):2988-2990.
[21] 左冰.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云南迪庆案例[J].旅游科学,2009(2):1-8.
[22] 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5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