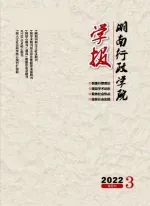中国哲学的进路:从“史”到“学”的建构——张立文先生治学路径探析
张永路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在张立文先生的致思之路上,不仅有着对中国哲学史及其研究方法的系统论述,还有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哲学理论的建构。细而言之,从最早关于周易、朱熹思想的研究,到新近对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系统阐述;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归纳演绎,到传统学、新人学的步步推进,最终到和合学的融通开创。可以说,张立文先生的研究历程,正是从“史”到“学”的演进,是对中国哲学进路的最佳诠释。
一、《周易》及儒学研究
(一)《周易》研究
上世纪六十年代,张立文先生在工作之初,便将治学方向定在宋明理学。而《周易》之于宋明理学,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张立文先生便以最为艰涩的《周易》作为研究突破口。首先,张立文先生运用传统治经方法,如文字、音韵、训诂等研究工具疏释《周易》文本,力求排除后人附着其上的种种成见和误解,尽量贴近《周易》本真面目。在此基础之上,张立文先生继续追寻《周易》书中的诸多疑问,将阅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解和看法整理出来,到1963年初完成了《周易思想研究》初稿。这部著作新意迭见,而这主要得益于其摆脱传统窠臼的努力。在写作之初,张立文先生便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力求贴近《周易》的历史本来面目,尽量再现《周易》文本原意,清除后世学者以己意解经的傅会和曲解。第二、明确区分《周易》的《经》与《传》,二者是不同历史时期及思想体系的著作,必须置入各自的历史环境中。第三、通过《易经》卦爻辞与甲骨卜辞的比较,弄清《易经》卦爻辞的时代、作者、性质和意义。第四、通过对《易经》思想体系的研究,明确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起始,以及这种起始是怎样同宗教巫术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上述指导思想无疑具有超越其时代的前瞻性。
两部书稿完成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研究工作不得不停滞下来。所幸十年动荡,书稿仍存,其间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更为张立文先生的研究带来了宝贵的新材料。1980年《周易思想研究》出版之后,1984年帛书《周易》释文公布,张立文先生便又着手完善《周易》的注释工作,于1985年撰成《周易帛书注译》。这部著作体例完善,其以校勘辨误为先,再加注释疏明文意,再以今文翻译,最后总释通解卦义。特别是由于新材料的运用,使得本书在校勘及注释方面屡有创获,成为扎实严谨而又创见迭出的一部著作,而且更是这一方面的首部著作。
(二)宋明理学及儒学研究
朱熹是宋明理学研究中绝对躲避不开的关键人物,理清这一点便可以带动整个宋明理学的研究。为此,1963年,《周易》相关研究告一段落之后,张立文先生就开始一心钻到朱熹思想研究之中。张立文先生继续运用“笨方法”,从《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一字字读起,并分概念、范畴做读书卡片。即使其后的十几年中运动不断,他仍然不为世事所撼,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和机会啃读原典。艰辛的付出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79年“文革”刚刚结束,50余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便已写定。这部凝含了张立文先生十几年心血与功力的著作,是1949年后国内首部详致论述朱熹的专著,因此一面世便引来国内外学者的赞誉。在当时僵化的苏联研究范式尚未完全消除之前,《朱熹思想研究》这样一部著作无疑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扭转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书中,张立文先生抛弃了过去数十年来流行的唯物、唯心的分析框架,以及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论、历史观等“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而是切实还原至哲学家思想本身,运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方法,深入揭示朱熹哲学思想中的哲学逻辑结构,依照朱熹思想中固有的范畴逻辑结构,解剖其整个思想体系。由此,《朱熹思想研究》不仅深入分析阐述了朱熹的哲学思想体系,其所树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还为今后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1982年,在朱熹思想研究的基础之上,张立文先生完成了《宋明理学研究》一书。此书进一步强化了先前所运用的逻辑结构方法,详致疏释了理学各大家的哲学思想,同时对理学给予了重新定位——基于对汉唐以来僵化章句注疏之学的反动,宋明理学家开始了“疑经改经”的思潮,从而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和各派学说的兴盛。另外,《宋明理学研究》一书还对理学各流派做了划分,认为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苏辙的蜀学属于理学中的非主流派,而非反理学派别,由此将理学分为主流派和反主流派,重新对理学流派做了定位。
在逐渐确立了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之后,张立文先生开始逐步对宋明主要理学家展开研究,先后撰写了《朱熹评传》、《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船山哲学》、《戴震》、《宋明学术略论》等专著,以及众多的论文,并结集为《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儒学与人生》、《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国学新诠释》等书。
(三)朝鲜李退溪思想研究
理学形成并在中国占据主流地位之后,借助着文化的传播逐渐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这些国家中一定时期内的主导意识形态。因此,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必须观照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否则便无法形成完整的理学研究领域。有鉴于此,张立文先生在研究宋明理学的同时,对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家李滉(号退溪)也进行了深入研究。1983年之后的几年间,分别撰写了数篇长文,作为中国研究李退溪思想的先行者,张立文先生的研究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和赞扬。随后,张立文先生完成了专著《李退溪思想研究》的写作。他充分肯定了李退溪的思想贡献,认为退溪将朱子学与朝鲜传统思想融合起来,创造、发展了朝鲜性理学,适应了当时朝鲜的社会需要,从而使朱子学在朝鲜李朝成为了主流思想。张立文先生还细致梳理了退溪的哲学逻辑结构,认为其最高范畴是“理”,或称之“太极”、“道”,其核心范畴是“理”与“气”。“理”既是最一般的规定,又是最具体的展现,其是整个逻辑结构的起点。由“理”、“太极”、“道”的动静流行,便从“天道”(圆)到“地道”(方),包括“人道”。同时,在书中,张立文先生还将退溪思想与朱熹思想以及李朝的李栗谷思想做了比较。通过前者的比较,理清了朝鲜从哪些方面吸收了朱子学,又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创新;通过后者的比较,分梳了朝鲜同一时期不同思想家对朱子学所做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张立文先生另有《退溪哲学入门》一书在韩国出版,其他退溪思想研究论文结集为《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一书。
除此之外,张立文先生还对韩国儒学做了整体研究,撰写了《韩国儒学研究》一书。其中既有对韩国儒学宏观的精妙论述,又有微观的深入研究;既分阶段论述了韩国儒教实践经验伦理、理性经验伦理和性理逻辑思辨伦理等特点,又对韩国性理学家的生平、著作、思想作了细致、深入、全面的分析,包括退溪的性理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南冥思想的逻辑结构,奇大升与退溪的四端七情之辩,栗谷的理气观与礼学说,郭再祐的《春秋》大义精神等。通过对韩国儒学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张立文先生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理学研究,并进而在整个东亚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及新人学研究
(一)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从最初的研究工作开始,张立文先生便提出了范畴及逻辑结构的问题。1964年,在探讨谭嗣同哲学思想时,张立文先生便通过梳理范畴及逻辑结构的方式,指出了谭嗣同哲学思想中“仁——通——平等”的体系特点。之后,在《朱熹思想研究》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并得到了具体的运用,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随着张立文先生的这一方法论逐渐成熟,最终于1984年写成《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此书的写作是对中国哲学史照搬西方研究范式的一大否定,那种研究方法完全脱离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语境,削足适履、圆凿方枘,已经严重不适用于中国哲学研究。而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如实贴近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本真面目,承继源远流长的以《北溪字义》、《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范畴研究,同时又根据现代对哲学范畴的诠释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改造,最终建构了中国哲学范畴结构系统。具体而言,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根据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实际性质、特点、内涵,度越西方哲学方法,独创性地提出了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以及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哲学范畴分类法。在西方哲学中,范畴一般被分为实体、属性、关系三类,或者是辨证的唯物论、唯物的辨证法、辨证的认识论等。这种分类法显然无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契合。因此,张立文先生按照中国理论思维发展的进程,即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抽象——具体的发展,将中国固有的哲学范畴分为象性范畴、实性范畴、虚性范畴三大类。随后他以这三类范畴为基础,以中国传统范畴演变为对象,运用纵横互补律、整体贯通律、浑沌对应律为方法,详尽考察了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
自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出版之后,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多学者都将其作为必要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二)传统学
建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后,张立文先生逐渐契入传统文化本身,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而在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也正成为讨论的焦点,中国传统文化有无价值、传统与现代关系如何等等问题都被抛入论争之中。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张立文先生将传统学从文化学中分离出来,把传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构,从而完成对传统的体认、继承、度越和创造,使传统重新焕发生命智慧,以适应现代化的合理性需要,化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终完成传统的现代化转生。为此,1986年,张立文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论传统和传统学》一文,首次提出“传统学”概念,标志着传统学的建立。到1989年,《传统学引论》一书出版,传统学体系最终建构起来。之后,张立文先生的相关论文又结集为《传统与现代》一书。
在书中,张立文先生首先区分了传统和文化。他将传统定义为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着、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而传统学则是关于研究传统发生、成长、发展的规则、原理与其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学问,是传统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内在性与外在性、殊相性与共相性的融突和合的学说。与文化学相比,传统学的特征非常明显,首先其是研究客体化的对象物是如何及怎样体现主体精神、风格、神韵、心理素质的;其次是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如何凝聚、固化成传统,构成传统的有机系统的;最后是研究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异和契合,以及如何重新筛选、凝聚、固化,如何世代延续的。而从传统系统、传统模式、传统认知功能和传统无意识等角度来探讨传统学的对象和范围,其主要包含四个要素:传统的价值观念系统、传统的精神心气系统、传统的知识系统以及传统的语言符号系统。其中,传统价值观念系统是核心,其指向制约着传统的精神心气,知识系统则是传统的产物,而且是传统延续和再创造的工具,语言符号系统还是价值系统和心气系统的外在表现,四者之间相依相存、不离不杂,共同构成了传统学的基本内涵。
传统学研究,张立文先生无疑是第一人。在《传统学引论》中,张立文先生对传统和传统学的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奠定了传统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三)新人学
传统和文化终归是由人创造的,人创造了传统和文化,而传统和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人,因此,传统学的实质其实就是人学。而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现代化的中国人,新的时代急需重新规范人自身,重新发现人自身。由此,张立文先生开始从传统学研究进入到人学的探索之中,并最终完成了《新人学导论》。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但在21世纪的全球化、网络化进程中,这个论断显然已经过时。因此,张立文先生重新对人做了定义,即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之后,为了进一步化解新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五大冲突及生态、人文、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张立文先生又将定义修正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这是对人在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中所应有的作用、地位和价值的重新思考,也是继从自然发现人和从宗教神学发现人之后的第三次人的自我发现。在书中,张立文先生还探讨了人的自我塑造、自我规范、自我创造、自我关怀、以及自我和合等问题。自我塑造探索了人的创造力的来源,批判了达尔文和梁漱溟关于人身、人心观点的缺陷,他随后又探讨了面临各种冲突和危机时,人如何自我规范的问题,其后又论及人的观念、思维、道德的自我创造,以及人对自身一些终极问题的自我关怀。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达成自我和合论所塑造的和合型的人与优美型的人,最终实现真善美融合的和合优美境界,也就是自由境界。在此基础之上,张立文先生根据现代社会的状况和需要,建构出人生五大境界:生命超越境、知行合一境、情景互渗境、圣王一体境以及道体自由境,以此作为现代社会新人的价值导向,从而完成对人的重构。
张立文先生对新人学的建构,有着深厚的现实关怀,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现代化转生的深切关怀,也是对人的现代化的深挚关切。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现代人,现代人的中国也需要现代化,通过对新人学的建构,张立文先生解决了这项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同时也完善了自身的哲学体系,使其奠基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充满了人本情怀。
三、和合学研究
在数十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张立文先生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其创新意识和意义就在于度越“照着讲”与“接着讲”。而得益于他对“自己讲”、“讲自己”的体悟和关注,与此相关的论文结集为《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一书。中国哲学必须“自己讲”、“讲自己”,否则便无法创新、无法发展。张立文先生认为,要做到“自己讲”、“讲自己”,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从纵向而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种哲学理论思维形态都是某个时代环境的产物,是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的精神硕果。因此,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创新也必是与时代的发展相联系的,这其中便蕴涵着哲学变迁的秘密。张立文先生在几十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为我们逐渐揭开了这个秘密,总结出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的三大游戏规则,即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核心话题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是中国哲学创新的话语标志;人文语境是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历史变迁的集中体现;诠释文本是学术思想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这三者是依时变迁的,不存在千年不变的哲学问题,也没有万古常住的哲学范畴,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文本。同样,中国哲学的创新也只有依据这三大游戏规则才能实现,否则只能是亦步亦趋、人云亦云。
第二、从横向而言,中国哲学绝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不能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而应该是智能创新式地“自己讲”。以往的研究方式基本上是以中国哲学注解西方哲学,而“自己讲”、“讲自己”则是以西方哲学注解中国哲学,其主体是中国哲学自身。这首先就需要中国哲学自我定义、自立标准,而不再以西方哲学定义为圭臬,必须扎根中国哲学沃土,梳理出自己的哲学定义,张立文先生把中国哲学定义为“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其次,“讲”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采用六经注我、以中解中的方式,而不能以西解中。最后,“讲”的对象也必须是中国哲学话题本身,必须直面中国哲学生命本真,讲述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
“自己讲”、“讲自己”以及三大游戏规则是张立文先生数十年中国哲学研究所得,是深刻反思中国哲学自身问题的开悟,正是在此基础上,张立文先生完成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在新时代的转生。
新的时代之下,人文语境、核心话题以及诠释文本都面临着转换,这就要求新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必须提出自己的创新之道。由此,张立文先生在和平与发展的人文语境之下,提出了“和合”的时代话题,并选取《国语》作为诠释文本,建构起了“自己讲”、“讲自己”的和合学理论体系。
在《新人学导论》中,张立文先生便提出了“和合型”人格的问题,同时伴随着他一直以来对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忧虑和思考,最终于1989年明确提出了和合学。中国文化不仅面临着人类共同的冲突与危机,而且还有着自己独特的问题,前者是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以及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和由此而造成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和价值等五大危机,后者则是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如何现代转生的困境。基于对上述种种问题的思考,张立文先生历经殚精竭虑地反思,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发表多篇和合学文章,并于1996出版了《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最终建构起和合学理论体系。和合学的建构便是立足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度越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意识形态的网罗,从而化解上述种种冲突、危机、挑战,完成传统的现代化转生。随后他又陆续写成《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和合哲学论》、《中国和合文化导论》等专著,就不同方面深入阐发和合学理论。
和合学是时代精神的召唤,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中国文化的生命智慧,是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现代转生,也是回应人类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最佳文化选择。和合学的核心范畴是“和合”,这一范畴源自《国语》,即“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因此,作为和合学的核心范畴,和合是扎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中,有着坚实的文献基础的。当然,和合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和合学之和合却是张立文先生体贴出来的。依照张立文先生的定义,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建立在和合文化基础上的和合学,便是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并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是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和合学体系恢弘博大,其中包括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等和合三个世界,也包括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等五大原理。前者组成了完整的和合学模型,是和合学的智慧之光和理论支撑;后者则从文化战略层面有效地化解了人类的五大冲突及其危机。
和合学提出之后,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国内,《和合学概论》出版后,学界随之掀起了和合研究的热潮。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合研究更是持续为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着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同时,自1991年始,张立文先生多次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葡萄牙等国,或讲授和合学课程,或做主题演讲,引起了学界甚至政界的极大兴趣。和合学所凝含的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深切关怀和终极思索,无疑是引起人们广泛共鸣的根本原因。在新时代的世界形势下,和合学对时代问题作出了最佳回应,为人类所面临的冲突与危机提供了最优化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