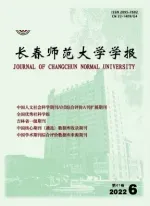从“恋父”到“弑父”的历程
——由陈染作品对父亲的建构看陈染的写作姿态
张罡风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藏拉萨 850000)
从“恋父”到“弑父”的历程
——由陈染作品对父亲的建构看陈染的写作姿态
张罡风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藏拉萨 850000)
陈染的作品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建构完成了对自我心路历程的找寻,同时也透露出她对他者(人类)和现实世界反抗中的复杂情绪。本文从陈染与其“父”的关系出发,通过对陈染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来体察作者的心路历程和写作姿态。
陈染;人物形象;父亲;写作姿态
陈染的大部分作品里,有关“父亲”和“父亲样”的描绘占据了她的“男性世界”中的大部分。她清晰地向读者描绘了一个最初的深刻的创伤性情景:童年少女时代的家庭破裂,父亲角色的缺席,父爱的匮乏,使她未能顺利地完成一个女性的成长;一个因父母离异而倍感童年的寂寞和凄清,变得早熟而敏感的女孩。这个女孩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同时我们很容易从中找到一个典型的心理情结:恋父(女性俄狄浦斯情结)。一个因创伤、匮乏而产生的某种心理固置:永远迷恋着种种父亲形象,以其为补偿,不断地在对年长者(父亲形象)、对他人之夫(父亲位置的重现)与男性权威者的迷恋中,在寻找心理补偿的同时,下意识地强制重现被弃的创伤情境。所以,强烈的恋父情结是陈染作品世界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幼年时遭到父亲伤害的感情与被成年男性侵犯的场景重合而为一种心理固置,使头脑中的男性形象在无意识中被反复描摹。
父亲,作为无法逾越的绝对存在,一种先天性的占有和永久的恐吓,一片因童年创伤而抹不去的阴影,使父亲这样一个男性形象总是浮于陈染的意识之中。按照弗洛伊德的“埃勒克特拉情结”(女性俄底浦斯情结)理论:对父亲的依恋和“绝裂”,是女性心理成长的途径之一。陈染正是通过个体化的叙事,将女性对父的依恋和“绝裂”文本化了。
在小说《私人生活》中所展现的故事透视了一个痛苦的女孩成长的家庭背景:一个强大高压的父亲和身陷恐惧中的小女孩构成了一个丢失父爱的埃勒克特拉情结。畸形的恋父情结使得小女孩从外部男性世界中寻找感情和欲望的补偿,所以在小说中就产生了一系列陈染小说中的“男邻居”这一人物形象。“男邻居”通常会与女孩以游戏的形式享受两性之间的吸引和一切与“性”有关的禁忌。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父亲一个粗暴的耳光伤透了女孩的心,可是被打伤的女孩又去找一个父亲式的邻居男人来自慰,向这个父亲一样老的邻居奉献自己,她自虐,想自我毁灭,将父亲对她的毁灭转化为自我毁灭。在《与往事干杯》中,肖蒙与一个年轻人老巴相爱,可是她的恋父情结使她先爱上了年轻人的父亲(邻居男人),这样便无法再爱这个年轻人。“父亲”的存在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这便是陈染“恋父情结”投射在小说中的潜在结构。少女对于父爱和异性之爱抱的天真幻想的过早破灭使“她”更早地期待父亲的替代的出现,对成熟男人,特别是和与父亲同辈男人的性的关注成了“她”无法回避的精神创伤:在《私人生活》中T老师的出现恰巧构成了与她家庭生活中的父女关系的替代,这一充满性象征意味的课堂关系多少弥补了作者内心的缺失:作者让一位纯真少女羞怯地勾画出一个中年父亲式的男人难以言状的性幻想并且在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指引下,一个少女在潜意识里与缺失的父亲完成了带有性意味的互动。同时,在《与往事干杯》中,肖蒙对“父”或者男性的依恋是颇具意味的,具有“诱奸故事程式”,但主角已不再是男性,男性在小说中被安排为被动者。早在陈染80年代中期的第一篇小说《世纪病》中就写了一个年轻人对父亲失望,以至无处寻得生命的意义,去自杀。之后的一系列作品,如上文提到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等,都有这个原型情结,但是都未解决对父亲的失望和绝望这个问题。
“弑父”的最初表现为由依恋走向逃离。
在《与往事干杯》中,肖蒙不顾老巴的苦苦挽留,别无选择地离开了老巴。在《无处告别》中,黛二小姐毅然决然逃离了那位高大英俊,能为她提供现代文明生活的约翰·琼斯,原因是约翰不能唤醒“她内心的东西”。在《女人没有岸》中,女作家麦一不愿意当物理学博士泰力的附属物,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逃离家庭,成就自我的道路。
在逃离之后,作者试图冲出父亲(男性)所制造的氛围和樊篱,更坚定了“弑父”的勇气和决心,其表现形式为对男性报复、控诉和安排人物死亡线索。
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从小就感受到父母双亲之间的冷淡情感和对于自私父亲的厌恶,以至于仿佛不由自主地拿起剪刀,把父亲的裤子剪坏,对他进行报复。在《嘴唇里的阳光》中描写了黛二幼年时的一个邻居,一个有裸露癖的建筑师,“弑父”的愿望在这里表现为对性变态者之“父”的放逐:“一把大火伴随着令人窒息的汽油味结束了他的苦恼、悔恨和无能为力的欲望……”。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将一个充满快感的“光芒四射的耳光”还给了那位想象中的“替代性的父亲”。在《纸片儿》中,更流露了要是不弑父就会被父所弑的矛盾心情:残酷的外祖父为了阻止外孙女与单腿人乌克的恋情,带领其豢养的十几只猫咬断了乌克身上所有的血管,也咬断了纸片儿一生的幸福,作为报复,作者安排了纸片儿的外祖父被猫咬的同样命运。在《无处告别》中,作者对“父”之权力予以了控诉,那个气功师正是利用他能够控制人的能量和权力使黛二跌入了虚妄的深渊,这使得黛二再一次经历了创伤,同时也是作者对“父”性权力的一次深刻否定。
在陈染的一些作品中,有一条“父亲”死亡的线索始终贯穿其中:在《私人生活》中,父亲卑琐地死去;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我”的父亲成为疯子,死于“性缢死”;在《与往事干杯》中,作者最后安排了老巴的死亡,在无意中消解了男性形象的力量,使他们从自己身边和头脑中消失。
这样的一些“弑父”情景,潜藏着对父亲——男性权力的否定和挑战,也是在男性权力意义上引发的女性对性别、对自身身份的思考。在这里,陈染已经将父亲经验的体验上升到对社会经验的表达,在一篇访谈中她说:“‘父亲’是对生活中所有的权力——中国的权力主要是父权——的一个表示,而不是指生活中自己的父亲。……他们没有看到象征和社会化的关系,这是很微妙的关系,是通过父女关系涉及社会权力问题。”[2]
“弑父”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弱化、贬低男性形象,从上面分析过的人物以及她涉及过的一系列男性形象:大树枝(《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泰力(《女人没有岸》)、莫根(《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墨非(《无处告别》)、“父亲”、丈夫(《时光与牢笼》)、医生(《嘴唇里的阳光》)、气功师(《无处告别》)等等,不同的命名其内在编码却有着无可改写的同一性。他们或者仅仅是一个性动物,或者是一个朝朝暮暮的花花公子,要么吃东西时发出很大的声响,要么是一个无比自私的庸俗之徒。在陈染的作品中,这个世界的男人被描述成没有任何指望的,在她的笔下,“父亲”已经不再是温情而有权威的了,《时光与牢笼》中的丈夫已全然不再有“父”的特性。
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一个名叫“大树枝”的男人,被描写成一个被黛二使用的性工具,没法与之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下床之后,便被黛二抛弃,黛二由此声称:“没有一个男人有能力把我拉走。”
以上我们可以体会到陈染心理上对于男性的一种极度失望,这源于男性不能和她们一起建构属于自己的理想。她认为的男性人物在女性面前表现得怯懦、虚伪、卑劣。这样的失望情绪等于在宣告,只有符合女性提出的标准的男人才能成为她们心中的男子汉。这不仅是对当今男性世界的否定,而且也是对父权制社会莫大的嘲讽,是对男性把女性作为他者的一个根本性颠倒。
这些都成为陈染“弑父”的一种叙事策略。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陈染对男性形象的重构方式,陈染用女性的视角提出对于男性的标准,用弱化、降格、毁灭的方式写出了残暴、无能、异化的男性形象,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降低了男性的价值和权威,以此解构了男权社会的力量。
但是,“弑父”对陈染来说,并不意味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超脱,相反,在弑父之后,仍然有挣脱不去的束缚在等待着她。“弑父”但仍生活在父权的阴影之下。“弑父”并不意味着父权的消失,相反,父权以无处不在的巨型话语,在心理和现实中仍然让作者产生威胁感:婚姻失败、工作无望的黛二小姐只能在绝望的想象中逃往黑风衣铺就的最后的逃亡地(《无处告别》)。而《站在无人的风口》中,尼姑庵里的那个老女人,两个男人为她发动了一场“玫瑰战争”,但到最后,只有两件红白长衣相伴她,她只有无比钟爱地抚摸着那光滑高贵的颜色,恣意而贪婪地露出她的欣喜之情,“她一动不动地靠在高台阶上边那个窗子前,她双目低垂,她的忧戚而衰竭的脸颊,苍白枯槁的手臂都已在静静的等待中死去,只有她的梦想还活着”。死亡使女性在一瞬间洞悉了“爱”的真相,爱情不过是男性需要时捧在怀中、发泄时狠摔于地的易碎的花瓶,是男权文化设置的死亡陷阱。“弑父”还使作者永远背负着沉重的杀人罪孽感。尽管窥破了爱情真相,窥破了父亲/男人的自私虚伪、冷酷无情、但却仍“想要一个我爱恋的父亲”,“一个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像无以挣脱的死亡锁链,在“父亲”重重捆绑的同时,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自缚于锁链之中。
由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陈染的创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逃离社会历史、直视自我生存、关注内心体验的姿态。几乎她的每一篇作品都有一个女性叙述人,从童年到青年,都是在与外界相对封闭的自我空间里品尝着孤独、自恋、忧郁的女性,并且充满了焦虑、恐惧与紧张感。这种感觉和状态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产生的:一个威严冷酷的父亲、一个父母离婚的破碎家庭,与寡居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外部环境使得她们(作者在文本中的自我投射)承受着很大的外部压力,在歧视和冷眼中,她们高傲而又自卑的心灵主动选择了逃离,退回到内心世界,在回忆、梦幻和唯恐外界侵害的惧怕中打发着不尽的时日。又由于在成长期中父亲的缺席,使她们难以完整地完成女性的成长,因而就造成了某种心理障碍。作为心理补偿,她们一方面在作品中塑造了父亲般的有依赖感的男性形象,来完成她们先前未完成的恋父愿望。另一方面,她们在寻求和获得补偿之后,无法摆脱的恐吓和专制的阴影又激发了她们的女性自觉意识,使她们开始实施“弑父”,逃离男性氛围的网罗。
[1]陈染.陈染文集·私人生活[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2]陈染.陈染文集·与往事干杯[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The Course from“Electra”to“Patricide”——An Analysis on Chen Ran’s Writing Attitud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Father in Her Works
ZHANG Gang-feng
(Lhasa Teachers College,Lhasa 850007,China)
Chen Ran’s works accomplished the search of herself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constructing a series of characters;meanwhile it revealed her complex mood about human beings and revolted against the present world.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en Ran and her father,in order to experience and observe the author’s self development and writing attitude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 of Chen Ran’s work.
Chen Ran;characters;father;writing attitude
I206.7
A
1008-178X(2012)10-0095-03
2012-05-27
张罡风(1982-),男,吉林乾安人,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