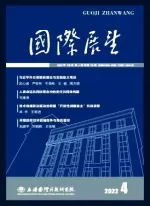试论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统筹两个大局的成就与挑战
金良祥
试论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统筹两个大局的成就与挑战
金良祥
统筹两个大局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联系和协调内外矛盾关系的决策方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统筹两个大局的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中国历代领导集体驾驭内外关系的实践。新世纪前十年,中国党和政府提出的“两个判断”和“两个意识”、“走出去”和“互利共赢”战略、和平发展观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方针均体现了统筹两个大局的思想。中国在外交实践中保持了维护利益与承担责任以及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平衡。统筹两个大局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意识薄弱、机制不够健全以及能力有待提升等。
新世纪前十年 统筹两个大局 责任承担 维权维稳
新世纪前十年(2001—2010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党和政府驾驭国内国际大局的任务更加艰巨。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及时强调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两个大局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综合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通盘考虑内外需求,制定全面平衡战略,建立有效协调机制,贯彻配套应对政策,从而实现中国内政外交的既定目标。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中极其关键的阶段。其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万亿美元上升到6万亿美元,陆续超过一些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相继成功举办了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中国成功实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高层决策者和各级内政和涉外部门长期坚持两个大局的统筹方法。可以预期,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内与国际、内政与外交的联系将更加频繁紧密,矛盾将更加突出,统筹两个大局的要求将更高。
一、统筹两个大局的理论和实践来源
统筹两个大局思想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之中。尽管统筹两个大局概念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但中国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集体实际上都是统筹两个大局方法的有意或无意的实践者。
首先,统筹两个大局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与西方国家在决策的过程中首先考虑个人或个体不同,中国传统思维倾向于优先考虑宏观环境而不是个体,体现的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①秦亚青:“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 5期,第29页。
外部环境指的就是“势”,或者今日最常用的“形势”。所谓“势”,既指静态的总体格局,即局势、形势、气势,又指动态的主流趋向,即情势、态势、趋势等。②潘忠岐:“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7页。基于这种对“势”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顺势而为。孙子强调“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孟子强调“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孙中山强调“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然,顺势并不是消极的守株待兔,而是顺势与借势的结合。所谓把握战略机遇期,便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与这种强调顺势相对应,中国文化也强调积极运筹大势。如“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意思是高超的棋手胜在能够运筹大格局,而不是一子一步之得失。
统筹两个大局强调需要考虑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相互影响以及把握机遇和规避风险等,实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这一特点。
其次,统筹两个大局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矛盾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之一的统筹两个大局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当代运用。
统筹两个大局是协调国内和国际矛盾的方法,其前提则是对矛盾存在的肯定,即唯物辩证法所称之为的矛盾普遍性。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中”。②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7页。③ 毛泽东:《矛盾论》,第330页。同时,统筹两个大局的概念也是基于对内政和外交、国内和国际形势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③
统筹两个大局主张将国内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考虑,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的继承。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反对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主张不仅要从事务的内部,而且“要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④毛泽东:《矛盾论》,第301页。反对片面地看问题,“反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⑤毛泽东:《矛盾论》,第313页。。
第三,统筹两个大局也有着丰富的实践渊源。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历代领导集体实际上都是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行决策的卓越实践者。他们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经验,为统筹两个大局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共同构成了统筹两个大局概念的实践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形成和长期坚持改革开放战略,这固然首先是出于遭遇多重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建立在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基础之上,即“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①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127页;类似讲话可参见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41页;邓小平:《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5页。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内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致力于并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以及中国深入融入世界,创设了必要制度条件。与上述两项重大决定有关的其他重大举措还包括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实施“走出去”战略等。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统筹两个大局的概念,是理论创新,但更是中国当代政治实践经验长期沉淀的结果,是对历代中国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将两个大局联系起来考虑和决策传统的继承,是对中国党和国家长期以来以一种无意识的方法实施的统筹两个大局的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当然,统筹两个大局概念的提出,也是21世纪初期时代紧迫性的体现,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空前频繁、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互动空前紧密这一客观事实和历史趋势在决策理念和方法上的反映。因此,统筹两个大局的概念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标志着统筹两个大局作为方法和机制,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了自觉阶段。
二、新世纪前十年统筹两个大局的理论与战略体现
新世纪前十年,国内国际联系日益紧密、矛盾突出。中国党和政府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利用联系,驾驭矛盾,不仅体现在重大战略判断方面,而且体现在充分利用和协调内外经济联系和矛盾方面以及在涉及重大政治和安全战略方面。
(一)提出了“两个判断”和“两个意识”,为借助有利的国际条件和规避消极国际因素干扰提供了指导思想。所谓“两个判断”,是指党中央关于新世纪初期国际形势新特点的高度概括,即“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①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及“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0年。“两个意识”则指基于“两个判断”所提出的“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
21世纪初期,中国既面临如何借助有利的外部条件实现内部发展,也面临如何通过国内政策调整克服外部不利因素影响的任务。中国高层适时提出了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为党和政府驾驭国际国内形势之间复杂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战略机遇期”和“机遇意识”的提出为中国把握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国际和平条件实现国内发展明确了战略方向。同时,“忧患意识”则为中国在国际权力结构深刻变化、西方经济危机及资源能源环境限制等外部挑战下通过国内调整应对困难提供了警示。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统筹两个大局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把握和平的国际条件发展自己方面,而且表现在应对国际环境中的风险因素方面。在“战略机遇期”概念的导向下,中国各级政府放手发展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万亿美元增长到6万亿美元,实质性地缩小了中国与世界第头号经济大国的距离。2008年以来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则提供了应对不利因素的案例。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及时实施了 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国内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办法抵消了外部环境恶化的消极影响,不仅使得中国经济在经历短暂的下滑之后迅速、率先走出危机,而且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提出并践行“走出去”和“互利共赢”战略,为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以及协调内外利益提供了指导方针。中国顺应国内国际形势发展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是指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走出去”战略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为中国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进行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提供了政策导向。它既是中国总体的改革开放战略不断深化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手段。
如果说“走出去”是一项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相互联系的战略,那么互利共赢则是协调国内国际相互矛盾关系的战略。经济合作和贸易能够促进各国共同受益,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各方获益程度不同,贸易双方是一对相互矛盾的关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不仅必须通过扩大出口缓和国内就业压力,此举直接关系到社会和政治稳定,而且必须与世界各国携手促进国际经济共同繁荣。
在参与全球经济的进程中,中国并不寻求单方面受益,而是兼顾合作方的利益,并积极为全球经济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极大地促进了中外经济关系的可持续性。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年均进口近7500亿美元商品,相当于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2000年至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年度对外直接投资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590亿美元,有力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发展。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
中国的互利共赢战略也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如何处理本国与他国的利益作出了理论贡献,具有世界和历史意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片面压低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此举虽一度确保了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最终不仅损害了广大亚非拉发展中能源资源输出国的利益,而且损害了其自身的利益。亚非拉国家陷入长期贫困之中,经济结构也极其单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又使得发达国家难以进一步扩大市场,全球经济一度陷入恶性循环。
(三)提出一些新的外交理念和观念,充分体现了整体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国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和谐文化特点和现实发展需要的战略体现,也是基于打消“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取信于世界的深层次考虑;中国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既是中国通过稳定周边维护国内发展大局战略思想的反映,也是出于重视周边国家的现实顾虑和现实利益的需要;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实质是相互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中国摒弃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观,主张将本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内外平衡的精神。
三、统筹两个大局背景下外交实践
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以适应参与全球经济和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外部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国内的影响趋于上升,中国也以积极主动的外交化解来自外部的挑战,既维护了国内经济发展大局,也维护了国内政治社会稳定的大局。
(一)中国在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上做到了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相对平衡。在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重大热点问题的应对,既承担了应尽国际责任,又维护了国内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以劝和促谈为指导,积极构建“六方会谈”机制,不仅维护了沿边地区和国家稳定,而且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不扩散体制的威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在诚恳劝服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和谈判机制,既维护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的能源供应条件,也防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维护了地区和平。此外,在缅甸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也保持了履行责任和维护利益之间的平衡。
(二)中国通过塑造全球经济环境推动国内和全球经济良性发展。在新世纪前十年,中国在增加全球经济体系话语权和规制权方面取得质的飞跃。中国通过“8+5”和“二十国集团”渐次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圈,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一定程度沿着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调整。经过中国的努力,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均有所增加,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有所提升,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环境进一步优化。
(三)中国外交工作为国内维稳作出了新贡献。首先,外交为维护国内政治安全作出了新贡献。新世纪头十年,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潮影响,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危害政治安全的事件,包括“零八宪章”、刘晓波和艾未未事件等。上述事件不仅由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偏见,西方媒体的炒作,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对中国的政治安全造成潜在危害。中国并不排斥对话,而是积极利用各种对话机制,既介绍中国的观点,也进行坚决的斗争,部分弱化了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和“民主”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动力,维护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安全。比如,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入“双方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①这是中国长期对美外交斗争的结果。
其次,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外交配合了国内在涉及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政策。2008年发生的西藏“3·14”事件和2009年发生的新疆“7·5”事件,本质上都是中国内部事务。然而,由于境外分离主义势力和西方反华与敌对势力恶意扭曲和攻击,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受到影响。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举措,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新疆“7·5”事件以后,中国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桑奥卢访问中国,极大地消除了伊斯兰世界对中国处理该事件的政策以及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误解。西藏“3·14”事件之后,针对境外发生的干扰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行为,中国时任驻英大使傅莹在英国主流媒体《星期日电讯报》上刊登文章——《如果西方倾听中国》,向国外公众解释了中国普通百姓对举办奥运的渴望、付出的努力以及西藏地区的发展进步。②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荷兰、捷克、立陶宛、拉脱维亚、芬兰等数十个国家,解释中国政府的政策。上述外交互动一定程度地扭转了国际上关于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误解,将中国处理上述事件的消极国际影响降到了最低点,维护了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再次,中国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既维护了国际反恐大局,也维护了国内安定团结的民族宗教关系。“9·11”事件以后,反恐在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中国一度面临非常复杂的处境。一方面,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违背人类的基本道义;另一方面,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斗争具有明显的反伊斯兰色彩。如果中国不与美国保持距离,①“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17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94969.html。②参见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41—42页。不仅将可能损害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而且可能影响国内穆斯林地区的稳定。中国客观判断反恐形势,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并不主张过于夸大恐怖主义威胁。事实证明,中国关于国际反恐的政策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万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中国没有因为其反恐政策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安全问题。
最后,中国外交在涉及领土、领海争议问题上坚决斗争、捍卫主权,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国内稳定的干扰。2010年9月,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发生碰撞事件,此后日方逮捕了中方船长及船员。围绕这一事件的外交斗争为近年来中国外交捍卫主权的实践提供了典型案例。中国高层官员通过多次召见日方外交官等方式施加压力,国务委员戴秉国甚至深夜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迫于中方压力,日方最后不得不释放了中国船员。尽管国内民众对中国外交在涉及领土和领海争议问题上抱持更高的要求,但中国外交坚决捍卫主权的行动极大地消除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对国内稳定的影响。
四、统筹两个大局面临的挑战
内政与外交互动日益紧密,新世纪头十年统筹两个大局任务一直面临严峻挑战,未来会更加艰巨。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并逐渐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既要继续深化国内改革以适应国际形势,又必须根据国内需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既要把握机遇发展自己,又要考虑自身发展政策的国际影响。统筹两个大局是中国平衡调和的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未来更面临如何提升和如何机制化系统化的挑战。
(一)统筹两个大局的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积累使得中国开始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日增,相互影响日强。因此,全面深度融入世界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更使得中国统筹两个大局的任务面临空前挑战。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长期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形成的思维习惯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等,国内关于统筹两个大局的认识、意识和观念仍滞后于形势的发展。一是对国内曾经长期实施但并不符合通行国际规范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国际反应缺乏足够的重视;二是对中国发展和崛起所引起的国际关注、顾虑估计不足;三是对国际形势变化可能造成的国内影响缺乏充分的认识。
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屡屡被西方国家用来攻击中国,固然首先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偏见和敌视,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实施发展政策以及在执法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大量不尊重人权的现象。中国军队进行的反卫星装置的试验以及海军进行的突破日美传统势力范围的演习训练等行为,也曾经使得外交陷入被动局面。①参见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对外政策新取向》,第103页。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面临的国际压力,以及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激增所引起的国际社会强烈反应,均一度使中国外交处于被动局面。
(二)尚未完全形成在内外互动日紧条件下的有效统筹协调机制。20世纪末,中国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了适应对外开放需要的改革。新世纪前十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经过2003和2008年两轮改革,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29个组成部门最终调整为27个。改革后的政府机构设置能够更好地适应统筹两个大局的需要。撤销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并建立商务部,显然是为了更好理顺对外贸易关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则有利于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关系,前者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经过改革,各政府机构在联系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方面的能力大大加强。然而,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各类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仍未满足两个大局之间互动日益频繁的现实需要。由于包括各政府部门在内不同对外行为主体对国际规范的认知水平不同、政治敏锐性强弱不同、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足以及政策协调不充分等原因,近年来中国对外协调不够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国内统筹两个大局意识仍然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中国尤其需要加强部门间协调机制建设,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三)统筹两个大局任务面临从“主动应对”到“主动运筹”的转型挑战。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如前文所述,中国在两个大局统筹方面取得了大量成就,但两个大局统筹的水平仍然处于“被动应对”的阶段,为适应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历史任务,中国还需不断提升“主动运筹”国际事务,并使其朝着更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演变的能力。
新世纪头十年,任凭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始终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主动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然而,无论是分析形势,作出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论断,还是把握机遇发展自己,实则都是处于“被动应对”外部形势的阶段。中国虽在一些重大地区热点问题上获得了发言权,但其参与的进程并非中国主动运筹国际事务的体现,而是被动参与。中国参与伊核问题固然是中国作为大国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体现,但其基本原因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在伊核问题上保持符合其利益的大国一致,从而防止中国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伊朗离间。①Henry Kissenger, “A Nuclear Test for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6, 2006.
尽管如前文所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两个大局统筹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受这种“被动应对”的地位和态势的影响,中国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国际事务变化的受害者,甚至是某些西方国家制造、操纵一些重大国际热点问题的受害者。苏丹、伊朗以及利比亚等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指责、干涉和入侵,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其是否是直接针对中国的阴谋。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相继提出了“和谐世界”和“和平发展道路”等外交理念和理论,既合乎中国国力增长的政治逻辑,也是中国关于和参与塑造世界未来的理想和愿望的集中体现。然而,如何将“和谐世界”的理念具体化和行动化,更加有效地参与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仍将是中国外交面临的艰巨挑战。自近代以来,英美等西方国家都先后提出、实施若干比较成熟的管理和塑造国际事务的模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曾发展和实施了分而治之的理论,美国则有离岸平衡、遏制、制裁、人道主义干预等战略措施。中国是一个秉持“和谐世界”理念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抵制上述损人但未必利己的政策。
作为一个崛起的、利益遍及全球的国家,中国在批评西方国家不道德的政策的同时,还需提出并践行那些既符合自身又符合全人类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的对外行为举措,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反对干涉内政,固然符合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所确立的主权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些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实则服务于一己私利的政策设置了障碍。但不干涉内政,作为一种对西方强权政治的被动反应,只是一项原则表述,而不是能够塑造国际事务的有效举措。中国向苏丹、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以及利比亚等国家提供了数量不菲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积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体现,有利于缓和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但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主导作用而言,中国的援助只具有辅助性作用,并不具有塑造性功能。
经过第一个十年的积累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市场容量极为广阔,外汇储备充足。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只是具有充足经济资源的经济大国,包括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中国未来运筹国际形势的能力建设将首先在于能否更加灵活地运用经济方法。
On China’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 Reconcil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2001-2010)
JIN Liangxiang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D6
A
1006-1568-(2012)04-0025-36
Manag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s a whole, that is, make full use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deal properly with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ar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ethods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he concepts of managing the two situations as a whole take roots in China’s traditional holism, dialectic materialism and the practices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 in handling rela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The new ideas and guidelines proposed by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including “the two judgments and two awareness’s”, “going-out” and“win-win” strategies, and neighbor policies, all reflected the concepts of managing the two situations as a whole. China’s diplomacy has achieved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domestic efforts to maintain stability. China is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including weak awareness of its importance, insufficient mechanisms and poor capabilities regarding overall management of the two situ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