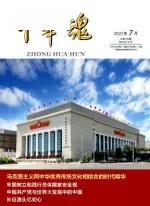敢抛热血护新生:辛亥革命前后的林伯渠
文郭 钦
1918年春,在战火纷飞的湘南,林伯渠风尘仆仆,奔走于衡阳、零陵、广州之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国内,好友李大钊来的几封介绍十月革命的信也收到了。民国建立8年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也接踵而至,而国内依然是军阀混战,革命屡遭挫折,民主共和的出路在哪?林伯渠思索着,沉沉心事凭谁诉,好友李大钊的来信无疑像是在苦旱的沙漠中得到的一股甘泉,心里顿觉一清,行走于郴州至衡阳途中的他写道:
春风作态已媚人,
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曼舞,
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从现象能摸底,
免入歧途须趱行。
待到百花齐放日,
与君携手共芳辰。
是的,新的春天已经来临了,“路引平沙履迹新”,新的希望已经出现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回忆着,思考着……
少年英雄气
林伯渠,原名祖涵,号邃园。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北约10公里的凉水井村一个“九牧世家”的乡村家庭。村前溪流淙淙,屋前有稻田,后有茶山,左晒场,右池塘,晒场中央千年古柏巍然屹立,这是一个具有浓厚书香气息的家庭。童年的林伯渠就生活在这里,他体弱多病,家里人本想让他静养,但又怕像俗语所云,“抠成的疮,睏成的病”,最终还是决定让他经风雨,见世面,在生活的摔打中成长。7岁的时候,林伯渠在比他大7岁的堂兄林修梅的指点下,习千字文,读三字经。熟读诗书的父亲林鸿仪也经常带他走出家门,或登高,或远足,锻炼体魄,开阔眼界。
1896年,父亲林鸿仪受聘于安福县城道水书院教书,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随之来此。甲午战争的失败,保守落后的湖南猛然惊醒,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图谋新政,以救中国。林伯渠的父亲也是一个思想与时俱进的人士,面对甲午战败,他愤然指出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割据我土地,重耗我金币”。然而究其原因,他认为是“中国之孱弱实甚耶”。一个自己衣食无忧之人,却对劳动人民满怀同情之情,对祖国的灾难深感忧虑,这一切无疑深深影响着年幼的林伯渠。
1898年的一天,林伯渠登上了书院东南方的奎星楼顶,近看道水,碧波荡漾;远望浮山,云遮雾掩。然而书院近处,却是烟雾缭绕,城隍庙、龙王庙、火神庙,殿宇森森,神像林立,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神吗?第二天,林伯渠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年已18岁的林修梅和另外一个同学黄右昌。二人听罢,决定一起捣毁这骗人的神庙。为了成功,他们特意把知县的儿子也联络了进来。夏末的一天,在林修梅的指挥下,林伯渠和十几个同学行动了,喊的喊、推的推、拉的拉,砸的砸,一举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由于知县的儿子参加了,加上林修梅、林伯渠的祖上也有过功名,在地方上也算是名人之后,捣毁神庙之事也只能不了了之,反倒是林伯渠等人欢欣鼓舞,助长了少年英雄气慨。
戊戌变法失败后,林伯渠随父亲进入澧州钦山寺学馆读书。1902年,16岁的林伯渠考入在常德刚刚成立的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西路师范学堂房屋是由原来的明朝王府几经兴废改建而成,模样已大非昔日,遗物只有几块大石磉和一口胭脂井。林伯渠对从王府到学堂的变化,大有感触,于是写道:
此是何处?父老传言,云是昔日王府。断井还浸婢妾泪,遗础犹呻龙凤宇。金屋高悬午夜灯,照得轻歌曼舞。为问当年王后宫,今日该由谁作主?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昔日王府,今日新学堂,新知新潮当由此而传播。林伯渠这一吟咏,辗转相传,终为西路师范学堂主持者,昔日维新风流人物熊希龄所得知。熊希龄欣赏林伯渠是个人才,便指点林伯渠课余读一些有益于青年的新报刊。
此时,在西路师范学堂中,公开半公开的流传着一些进步书刊,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严复译的《天演论》、康有为和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等,到了1903年下半年,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邹容的《革命军》也在学校秘密传播。在这些新书报中,林伯渠受影响最大的是《新民丛报》。该报本是一份维新报刊,梁启超本意也在于恢复“百日维新”新政,实行君主立宪,但是许多人正是经过梁启超而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革命潮流,林伯渠就是这种人。
1903年冬,林伯渠以西路师范学堂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赴日官费留学的资格。次年的春天,林伯渠告别家人,到达日本东京,进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东京正是当时革命风潮激荡之地,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林伯渠的人生信仰也将发生急剧的变化。
频将泪雨洗乾坤
林伯渠到东京留学后,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姚宏业、程潜等人,他的革命思想逐渐增长着。
1905年8月13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东京富士见楼发表革命演说,孙中山激情的演讲,宏伟的气魄,开阔的视野,给林伯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最深的是孙中山说的这一段话:“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这段话一下子解决了长期憋在林伯渠心里的疑问:是走君主立宪维新之路还是走民主共和革命之路问题,至此迎刃而解,自此后林伯渠决心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在黄兴和宋教仁的介绍下,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他便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1906年年初,受同盟会派遣,林伯渠回到长沙办理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这两个学堂都是同盟会在湖南用以掩护地下活动的机关。林伯渠还兼管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湖南的秘密发行工作。
1906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林伯渠和友人登临岳麓山。看着陈天华和姚宏业的新墓,林伯渠感概良多。为抗议日本政府、警醒同胞,一步一步走向东京大森湾冰冷海水的陈天华,愤而投黄浦江自尽的姚宏业,悲痛愤怒的公葬陈、姚二烈士于岳麓山的三湘人士,这一幕幕就在眼前。可是国家如此黑暗,何日是尽头?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此时此刻,面对烈士的鲜血,面对巍巍麓山,林伯渠泪如雨下,写道:
到处枫林压酒痕,
十分景色赛天荪。
千山洒遍杜鹃血,
一缕难招帝子魂。
欲把神州回锦绣,
频将泪雨洗乾坤。
兰成亦有关河感,
不信沉沙戟已深。
革命志士死难,“频将泪雨洗乾坤”,但是“不信沉沙戟已深”,坚信革命必将再起。
1907年,林伯渠受同盟会总部的派遣,到东北从事边疆革命。林伯渠以随东北吉林巡抚朱家宝办教育的身份到达东北后,以办教育为掩护,联络绿林豪杰,配合宋教仁联络当地“马贼”起义,未能成功。随后,适逢日本妄图侵占中国东北延吉地区的“间岛问题”爆发,林伯渠、宋教仁、吴禄贞深入延吉地区,联络马帮首领韩登举,获得了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伪证的资料,终于协助潜伏在军界的同盟会会员吴禄贞(时为吉林省边防会办)收回了主权。
1910年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1911年林伯渠奉命回到上海,被派往常德运动西路巡防营,准备两湖起义。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南响应起义,但不久湖南政权落到了立宪派手中。林伯渠不能留在湖南,去了上海、南京。
辛亥革命后,林伯渠本以为推倒了皇帝,民主共和议会制度这付“救时”药方定会挽救“东亚病夫”。但是事实破灭了幻想,孙中山也无可奈何将总统一职送给了袁世凯。随后宋教仁力图组织责任内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又被醉心独裁、日夜做着皇帝梦的袁世凯暗杀。革命者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奋力反抗,“二次革命”爆发。林伯渠对于自己的入盟介绍人惨遭杀害,满腔悲愤,他接受革命党人的命令,出任湖南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但是由于力量相差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林伯渠受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一文一武,大有作为”
二次革命失败,林伯渠一度陷入迷茫之中,加上他体弱多病,经常服药,而且“心情恶劣、精神昏瞀”。从第一次留日到现在逃往日本,重新进入学校,已经十年了,他感概道:“转瞬十年,依然故我,家国身世之感,其曷能已。”他在《宗楼看雪》中写道:
沉沉心事向谁说,
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
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
到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浑不语,
明朝有意弄晴晖。
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革命之路在何方?然他并不气馁,坚信只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光辉前景一定能够实现。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林伯渠和堂兄林修梅毅然参加,追随孙中山。孙中山对林氏兄弟的忠心耿耿,极为感动,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作为”,极为器重。
1915年,北京城内,袁世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称帝准备活动。东京收买革命党人的工作,也在添薪加油。袁世凯派同盟会叛徒蒋士立携巨款50万到东京,与驻日公使陆宗舆配合,进行收买活动。蒋士立公然设立办事处,凡国民党人不论是谁,只要前来办理自首手续,一律按质论价,或补给留日官费,多少不等;或资遣回国,予以官职;或厚馈款项,送往欧美休养。当时亡命东京的党人,大多生活困难,因而堕志丧节者不乏其人。对于湖南籍党人而言,湘中方面首先有前陆军第三师师长唐蟒与其亲信周鳌山等30多人,湘南方面则有参加过武昌起义时任上校团长的雷英以及其亲信萧志坚等40余人,均被收买。湘西方面的中华革命党湘支部长覃振和湘军总司令林支宇、参谋长林修梅却壁垒森严,不为所动。
蒋士立发现林伯渠是中华革命党湘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林修梅的兄弟,而且他们兄弟都住在愚公之谷,于是请陆宗舆找到林伯渠。陆宗舆开口便说:只要林修梅肯拥护袁世凯,服从北洋政府,就会有超级优遇,与唐蟒师长相当,而优于雷英团长。林伯渠回来后立即把情形告知了林修梅。林修梅是一个性烈如火的人,听到林伯渠一说,顿时大怒,骂道:“狗东西,蒋士立,自己撞上了阎罗殿。”林修梅恼火蒋士立,而且还得知雷英叛了党,心里更加气愤,立即告知了湘支部长覃振,总司令林支宇,大家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林修梅派出覃振的外甥——少年吴先梅执行刺杀蒋士立的任务。吴先梅怀揣手枪,化装来到蒋宅,自称是叛徒周鳌山之弟,有要事需面见蒋。蒋走到门口时,吴一枪把他打倒,又补了第二枪,即返身逃出。
蒋士立一案,林伯渠告知在先,林修梅谋划其中,吴先梅执行甚力,是反袁运动中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一次重大打击。没有这一打,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收买还会肆无忌惮,有了这一打,蒋士立躺在医院,虽受伤未死,但也吓得要命,自动写了悔过书,求革命党人饶他残生,从此销声匿迹,这个自首办事处也就关门大吉;唐蟒、雷英等人则惶恐不已,赶紧逃离东京;周鳌山悔罪求饶,萧志坚退学回家。留日学生则欢欣鼓舞,情绪高涨。
1916年年初,林修梅回到湖南,组织湖南护国军,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不久,林伯渠也离开东京回到湘南,任总司令部参议。兄弟二人为反袁驱汤奔走各方,历尽艰险。反袁成功后,林伯渠任谭延闿省长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不久又代理政务厅长。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林伯渠辞去各职,再次奔赴湘南,为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参加护法运动。危乱之秋,林伯渠始终追随孙中山。然而孙中山借助南方军阀的力量来进行革命的努力却不断地遭到失败,林伯渠渴望“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新路在哪里呢?
再造神州,肝胆相照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迅速传到国内。1918年春,行走在郴衡道路途中的林伯渠获悉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句,“路引平沙履迹新”,心情是欢愉的。李大钊的不断来信,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潮,给他“新的启示”。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传”人,也是林伯渠的入党引路人。林伯渠与李大钊结识较早,他是在第二次到日本期间与到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相识,并结为挚交的。
李大钊1914年到达日本留学。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李大钊等积极行动起来,谋划反袁救国的方策。他受留日学生总会之托,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反响,李大钊也因此被留学生称之为“文胆”,扬名东瀛。就在此时,林伯渠和李大钊相识了,共同的志趣,共同的遭遇,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15年年底,林伯渠与中华革命党人易象等湘籍留日学生,发起组织了以开展反袁斗争为主旨的团体——乙卯学会。此时,李大钊与一些同学发起组织了同样的反袁团体——中华学会。到1916年1月,林伯渠与李大钊等人决定,将乙卯学会与中华学会合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一个较大的以“再造神州”、“图谋国家富强”的革命团体——神州学会。李大钊被选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等任干事。至此,林伯渠与李大钊成为一个团体的战友。后来林伯渠回忆说李大钊是他“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由日本回国到达上海,此时林伯渠已在湖南进行反袁斗争。9月林伯渠与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的李大钊建立了通信联系。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并没有忘记在日本时结下的“最好的朋友”。1918年春,李大钊不断地写信给林伯渠,“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寄给“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林伯渠从中逐渐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同时,也对由中华革命党又改组成的中国国民党的境况及前景感到很迷茫。1920年冬,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交谈。林伯渠决心献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国民党营垒中最早脱颖而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在中共一大前参加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林伯渠加入共产党,不仅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也与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相关,是对辛亥革命反思、继承、超越的结果。林伯渠参加共产党后,并没有离开孙中山,也没有脱离国民党,而是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
林伯渠对于他的入党引路人李大钊是十分钦佩的,也一直深深怀念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遗憾的是,1927年4月,李大钊不幸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林伯渠为失去这位“再造神州”而肝胆相照的“最好的朋友”伤心不已。1958年,林伯渠写了《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深切缅怀这位引路人,诗写道:
登高一呼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
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
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
敢抛热血护新生。
“敢抛热血护新生”,既是林伯渠对李大钊创建中共的历史作用和丰功伟绩的高度评价,又何尝不是他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护新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