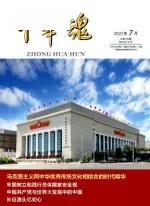震撼人心的传奇经历——读《百战归来认此生·曾志回忆录》
文/马蓥伯
我初识曾志是在党的十四大上。1992年,我有幸在会上与曾志同志相遇。一天午餐前,我们同坐在饭桌旁,位置是个犄角,她居然没有挪动身子就看清楚了我胸前代表证上的姓名,使我惊异。后来我才知道,她当时年已八十有二,在中直党代表中,她是年龄最高的。如此耳聪目明,实足令人艳羡。此后,她的人生故事便不断进入我的视野。最近我读了她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生》,对她的震撼人心的传奇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忠贞的战士 坎坷的人生
曾志15岁便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当时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唯一的女兵,也是大革命年代最早投笔从戎的女青年之一。她原本是个童养媳,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奋起反抗封建婚姻,毅然退婚,摆脱精神枷锁,逐步树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奋斗的志向。直到晚年,她还牢记早已成为革命先烈的夏明震在她入党仪式上的致辞:“肉体只是人的驱壳,政治生活是人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和灵魂支柱。肉体可以牺牲,政治生命却不能动摇改变。”她入党时的誓词是:“从今以后,我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她当时还不满16岁。揆诸此后将近70岁的人生旅程,充分证明她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词。
夏明震是她的入党仪式主持人,不久以后成了她的丈夫,尔后不久便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回忆录中对夏明震之死的记述可谓惊心动魄。书中写道:“夏明震悲壮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我,他才21岁,本不该死啊!但痛定之后,有更多的思考,并且愤怒使我加倍的坚强。我觉得自己不能在众人面前哭,我不愿让人看见我此刻的脆弱。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也不愿只为自己亲人的牺牲而哭泣。”继任的丈夫蔡协民也于1934年被叛徒告密,英勇就义,时年33岁。正如曾志所说:“他以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书中关于她和她的亲人为革命牺牲一切的记述可谓比比皆是。当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紧张,她从母亲寄来的四十块大洋中取出一半交给了组织,自己留下一半。她的初生的孩子送给了一位中医,由党组织收了100块大洋。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这哪里是送?这是卖!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她和陶铸的友谊和爱情感人尤深。她是从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事件的传说中得知这个事件的总指挥陶铸的。当曾志耳闻目睹了陶铸的所作所为后,她觉得陶铸不仅是个有作为的革命者,而且“还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富有同情心,对同志像严冬里的一把火”。她同陶铸并肩战斗了大半辈子,其间的革命情缘可歌可泣。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时写的《赠曾志》一诗令人读后潸然泪下:“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含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从这里,我们能不被这对革命夫妇为党的事业献身的赤胆忠心感动得无以复加吗!坎坷的人生更彰显了战士的无比忠贞!
革命的征程 宝贵的记录
曾志是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参加革命很早、斗争经历极为丰富的妇女老前辈。革命战争年代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往事她都亲身经历过。例如,毛泽东有一首词《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我们对此都耳熟能详。但当时的战斗状况究竟怎样却缺乏身临其境的感受。曾志以其亲身的经历为我们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1928年8月,湘赣两省的敌人,乘红军主力部队正在向南外线作战之机,以四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东西夹击“会剿”,企图一举加以荡平。当时在山上的红军不足两个连,且兵力分散在周围的八个哨口。为了抗击敌人,井冈山上所有的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了,当时已有7个月身孕的曾志也参加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当敌军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攻的时候,他们就用红军在打许克祥时缴获来的两门炮和自制的“松树炮”狠狠地还击敌人。所谓“松树炮”,就是将松树挖个窟窿,里面放进黑色炸药,还有破碎的铁片、碗片一古脑儿全射出去。再加上居高临下滚滚而来的乱石、断木,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屁滚尿流。敌人最后丢下了一个县长、一个团长和无数尸体,狼狈地连夜逃回老巢。如此战斗情景,读来令人神往。
当然,斗争并非一帆风顺。挫折和失败是常有的事。曾志在回忆录里对此并不讳言。例如,儿童团和少年队曾经到寺庙里砸菩萨、赶走和尚,把祠堂中祖宗的神位打碎,甚至发展到连祖坟的墓碑也挖掉,对虐待童养媳的家人进行体罚、捆绑游街示众等。这些幼稚行为造成了老人同年轻人、父母同儿女发生尖锐矛盾。但这些现象都及时得到了制止,使革命事业得以顺利推进。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动乱中,曾志的亲人遭到了残酷的迫害,陶铸的屋里设了三个哨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子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夫妇说话时也贴身而站。此种精神酷刑使人分分秒秒都处在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至于残酷的批斗更是惨绝人寰,恰如陶铸所说:“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
革命的征程确实崎岖不平。然而正是在这种坎坷之中,突现了精神巨人的雄伟身躯和旷世魅力。
领袖的形象 难得的剪影
曾志在回忆录里刻画了我们的党的领袖的形象。例如朱德,虽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1928年2月的一天,工农革命军占领了郴州,翌日上午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师长朱德在戏台上作报告。这是曾志第一次见到朱老总,那时他才四十多岁,围着一条绿围巾,穿着一件很长的黄颜色的齐脚大衣,显得威风凛凛,精神焕发。晚间曾志被领去见朱德,此时的朱德与白天在戏台上的情景判若两人,非常和蔼可亲,说话和风细雨,如同慈母一般。这使曾志原来有些害怕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这便是朱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的杰出的军事家!
毛泽东在回忆录里的初次出现,是在行军途中。他来看望蔡协民和曾志夫妇。尽管毛泽东当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架子,和蔡协民就像一对老朋友,两人亲热随便,侃侃而谈,似乎把曾志给忘了。她端详着毛泽东,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深沉。毛泽东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热情风趣,平易近人。曾志对他即由崇敬变成了仰慕,从此毫无拘束。诚如曾志所说:“就是后来人们把他神化而顶礼膜拜时,在我心目中,他还是那个热情风趣、平易近人的毛泽东。”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剪影,却深入人们的脑海,这便是没有光环、没有文饰的真实的毛泽东!
在曾志的回忆里,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感人尤深。《回忆录》里专门有一节《毛泽东的“座谈会”》,生动地记述了她有幸亲身参加的毛泽东召开的旨在调查研究的多次座谈会。每次座谈会邀请的人不多,不是一问一答,而是生动活泼,犹如在唠家常。毛给大家提的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大家见他这样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也就无拘无束,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有时他们也提出一些问题,毛对此总是谈笑风生,旁征博引,能讲出许多道理来,并且通俗易懂。毛主持的座谈会,曾志都在边上旁听,有时帮忙做些杂务,但就是不要她做记录,“毛委员每次都是亲自记录,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
回忆录记述了曾志与毛泽东的吵架。一次,毛泽东带队伍去江西,把怀孕的贺子珍托付给曾志,请她“负责照顾”。她误以为让她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于是,“要你照顾!”“就是不照顾!”如此争执起来。后来终于弄明白“照顾”之意不过是关心些而已,并非专门护理。这场争吵才烟消云散。曾志写道:“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委员,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与毛委员吵架!”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领袖是人不是神,对领袖不是畏惧而是崇敬,这才是革命队伍里领袖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才是新时代人与人的社会主义本质。
回忆录里还有毛泽东学英文的剪影。“我看到毛委员那时很用功,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当时初中二年级的课本。虽然他有很重的湖南口音,读得也不很准,听起来令人发笑,但他天天读。”毛泽东的勤奋好学可谓跃然纸上。曾志还记述了她陪同毛泽东去找书的经历:“我曾陪同毛泽东到已跑得空无一人的省立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埋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几担的书,什么内容的都有。后来听说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的个人财物依然少得可怜,惟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有半卡车之多。……他用这批书在瑞金创办了中央图书馆,丰富了苏区红军的文化生活。”
以上这些虽然只是若干剪影,但却勾勒出了真实的人民领袖,他的风采,他的魅力,令人肃然起敬,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