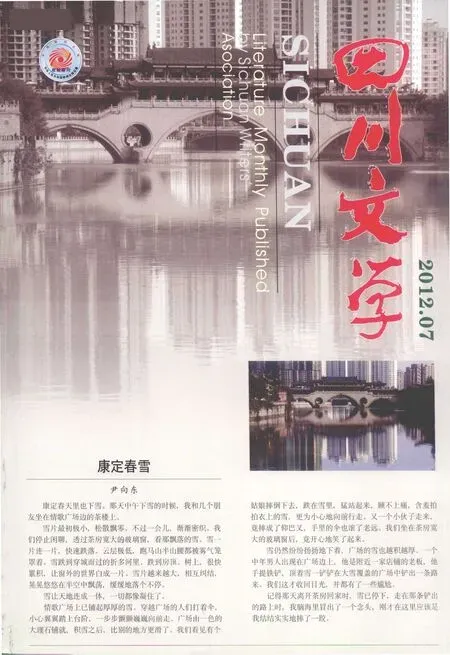隐居者
□小 米
砍柴、种药材、挖野药、打野菜、摘野果、积聚修房子用的木头和椽子、砍打家具或装修房子用的木料,还有打猎,所有这些,村里人都得到很远的山林里去才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些东西既可以自己享用,也能够拿来换钱。森林似乎是人们取之不尽的宝库,想什么就去找什么,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农闲的时间,人们多半到森林里去找一点儿“经济”,用来补贴家里的日常开支的。到山林里去,一般都是早出晚归,偶尔也有在山林里过夜的。从村里出发,顺着村边的河,逆流而上,大约走二十多里山路,就到了一处叫做“唐楞杆梁上”的地点。这一道梁是原始森林和灌木林子的分界点,它仿佛是个门户,过了这道梁,就到了生机盎然的原始森林里。一头扎进去,往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用村里人的话来说,是“一把菜籽撒到了海里”。森林里的树木多为高大健硕的乔木,遮天蔽日,林子里气候更湿润,植被更茂密,不像山梁下或山梁外的那些林子,是一副苦巴巴的样子。
上这道梁之前,就得爬山。爬山的路程,约为五里。
从村里出发到爬山以前,这十多里山路,都是顺着流经村边的那条河走的,路较为平坦,走起来也不费力,从爬山开始,就得绕开河水,人要上山,河水却还在峡谷里无声无息地流。上山的路是突然陡峭起来的。这是到山林里去,最难走的一段路。要爬的这座山,它的山腰部位,就是我们称之为“唐楞杆梁上”地方。从这儿开始,再走约一百米,道路又跟河会合了,也再一次平坦起来了。人们又可以跟着河走。
到山林里去,到了“唐楞杆梁上”,才刚刚走了一半的路程。
我们的祖先在开路之初,在他们打算要开发或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多半都是跟着河流前进的。河流是参照物,是坐标,也是人的开路先锋。河流途经之处,由于流水的长期冲刷与无数次的改道,在河的两岸,道路已经有了雏形,人可以省不少力。这种最初的道路,往往不是什么人专门修建出来的,通常都是无数行人,将它一遍又一遍地走成了路的。跟着河流走,随时随地地,河水还可以为饥渴的行人提供畅饮的机会。最初开辟道路的先行者,不用说是非常聪明的,也是有意无意地遵循“跟着河走”的原则的。
那么,在这条道路的开辟之初,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绕开这么一段路,合而分之,分而又合呢?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到了“唐楞杆梁上”,在它旁边峡谷里,有一处高大的断崖,无路可以通行,河水从断崖上落下去,形成了极为壮观的瀑布。这个瀑布藏在茂密的树林里,无人近前看过,我也没有见过,目前所有仍在世的人,几乎都不知道瀑布是什么样子,它的下面又是什么样子。人们都说,瀑布落下去的时候,中间没有接触任何山体,从断崖那儿,直接落在了谷底。从周围的地形来判断,我也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从与河的分路口开始,直到瀑布下面,这一段河流在人们眼里,格外神秘。有人想近前看看瀑布的落差,但进不去,河面被高大粗壮的藤蔓植物缠绕着、覆盖着,像一条地下河,这些藤蔓植物多半还有刺,这更增加了进入的难度。这一段河谷,即使在农闲时放养的骡马也从不涉足,更别说是人了,偶有骡马撞入也是有去无回,从未有侥幸得以生还的。这些误入歧途的家畜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总之,从此,在人的世界里,再也见不到它了,在人的意识里,就当没有它了。
把那些带刺的藤蔓砍掉再进入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一个人这样做,怎么也得花费一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仅仅为了看看瀑布,或者,仅仅为了寻找一头家畜,那也太不划算了不是。
据说,瀑布下面,是一口天然形成的石缸,这口石缸的高度至少有三四丈,它的粗细,要几个人才能抱得住。从万丈悬崖上掉落下来的河水,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石缸里,又从里面漫溢出来,成为一个千古奇观。
我反复而又仔细地想过,这并不是没有可能。水从那么高的地方砸下来,先把岩石砸成一个巨大的石坑,从坑里漫溢出来的河水,继续冲刷并切掉石坑周围的泥土和质地较软的岩石,天长日久,又形成一个比水面越来越高的天然石缸,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这要多少年才可以做到?是几万年,还是几十万年?
人们众口一词,传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应该不是妄言。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这石缸,就一定有人见过,也就是说,有人曾到瀑布下面去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的一位远房堂叔,名叫玉成的,跟人相约,到山林里去打猎。
这个邀约玉成的人,是个刚迁移到本村不久的外来户,他的老家,在非常遥远的河南省。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他为什么要携家带口地迁移到我们村来?我那时年龄很小,也忘记了原因。我只依稀记得,这个人有老婆,她的名字,好像叫做映秀。他们有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这一家人买下了村里闲置不久的知青点,住了下来。
这家的女主人待人和气,脾气很好。他们家的老大是个儿子,常常跟我一起玩耍,我偶尔地,出于好奇,也跟着那个孩子到他家里去。我只记得映秀对我的态度是殷勤而周到的,刚到她的家里,映秀就会问我饿不饿,想不想吃点儿什么,或者问我是不是渴了,要不要喝水。映秀还要求她的儿子,一定要跟我“好好玩”。她的意思是,不要玩出不愉快来。孩子们在一起,这样的事情,难免会发生。人们说,小孩之间的关系是“狗亲家”,看起来亲热得不得了,转眼之间,却又打起来了,或者刚刚打了架,转眼之间,又亲热起来了。在孩子身上,这的确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因为孩子心无杂念,他们的思想感情,往往直接地表现在自己的语言或行为上,不像大人,心里那么复杂,总是遮遮掩掩。
映秀原本不必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表露出过于热情而讨好的态度,可是,她对村里的大人小孩,一律表现得客气、尊重。她一视同仁。她也常给村里人施以小恩小惠,显得很大方,一点也不小气。这使她在村里广泛地赢得了人们的口碑。映秀的男人,脾气也不错,跟什么人都合得来。俗话说:“吃得了亏,打得了堆。”意思是,只有不怕吃亏的人,才能够跟别人友好相处。映秀的男人,甚至他们一家人,都是这样的性情。我现在想,她这么做,可能跟自己是外地人的身份不无关系吧,他们是想尽力获得村里人的广泛认可,从而更快地融入这个村子。
这家的男主人,有个特别的爱好,酷爱打猎。刚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一旦得了空闲,他必定扛起猎枪,带着猎狗,独自一人,向山林里走去。猎狗是猎人的好帮手,既可以给猎人寻找猎物,也是猎人的伴儿,可以给猎人壮胆。那时候,山林比现在茂密得多了,山林里的野物,也是时常可以碰见的,比如熊、狼、鹿、麝香,等等,在山林里走动,一不小心,野物就能跟你撞个满怀,不足为奇。
此人想要猎获的主要是麝香,别的猎物即使碰见了,一般,他也不会去打。狼太狡猾,是打不着也不必费心去打的;熊掌虽然特别值钱,熊又不敢轻易惹,怕斗不过它;打鹿虽然可以吃到鹿肉,又觉得不合算,所得无几,还浪费弹药。故乡不成文的规矩是,只要是看见你捕获到野物的人,无论你认识不认识,肉却应该是人人有份的,你要是不分一块给别人,就是瞧不起人家,必定得罪了人家,人家嘴上虽然不说,心里肯定非常不痛快。俗话说:“见了面,分一半。”就是这样的传统。人们普遍认为,野生动物不是谁家的私有之物,是属于大家的,即使是你独自猎获的,那也不是你把它养大的不是?你仅仅是猎获了它,如此而已,所以不能全都归你。每天到山林里去的人都是很多的,你往回走,别人也在往回走,你扛一只猎物一路走回来,不知道要碰见多少人。每遇见一个人,你都得分出去一块肉,到家的时候,也许,你能够拿回自己家里的,还不够一家人吃一顿。
也是因此,此人专门打麝香。而且,只是打伤它,不是打死它。他瞄准的是猎物的腿,不是猎物的要害部位。一旦有了猎获,他也是只近前看看,如果是母的,他就放了生,假如是公的,他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来,割了麝香的香囊,别在腰间,照例,还把猎物放了生。据说,麝香是不会因此而死的,伤口可以愈合,麝香还能再生产。他要是万一失了手,将猎物打死了,这才不得不割下一条腿来,犒赏他的猎狗,再割一块肉下来,打算带回家。他把剩余的肉扛到路上,路过的人,谁想拿谁拿,谁想拿多拿少,随便,不关他的事了,总之,肉是人见人爱,不会浪费的。他打算拿回家的肉本来就不多,最多也就五六斤重,走在路上,即使别人看见了,他也不会分给任何人,跟他们说清楚就是了。
此人的言外之意是,你想要,你到某某地方自己去割一块不就行了,我没有给你送到手里的义务是不是?他这么做了几次,人们果然不跟他计较。这种行为慢慢地,到了后来,也就成了猎人的传统。所有打猎的人都这么做。
麝香的香囊,在那时候,一只,一般可以卖到四五十元,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此人后来跟我的远房堂叔玉成好上了,因为玉成也喜欢打猎。
他们常常结伴进山。
很平常的一天,很偶然的一次,玉成把他的同伴,也就是那个河南人,一枪打死了。
不是玉成跟他有什么过节,也不是那人对玉成不友好。是玉成把他当成了猎物,这才在情急之中扣动了扳机。
玉成以为有了收获,他兴冲冲地奔向猎物倒下的地点,近前一看,他傻眼了,倒在血泊中的根本不是什么野物,而是一个人,是他的同伴。
玉成吓得魂飞天外。
玉成发现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同伴,也就是那个外地人,还没有咽气。玉成愣了片刻,怎么办?玉成的思想意识激烈地斗争了一会儿,之后,他赶紧将河南人扶起来,背在背上,飞快地往村里走。玉成回到村里已经是三个多小时以后的事了,回到村里的时候,河南人依旧没有咽气。人们闻讯纷纷前来围观,都在暗自替玉成庆幸,期间,人们自告奋勇,接替玉成,并跟玉成一起,以更快的速度把受了重伤的河南人向乡卫生院里送。可是,快到乡卫生院的时候,河南人终于坚持不住了,咽了气了。
玉成张罗着,替河南人办了后事。
办完后事的第二天,玉成不见了,村里村外,旮旯角落,踪影全无。
玉成逃了。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把要逃走的计划,对他的媳妇兰香,也没有吐露一个字。
玉成逃走之后,是生产队长到乡政府和县公安局报的案。这不能怪他,这是他作为生产队长的职责所在。映秀并未告发玉成,她还没有从悲痛中缓过神来,她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案子报了也就报了,跟未曾报案没有什么不同。没看见民警调查破案,也一直没有玉成的消息。民警只到村里来过一次,了解了一下情况,临走,民警留下话来,说是谁发现玉成了,要给县公安局报告。民警离开之后,再未到村里来过。
人们都认为,玉成是跟兰香商量好了,才逃走的。兰香又没有办法替自己开脱,她明白人们不相信她说的话,所以什么也不说,更不为自己辩解。玉成逃走后,大家都同情映秀的遭遇,渐渐地,连玉成的媳妇兰香,也因为玉成的失手误伤,自知理亏,在村里呆不下去了。半年后,兰香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而且一去不回。玉成的家里只留下玉成的老父亲,孤身一人,艰难度日。
虽说是外来户,可是,这一家河南人在村里度过的时光,原本是非常不错的,跟任何人处得都很融洽,可能是迁到这儿之前就有一些积蓄吧,他们的日子过得也不像村里人那么拮据。映秀的男人死后,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大约一年之后,映秀独自一人去了趟河南老家,不到半月,她又回了村。耽搁得久了,丢在这边的儿女,映秀放心不下。其实,在她离开的这一段时间,村里的人,尤其是附近的邻居,轮流着,在做饭前就给这三个孩子预计了饭量,饭做熟了就把映秀的孩子叫到家里来吃。映秀回村后,当然知道这些事情,她临走前并未叮嘱邻居们照看她的几个孩子。映秀于是分别上门,真心诚意地,向邻居们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映秀又坚持了大约一年的光景,期间,她找过乡政府,也找过县公安局。人们估计,关于男人的死,她想等一个结果。可是,没有什么结果。连玉成的人都找不到,公安局当然也就抓不到他,一切只能悬而未决。
映秀坚持不住了,等不住了,她又去了一趟河南老家。这一次,映秀很快就回了村。回村之后,映秀就开始动手变卖房屋和家里的器具,能卖的,贱价卖了,不好卖的,这家一件,那家一件,也送了人。
她很快就处理完了。
映秀带着她的儿女,离开我们村,举家回到故乡去了。
送映秀离开村子的时候,全村人都深深地、由衷地,感到内疚。整整一个村子的人,在映秀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好像不是玉成误伤了她的男人,好像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或者,都在故意欺负她,排斥她,做下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一晃几年过去了。
大约过了五年或六年,映秀再一次来到村里。人们问她,她说她还是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她还说,孩子们都大了一些了,可以帮她干活了。关于她在河南老家的生活状况,映秀似乎不想多说,而这恰恰是人们很想了解的。映秀既然不想说,人们也就知趣地闭上了好奇或关心的嘴巴。映秀是来打听案件的消息的。她说她已找过县公安局了,还是没有什么结果。映秀到村里来,说是专门前来看望大家的。她给每一家都买了小礼物。
映秀只在村里住了一晚就走了。
临走,映秀说,她不打算再回来了。
听说兰香至今还未回村来,映秀对村里人说,你们给兰香带个话,让她回来吧,她又没有什么错。
关于案件,映秀说,她不想再等那个结果了。
从此,村里人不知道映秀的任何消息,仿佛这个人,包括她的一家人,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
兰香虽在娘家住着,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可是,即使如此,她带着孩子,仍然在娘家村里,生活了将近十年,玉成虽然失踪了,她却没有改嫁。兰香也在等。十年之后,兰香确信映秀一家人是不会回来的了,这才带着孩子回到村里来住。
兰香不能不回来,因为玉成的父亲去世了。
兰香要是不回来,这个家就名存实亡了。
三十多年后,玉成意外地回了村。
三十多年来,玉成遭的罪,受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为自己的失误,可以说,也是付出了代价的,虽然侥幸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但他不能逃脱的,是良心的不安与谴责,他付出的是生不如死的三十多年美好人生。村子里的人,或远或近,毕竟都是玉成的亲戚,人们理所当然地原谅了玉成,再没有人到县公安局或乡政府去告发他了,也没有人到村里来找他,追究他过失杀人的事。玉成也没有到县公安局去自首。人们都说,要是玉成当初就去投案自首的话,也许不会判死刑,也许他十年前就回来了。可是,生活或人生里,丁是丁,卯是卯,是没有也许更不可能重新再来的。
人们见到玉成的时候,玉成须发飘飘,须发皆白,六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仿佛是八九十岁行将就木的人,苍老得不成样子了。如果不是玉成自报身份,即使是兰香,也认不出他来了。
这三十多年,玉成是怎么过的?
故事又要回到开头,重新从瀑布底下的石缸那儿说起。
据说,玉成是在石缸旁边,独自一人度过这三十多年时光的。也就是说,玉成并未逃远,而是在距离村子很近的地方,过了三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玉成说,离家出逃之后,他就躲在他跟河南男人打猎时,出事点附近的那一块林子里。玉成先是在森林里躲躲藏藏,漫无目的地转悠,饿了吃野果野菜,渴了喝一口山泉水,晚上找一个背风而干燥的地方,抱着猎枪打盹儿。玉成出门前带足了火药和铁砂,枪是他的胆,也是他用来吃饭的工具。他不能没有它。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玉成误打误撞,终于走到了瀑布底下,石缸跟前。
玉成被他看见的一切,惊呆了。
石缸旁边,是一块巨大的空地,靠近悬崖的山根下,有炕,炕上有草,可铺可盖,炕也被柴草围成的简易屋子庇护着,只要稍加修缮,足够遮风挡雨。草屋外边,赫然半依着一具完整的人骨架。这让玉成不由得冒出一身冷汗来。
镇定下来之后,玉成又仔细查看。在草屋一侧,有石头砌成的灶,灶上有锅,尽管锅已锈迹斑斑,玉成试了试,勉强还能凑合着用。在阳光能够照到的开阔地带,是一大片已经荒芜的曾被开垦过的土地,足够一个人耕种,过活。玉成想,这里的一切,肯定是那个死在这儿的人留下来的。玉成又想,别人来不了,或根本不打算到这儿来,野兽也来不了,即使附近村民喂养的家畜,照样到不了这儿。周围都是天然的屏障嘛。这一点,作为本地人,玉成是明白的。
天无绝人之路。
没有地方可去,也无路可走,玉成觉得,对自己来说,这儿真是一个好地方,好像是专门为自己预备下来的。
玉成挖一个坑,掩埋了那人的遗骨,在石缸旁边,住了下来,过起了野人般的生活。后来,玉成又在那人的墓旁,给被他误杀的河南猎人,也修了个坟头。闲来无事,玉成就在两个墓之间,跪一会儿,顺便想些事情。
不知道哪朝哪代,这一带战乱不断,紧接着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闹了一场大饥荒,那一年的庄稼,颗粒无收。据说,天灾加上人祸,远远近近的村子里,很多人顾不上脸面,勉强挨到秋天了还是没什么指望,就纷纷背井离乡,干起了讨饭的营生,放不下脸面因而未出门去讨饭的,因害怕乱兵而没有胆量出门讨饭的,在村里,也有近一半人,这一半人里,又有一半,就在那一年,最终饿死在自己的家里。
有一个人,为了躲避战乱与饥荒,也为了不被饿死,想出了到山里去打猎来填饱肚子的办法。
这个人在林子里转悠了好多天,却没有发现任何可供猎获的野物。他非常后悔,迷迷糊糊睡了一觉,梦见瀑布下面有成群的野物。他睡醒后想,不如到瀑布下面去看看。就这样,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挣扎着,轻易就走到了石缸跟前。可是,石缸周围不过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他连一只野物也没有看见,这个人后来就被眼前的景象给迷住了。他想,在这里种出来的庄稼总不至于还会被太阳晒死吧?天再怎么旱,水这么近,他完全可以浇灌他未来的庄稼,不是吗?
这个逃荒的人在离开村庄前,家里就没有一个亲人了。他在石缸一侧的空地上,搭建了茅屋,开垦了土地,从此过起了隐居的日子。他的后半生就在那儿生活。只是到了后来,这个人老得快要死了,才萌发了重新回到家乡的念头。他想埋入家族的祖坟,以便死后可以把自己写进家谱里,可以享用后辈的祭拜。但是,他出发了好多次,每一次都无功而返,最终不得不终老山林,野人一般过完了残生。
上一任隐居者的事,玉成是从那人用木炭写在石壁上的文字里,了解到的。玉成想说多少,别人就只能了解多少,关于那个人,除了非解释不可的,玉成才会说说,别的,他不想多说。我曾经问过玉成,他对我,也是不肯多讲一点点,我只得作罢。我能够知道的是,那个隐居者不甘心做一个无名之鬼,故而在临死之前,将自己的生卒年月、来龙去脉、一生经历,包括自己的名字、籍贯、亲属,等等等等,都写了下来。玉成童年时上过几年初小,粗通文墨,那人写在石壁上的文字,玉成多半是认得的。
三十多年里,玉成从来不曾回过一次村子,他坚信自己有能力从石缸那儿走出来,走到他熟悉的村庄里来,但他觉得,自己犯的是杀人的罪,是死罪,不如不回来了。
他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父亲肯定去世了,兰香肯定改嫁了,他冒险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这么,玉成在石缸旁边,隐居了三十多个年头。
老都老了,玉成却又不想像上一位隐居者那样死掉,要不是自己意外地走到了石缸那儿,连一把老骨头都没有人替他埋,这是他最基本的想法。考虑到身后的事,玉成最终选择了回村。玉成是一个普通人,当初,他不想为自己的过失承担什么,也在情理之中。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挽在他心里的疙瘩越来越大,这使他寝食难安。玉成不能不解开它。
玉成横下心来想,即使被公安局抓了去,杀了头,也比死在荒郊野外要好,他想,比起河南人来,他活够了,也活得够本了。
就这么,玉成回了村。
玉成回村后不久,就到县公安局去投案自首。可是,公安人员听了玉成的供述,查阅了他当年的卷宗,说,他的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不予追究了。公安人员留下了玉成的联系方式,让他回去,还说,如果有事,他们会通知玉成的。公安人员还笑着对他说,你的情况,要是当年你没有逃走,也是不会判死刑的。如果那时候就自首的话,最迟十年前,他就该刑满释放,回了村了。
玉成松了一口气,背负了三十多年的沉重的包袱,一下子卸了下来,他觉得一身轻松,说不出的畅快。
当然,他也深深地,为当年的选择,感到后悔。
玉成回村之后,又想起了映秀一家人。无论如何,他仍觉得愧对他们。玉成想到映秀的河南家乡去一趟,去找映秀,求得她和孩子们的原谅与宽恕。可是,映秀一家究竟在河南的什么县玉成也不知道,不用说更具体的乡镇或村社了。玉成没有他们详细的地址,自然是去不了的。他只能放弃这个想法。
回避错误显然是不对的,面对它,才是正确的选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担当,不面对自己的过失,付出的代价,往往只会更大。
再未有人来追究玉成杀人的事情。
玉成后来曾到上一位隐居者所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打听过,那个村子里没有人知道第一位隐居者,玉成也不知道,那个村里,谁有可能是上一位隐居者的后辈。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无人知道那个饥荒加战乱的时期,究竟属于哪朝哪代,是不是真的出现过,更无人愿意认可第一位隐居者,把他看成是他所指定的那个村子里的人。这么一来,无人替第一位隐居者出面上家谱,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谁也不会把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写在自己这个家族的家谱里。玉成想,要是第一位隐居者把他所处的年代也记下来就好了,如果是这样,他兴许还能找出一点儿蛛丝马迹来,替上一位隐居者完成他的心愿。
话又说回来,身后的事,谁会想得那么周到呢?
一个人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一旦分开了,必然被后人忘却,被历史湮灭。
现在,今天,玉成还活着。
玉成死后当然可以写进我们这个家族的家谱里,无论他活着时犯过什么错。因为他最终选择了融入社会,回到我们中间来。
关于石缸的若干传言,都是因玉成之口,才在村子里慢慢传开的。只是由于进入的艰难,也因为忙于生计,并未有人专门到石缸那儿去探险,以此来验证玉成的说法。
一切的一切,只能姑妄听之。
“好人命不长,祸害遗千年。”村里人偶尔想起河南人来,都这么说。这当然是从老一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话。这句话意思是说,品行好的人往往难以终老,反而是品质很差的人,能够长命百岁,寿终正寝。天意就这么不遂人愿,命运就这么不公平。说这话的人,显然是对那个河南人的死,发自内心地,觉得惋惜。
人们感叹说,真是应了那句古话:“生有时候,死有地方。”这的确是一句老掉牙的话,它意思是说,人出生的时间和死亡的地点,包括从生到死的过程,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人们说,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河南人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迁移到我们村来?这当然是唯心的宿命论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时至今日,我的乡亲们仍然相信这样的说法。这当然是人们的传统观念在作怪。
无论科技怎么发达,社会怎样进步,要想改变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传统观念,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不知道映秀和她的儿女们三十多年来,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改嫁。希望她能够再嫁一个好男人,希望她和她的一家人,身体健康,过得平安、幸福。
玉成是这么想的。
村子里的人,也这么想,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