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法律体制碰撞——评《西风落日:领事裁判权在近代中国的确立》
◎吴庆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本文是写给《西风落日:领事裁判权在近代中国的确立》的书评。安国胜著,法律出版社,2012年1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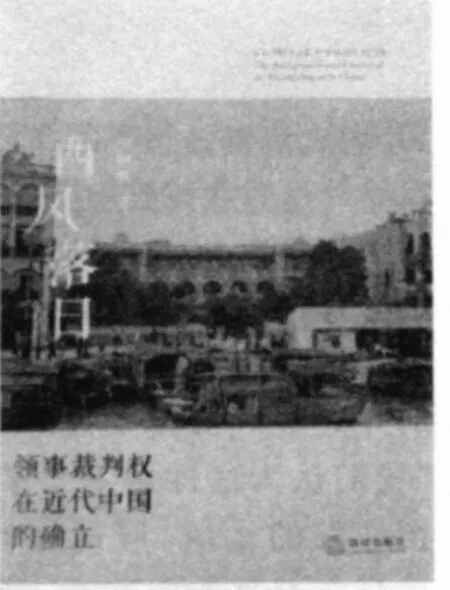
所有民族都源自共同的先祖,只是各自生存在相互隔离的环境中长达几千年,经历了不同的机遇与挑战,衍生出不同的文明。特别是在古老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文明:东方的农耕文明和西方的商业文明。在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底蕴之上,各自独立地演化出了不同的法律制度。
当西方世界开辟出新航线之后,欧洲商人开始在各大洲之间充当“二道贩子”,和世界各地的居民互通有无。一轮伟大的全球化就这么开始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惯例和法律体系也开始相互碰撞。今年1月份面世的新书《西风落日》通过详细讲述领事裁判权在近代中国确立的经过,重新展示出一副历史画卷。
欧洲商人来中国的目的是贸易。贸易需要建立在一整套规则之上。为了贸易持续下去并且降低成本,一些欧洲商人不得不在中国停留。有的停留几周,有的停留数年。这就需要一套法律来处理外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以及外国人和中国之间的纠纷。于是,到底是按照东方的法律还是按照西方的法律处理这些纠纷,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清末开放海禁的早期,解决涉外纠纷都是依照清朝法律和司法体系。中外双方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例如,英国女王和官员都曾经要求在华英商遵守中国法律,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不受英国政府保护。在华英商虽然不情愿认可清朝的司法,但也很快发现他们可以花钱买到他们认可的公平正义。英商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足以冲抵这些开销。因此,英商早期并不抱怨大清律例不公平、不正义,他们只是抱怨地方官员贪腐、商务成本高,同时也竭尽全力保证贸易畅通。
大清皇帝对司法的一次干预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1784年,LadyHughes号上的水手在放礼炮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炮中装有实弹,结果导致两名中国水手死亡。广东巡抚孙士毅原本打算按以往惯例息事宁人,不料当时清政府正在查办西方传教士与内地回民叛乱相勾连的案件,乾隆皇帝正想对洋人杀一儆百。他严厉申斥孙士毅,训令他“法在必惩,以示严肃”。这名英国炮手被处死之后,英国人再也没有向清政府交出过杀害中国人的英国凶手。
对于英国从大清国获得领事裁判权的过程,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是英国人凭借船坚炮利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事实上,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并没有提出领事裁判权要求,反倒是中方主动拱手相让。就在签订《南京条约》的三天以后,钦差大臣耆英等人向英国全权谈判代表璞鼎查(SirHenryPottinger)发出一份照会,提出《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需要解决的12个事项,其中包含了“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由内地惩办”的提议。英方正求之不得,正好写入了1843年签订的《虎门条约》。正是这一条款把领事裁判权赋予了英方。
安国胜先生在《西风落日》一书中还涉及到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例如,鸦片是不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是不是为利益而发动?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之间的分歧关键不在鸦片,而是在法律;有关法律的分歧关键不在鸦片,而是在英商的人身安全。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通过十三行责令洋商呈缴鸦片,洋商呈缴的鸦片数量令人震惊地超过了1千吨!但林则徐要求洋商按照指定的样式出具甘结(保证书),承诺永不贸易鸦片,“如经查出夹带,人即正法、货尽入官”,遭到英商拒绝。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回复林则徐说,不审判就判死刑,不符合英国法律,断然不能接受。他还带领英国商船退泊到九龙尖沙嘴一带。
不料英国水手在尖沙嘴斗殴,导致林维喜死亡。林则徐依照中国惯例,要求义律交出罪犯。具体是哪一个人无关紧要,但一定要有一个人定罪。义律无法满足林则徐的要求:他无法找出真凶,又不能抛弃英国侨民中的任何一个。林则徐把英国人赶出澳门的庇护所,英国侨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只好转移到停泊在香港的船上。林则徐使出最后一招:断绝新鲜食物和淡水,出动平地战船阻止装载食品的中国小船驶往英国船只。这导致冲突升级为战争的第一枪。
鸦片战争(以及领事裁判权)导致的结果复杂,全面的利益分析也很困难。从短期来看,与当时对林则徐的要求妥协的美国商人相比,直接对抗清政府的英商遭受了损失。
美国商人并不认同中国法律,但是他们并不像英国商人那样直接对抗。早在1784年的LadyHughes事件中,美国商船EmpressofChina的船员认为清朝当局逮捕英商大班的行为“是对人身自由犯下的罪行”,参与了在粤外商的武装游行示威。1821年,美国商船Emily号上的意大利籍水手FrancisTerranova投掷瓦罐,导致一名中国妇女死亡,被清朝官员判处死刑并处决。美国人当时的态度是:“我们认为案件是不公平的。我们在你们的水域,服从你们的法律,尽管它们是如此偏颇,我们也不作反抗。你们按照自己的法律观念,未经审判而定罪……”
美国商人的妥协行为在鸦片战争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短期回报,而英国商人不妥协的结果,使中英贸易中断,利益被美商夺去。在中英贸易中断之际,美国公司Russel&Co.的船只在香港和澳门之间贩运英国货,每吨收水脚30到40元;装载印度棉花,每包(336磅)收水脚7元。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价格:从伦敦到广州的水脚也不会超过55元。可见美商“趁火打劫”,获得暴利。
最具争议的问题有关领事裁判权对中国的影响。中外法律制度碰撞无疑是推进中国法律体制现代化的外部动力。对内部改革动力严重不足的大清帝国而言,外部动力尤其珍贵。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中华法律源远流长,但一直以来都是作为统治者治乱止争的工具,即“以法为器”。既然法是统治者手中之器,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防民治民,那么对于民众来说,法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既然民众避之唯恐不及,那么统治者就更加不受约束,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样的体制没有办法“自新”。
好问题总是很难得到好答案。《西风落日》一书虽然没有给出每一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凭借这本书提到的问题,以及书中提供的详尽而且可信的索引,它已经称得上一个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