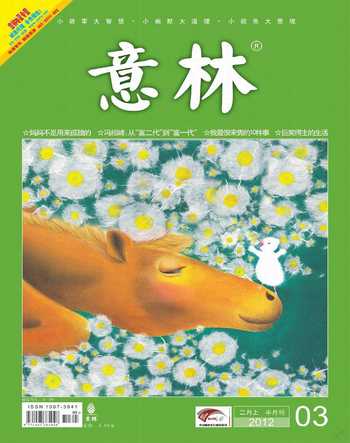被逼成“富人”
流沙
我的一颗牙出了问题,牙医的建议是:根管治疗、打桩、做烤瓷牙。在问到烤瓷牙价格时,牙医放下了笔,问:“你在哪个单位工作?”我如实以答。牙医又问我:“收入还好吧?”我又如实以答。
牙医听完,“发表”了讲话。她说,看来你是一个经常与人打交道的人,也算是有身份、有地位、有钱,你应该做一颗铬金镀边的烤瓷牙,这种牙特别真实,和真牙一模一样。我坐在牙医对面,听了云里雾里。但牙医的意思我是听明白了,如果我的口腔里不装上这种名叫铬金烤瓷牙,那么就与我的身份不匹配了。
拿着一张价值三千元的报价单从牙科诊所出来,开着车回家,我差一点儿迷醉。看哪,我在别人眼中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钱的人,我还开着有四个轮子的车,行走在纸醉金迷的城市里。
可我是有身份、有地位、有钱的人吗?我只是一个打工者,在生存的问题上,与民工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虽然有时候我会在许多场合说出许多漂亮的词汇,还写过几篇“城里人要关爱外来务工者”的文章。
但许多人不那么认为,而且还有许多人绝对不允许你做穷人,你的背后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推着你走,押着你走,你不走不行。我就这么犹犹豫豫,莫名其妙地成了“富人”,这叫“被富人”。
举例说明吧。几年前我从工厂里出来,换了一家单位。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它与我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是读高一时我姐花掉全部积蓄买给我的,价值二百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二百元,是个天文数字,几乎相当于现在的富裕家庭里购了一辆私家车,这车与我朝夕相处十多年。就是这辆极具纪念意义的车,却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让我决定换掉它。说来简单,在街头遇上原工厂里的领导,他看着我仍旧衣冠不整的样子,还是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就十分关切地问:“如果那边工资低,我看你还是回来吧。”这话在我脑里徘徊了多天,越想越不是味,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我一狠心,去买了一辆电瓶车。
我在城里买商品房也是偶然。前几年,我那些学友朋友一次次邀请我参观他们的新居,每一次参观,我都自惭形秽,这么大的房子,这么漂亮的装修,我根本没有能力做到。但他们哪管你的感受,说你怎么不买房啊,咱们圈子里的那些人,只有你没买房了,似乎我再不买新房,就融不进这个圈子了。于是我又越想越不是味,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我一狠心,按揭加举债,去买了一套商品房。
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被人“逼”成了在城里拥有两套房的“富人”。
现在轮到车的问题了。原先有辆价值两万多元的旧普桑,圈子里的人都建议我换车,至少得换个本田、丰田什么的,说开普桑太掉价了。
于是,我努力做一个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富人”。而且还在想着是不是把积蓄拿一点儿出来,买辆很有面子的车。
我本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很少会被别人所左右,但回过头去一看,太可笑了,也太可怕了。这个世界上的流行的“价值观”,像锈斑一样,腐蚀着你,即使你是一根坚硬的钢管,也经不住这种全方面的腐蚀,几年之后,你也会被腐蚀得千疮百孔。因为,你心中总是存在着一点点的虚荣心,一点点的争强斗胜心,它就像一个海妖,诱惑你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让你不可思议的地方。
做一个“富人”很快乐吗?我实在说不上来。我发现自己现在开上新车了,住上大套住房了,但这与快乐没有联系。我还是觉得十多年前,住着小套的住房,怡然而自得,每天骑着那辆自行車,头顶是暖暖的太阳,慢悠悠地行着,那样真的很快乐。
(培培摘自《潮州日报》2011年12月21日图/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