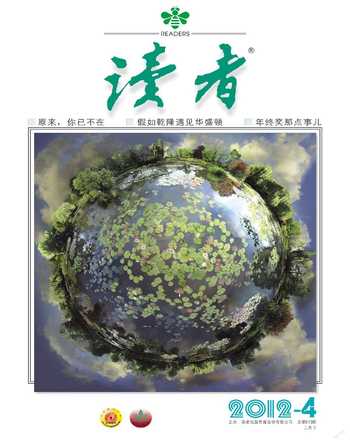我只有一束鲜花
张炜
“民兵”,这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两个字。我们全家人都在盯视之下,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事,连走路都轻轻的。父亲平时会被喊到离我们家五六里远的一个小村去做活,因为他没有资格在园艺场做工。父亲如果早一年回来,我上学的事肯定会化为泡影。
上学前,妈妈和外祖母一遍遍叮嘱我:“千万要听话啊——听各种人的话,无论是谁都不要招惹啊。”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是我必须记住的,即在外面千万不能提到父亲。就这样,我心里装着一大堆禁忌,战战兢兢背上了书包。
可能因为我太沉默了吧,从第一天开始,学校里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我每时每刻都是拘谨的,尽管我总是想办法掩饰。
从学校出来,一个人踏上那条灌木丛中的小路时,我才重新变成了自己。
值得庆幸的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同学和老师知道我们家的详细情况。但我想校长可能知道,因为他的镜片后面有一双好奇、诡秘的眼睛。我于是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着他。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校园里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孤单。我敢肯定,这个人大概也像我一样,暗暗压着一件可怕的心事。不仅在当时,以至于后来甚至一生,我都会从人群中发现那些真正的孤单者。
她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来这所学校已经一年多了,她与其他老师都不一样,我觉得她在用那温柔的眼睛抚慰着每一个同学,特别是当她的目光投向我的时候,目光中竟然没有歧视,也没有怜悯,而仅仅是一份温煦、一种滚烫的东西。
当时离学校十几里的地方有一处小煤矿,每到秋末全班同学就要去山上捡煤,以供冬天取暖用。因为雨水可以把泥中的煤块冲洗出来,所以越是下雨就越要爬到山上。大家都穿了雨衣,只有“黑子”几个故意不穿,故意溅上满身满脸的黑泥,像恶鬼一样吆吆喝喝。我好不容易才捡到的煤块,一转眼就被他们偷走了。有一次“黑子”走过来,狞笑着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猛地喊了一声父亲的名字。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脸。我吐出了流进口中的雨水,攥紧了拳头。“黑子”跳到一边,接着往前一拱,把我撞倒在斜坡上。坡很陡,我全力攀住一块石头。这时他们几个人一齐踢旁边盛煤的篮子,踢我的手。我和辛辛苦苦捡到的煤块一起,顺着陡坡一直滚落下去。
我的头上、手上乃至全身上下都被尖尖的石棱割破撞伤,雨衣被撕得稀烂。我满脸满身除了黑泥就是渗出的血,雨水又把血水涂开来……有几个同学吓坏了,他们一嚷,班主任老师也跑了过来。老师只听“黑子”他们几个说话,然后转脸向我怒吼。我什么也听不清,只任雨水抽打我的脸。
正在我发木的时候,有一只手扶住了我——是音乐老师!她不声不响地把我揽到一边,蹲下,用手绢擦去我身上、脸上的血迹,牵着我走开……
她领我直接去了场部医务室。我的伤口被药水洗过,又被包扎起来。场医与她说了什么,我都没有听清。离收工还有一段时间,她领我去了宿舍。
我平生第一次到老师的住处。天啊,原来是如此整洁的一间小屋,我大概再也看不到比这儿更干净的地方了。一张小床、一个书架,还有一张不大的办公桌。我特别注意到桌旁有一架手风琴。床上的被子叠得整齐极了,上面用白色的布罩罩住。屋里有阵阵香味儿——水瓶中插了一大束金黄色的花……
她让我把衣服上的泥浆洗掉、烘干,我只得在这儿耐心地等下去。天黑了,她打来饭让我一起吃。这是我所能记起的最好的一餐饭。我的目光长时间落在了那一大束花上……我想起我们家东篱下也有一丛金黄色的菊花。
第二天上学,我折下最大最好的几枝菊花,小心地藏在书包里。我比平时更早地来到了学校……她看到那一大束菊花,眼睛里立刻欢快地跳动了一下。
后来的日子,我就像有了一项新的任务:把带着露珠的鲜花折下来,用硬纸壳护住它们,这样装到书包里就不会弄坏。如果上课前没有找到老师,我就得小心地把花藏好。我看到她急匆匆往办公室走去了——她如果在课间休息时回宿舍就好了,那时我就可以把花交给她。我倚在门框上,咬着嘴唇等待。第一节课下课了,她没有返回,我只好等第二节课下课。我知道,我的老师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大蓬颤颤的、香气四溢的鲜花——比起我无尽的感激,这只是一份微薄的礼物。我一无所有,我只有一大束鲜花。
(聂勇摘自作家出版社《你在高原:鹿眼》一书,图选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外插图艺术大观》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