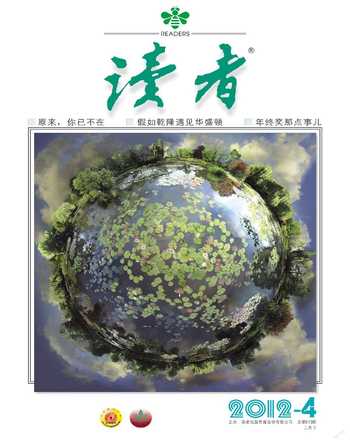生活的魅力:一团乱麻
于坚

去宋庄看方力钧的画,车间般巨大的画室里全是大亮蛋(光头)。他为什么不画头发呢?因为头发难画,每一根都是细节,直的或卷的、粗的或细的、长的或短的、白的或黑的……光头嘛,就是一个梨子似的圆,相对容易。方力钧自有寓意。
生活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团乱麻。
与西方祛魅后的契约社会不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是一团“道法自然”的乱麻史。中国人讲情理,情先理后;讲心安理得,心先理后。麻状,只要无违天地国亲师,怎么过都行,重要的是要“活泼泼”(王阳明语),不是住院部般的死寂、整饬。今日中国依然活泼泼的地方在乡村,城市基本上给城管搞得没有多少趣味了。因为城管不认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一种最人性的生活方式,他们想象中的宜居城市和住院部差不多。今日的中国城市,除了开车购物、开车上班,还有多少令人生活泼泼的功能呢?
中国不是西方那种逻辑社会,非理性的诗性很强大,实践理性也很强大。一阴一阳,有无相生,生生之谓易,以中为度,是为中国。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双在“道法自然”的哲学中生长了五千年的大脚,生活世界总是曲里拐弯,充满细节、血肉,一团团如乱麻。天人合一,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剪不断,理还乱,这正是中国生活的魅力所在。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方面也许很落后,但在诗歌、艺术、建筑、饮食、古玩、园林等更辽阔的生活世界方面则未必。例如,在是否宜居方面,与摩天大楼相比,苏州园林、四合院并不落后,而是更宜居;与以购物为唯一目的的超级市场比较,庙会、集市、卖花姑娘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更顺乎人情,可以巩固亲和,抵抗人生之孤独,预防铤而走险。
人类社会要有秩序,天地国亲师是必须的。道理固然要“理麻”,但也不是剃个光头那么简单。西方社会契约化的人际关系,固然钱粮两清,却也冰冷无情。如果用美国、新加坡等地的生活模式来摧毁中国传统的生活世界,将中国经验判决为脏、乱、差而一刀切断,结果只会更糟糕。
美国、新加坡的建筑格局,适合该地的生活经验。比如美国辽阔,适合发展汽车工业;新加坡逼仄,适合盖高楼,人少,适合罚款。我最近去了趟印度,以中国的标准,印度就是个巨大的城中村,但并不见得人家就活得惨兮兮的。印度人一边打着手机,无线电穿过宇宙的边缘去谈生意,一边为湿婆大神进香。印度人用加法,诸神都显着灵,一切欣欣向荣。
生活世界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现在,削足适履已经成了行政的家常便饭。一刀切省事,因地制宜比较麻烦。生活世界如果不像麻一样纷繁,那还是世界吗?整齐划一、一刀切成方阵的,那是军营,是士兵的生活,不是百姓的生活。以军事化的思维来管理生活世界已经成了许多行政部门的传统。一刀切只是纸上的一个文件,量化、百分之多少、一律、坚决……但一刀切下去的地方,永远不会像预想的那样就是蛋糕,这一刀下去,伸的伸、缩的缩,断的断、碎的碎,皮开肉绽,总是有无数生命在刀下惨叫。
这种一刀切的传统很可怕。反右时,规定每个单位的右派要占5%。有些单位一个右派也没发现,也要抓出5%。我有个朋友,开了家小书店。城市要绿化,规定必须完成一定的面积。他的书店位于两个建筑物之间,走三步就到头的一点空间,只有七八平方米,也要拆掉绿化。绿化自然是好事情,但什么地方该绿化,什么地方不该绿化,却不因地制宜。那么小的一块地方,是留下一个很有品位的小书店,还是不伦不类地只是为了敷衍指标而一刀切下去好呢?书店与绿化,难道不能共存?决不考虑。为了绿化,把街道上的小吃店、杂货铺、自行车棚、报刊亭……一律拆掉。最可恶的是,为了达到指标,树就种在人家门前,让人出门都要绕着走,因为不如此就完成不了百分之几的绿化面积,因为检查团只看得见街面。绿化指标是完成了,生活世界也完蛋了。没有吃早餐的小店,没有散步的地方,那绿化真是寒碜啊。
要理顺生活世界,只能因地制宜,而不能削足适履。这是一个常识。行政者中只要读过小学的就应该知道“削足适履”这个典故。善良者以为是文化水平的问题,其实是钱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世界应当是活泼泼的,而不是削足适履之后的惨痛。
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这才是世界,这才是中国世界。行政人员领薪水,就是该“理麻”的。剪不断,理还乱,世界因此微妙、美丽、活泼、生动、复杂。图省事,一刀剃成小平头,削成亮蛋,还要他们做什么?烫头发我不会,剃光头谁不会!
方力钧的那些大亮蛋,也可理解为对一刀切的反讽。
(初雪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日,刘 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