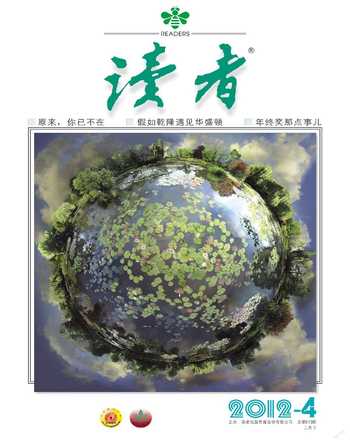胡凡小姐的故事
席慕蓉

小时候看童话书,最爱看的是这样的结尾:“于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了,他们住在美丽的城堡里,过着非常快乐的日子。”
把书合起来以后,小小的心灵觉得欣慰又满足,历尽了千辛万苦的情侣终于可以在一起,人世间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
等到长大了一点,对爱情的憧憬又不一样了:爱应该是不指望报偿的奉献,是长久的等待,是火车上费雯丽带着泪的送别,是春花树下李察·波顿越来越模糊的挥手特写。凄怨感人的故事赚了我满眶热泪,却让我有一种痛快的感觉,毕竟,悲剧中的美才是永恒而持久的。
可是,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又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在布鲁塞尔读书时住过好几个女生宿舍,其中有一间宿舍名叫“少女之家”。顾名思义,这里面住的应该都是年轻的女孩子。事实上,宿舍里最小的十六岁,大点的二十四岁,有一个住了十年的法兰西丝是例外。但是,她平日收拾得很漂亮,人也乐观和气,脸色红润,所以看起来仍然很年轻。
但有一个同伴与我们完全不一样。
其实,假如置身其外来看的话,她一点也不古怪,不过是个白头发的瘦老太太罢了。然而,在我们这些女孩子中间,她的面貌与举止就非常令人不舒服了。
胡凡小姐实在是个很奇怪的人。她并不住在宿舍,只是每天来吃三顿饭。她每天七点整一定来到饭厅了,穿着灰绿色的大学生式样的长大衣,终年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进门第一件事,便是伸出长而瘦的双手去摸窗边的暖气,一个一个窗户地摸过来。假如暖气开得够大,她就喜笑颜开,否则,她就会一直搓着手,然后到每一桌的前面来抱怨:
“你不觉得冷吗?”
“你不觉得这房间冷得像冰窖吗?”
问的时候,她那灰色的眼睛就直瞪着你,你如果不马上回答她,她就会一直瞪着你看。只有听到你表示同意的回答以后,她才会离开你。一面很满足地点头,一面开始解开围巾,脱下大衣,扯一下灰色毛衣的下襟,然后仔细地挑选一个她认为最温暖的角落坐下来。
于是,她这一天差不多都会固定在这个角落上了。平日我们上班、上学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待在冷清清的餐厅里,面前放一杯咖啡。偶尔,门房马格达会过来和她聊上几句,除此之外的多半时间,她都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
她叫得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很关心,也都想参与。我们唱情歌时,她也用沙哑的声音拔高了来跟着我们一起唱;我们买了新衣服时,她比谁都热心地先来评价一番;我们有谁的男朋友来了信或者来了电话时,她也总会头一个大呼小叫起来。
而青春有一种很冷酷的界限,自觉青春的少女们更有着一种很残忍的排他心理——觉得她嗓子太尖,觉得她头发太白,觉得她的话太无趣……于是,不管我们玩得有多高兴,一发现她加入,大家就都会无奈地停下来,然后冷漠地离开她。
有一天,我们正在谈论着男朋友和未婚夫之类的话题,她也在一旁竖着耳朵细听,从刚果来的安妮忽然对她蹦出一句话来:
“胡凡小姐,你有没有过未婚夫?”
“有过啊。”她很快地回答。
“别唬人!拿相片来看才信你。”安妮恶作剧似的笑起来。
头一次,胡凡小姐不跟着我们傻笑了,她装做没听见似的低头喝咖啡。马格达在门边狠狠地瞪了安妮一眼。我们觉得很无趣,就都站了起来,散了。
学校放暑假,大卫打电话来约我参加他和同学们的郊游,我兴高采烈地去了。我们在比利时东部的山区里消磨了一天。当我正想走上一条很狭窄的山径,单独去寻幽探胜的时候,彼得——大卫的一个比利时朋友叫住了我。
那位比利时朋友是山区里的居民,他告诉我山中多歧路,很容易迷途,尤其是在冬天,因为积雪很久都不化,更不易找路。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是风和日丽的夏日正午,地上开满了野花,鸟鸣带着怡人的尾音,美丽的森林安详宁静地包围着我们。
我实在不能想象这样美丽的森林还会有另外一副恐怖的面貌,有着狰狞的威胁,我也不愿想象。
回到宿舍时,已经很晚了。洗了澡换了睡衣,正想回房睡觉,走过法兰西丝的门前时,看见三四个女孩子正围坐在地板上闲聊。
“怎么还不睡?”
“进来坐,阿蓉。”
“嘿!阿蓉,今天玩得高兴吗?你们到哪里去了?”
法兰西丝一面问我,一面拍拍她身旁的空地。
我先报告了今天的行踪,她们马上就热热闹闹地谈起来了。
“嗨,说个秘密给你们听好吗?”法兰西丝忽然想起了什么来,“是关于胡凡小姐的。”
“好啊!”我们大家都要听,安妮又想到胡凡小姐的古怪模样,于是她站起来,伸出手在墙壁上乱摸,一面摸,一面问我们:
“你们觉得够暖吗?”
“你们不觉这房子冷吗?”
大家都嬉笑了起来,法兰西丝也笑了,招手把安妮叫了回来,然后用暂时的静默和逐渐转变的神色来向我们暗示,她要讲的不是个轻松的故事:
“你们别看胡凡小姐现在这个模样,她年轻时可是个出了名的美人哩!她的相片还上过报纸呢。
“当然,假如不是因为那件事,仅仅因为她长得美,记者是不会特意去报道的。实在是因为那件事情太惨了。
“大概在四十多年前,胡凡小姐十九岁的时候,和同村的一个男孩子订了婚。那个男孩子大学毕业,在镇上找到了工作。他们两家都住在阿蓉今天去过的那个山区里,两家的中间,隔着一片森林。假如天气好,路又熟的话,从这家走到那家不过三四十分钟的样子。
“他们订婚的那一天照了很多相片,在几天后的傍晚都冲洗出来了。男孩子从镇上下了班以后,就把这些相片都带回来了,他想马上就把相片拿去给胡凡小姐看。可是,那几天山区下雪,天又快黑了,男孩子的母亲用那地方乡下人惯有的顾忌劝阻她的孩子,她认为这不是个可以外出的晚上,尤其是到森林里去。
“可是,你们大概是知道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年轻人去会爱人的心的。男孩子虽然知道山区里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但是,他自恃身强体壮,又自信对这森林了如指掌,于是就兴冲冲地带着相片要去献给爱人了。
“他进了那片林子以后,母亲就开始担心。母亲整夜都无法合眼,天刚亮,就四处求人去帮她找孩子。
“孩子找到了,就在一片枯树林中,一条他们平时极少走的路上。怀中的相片上微笑的情侣再也无法相见了,相片却被记者拿去登在报上,赚了很多读者的眼泪。
“胡凡小姐就这样出了名。后来,她一个人离开了家,到布鲁塞尔来做事。她没读过什么书,只能在工厂里做工,或者在商店里做店员。就是在那个时候她认识了安丝玉小姐,就搬到我们这个宿舍来住了。可是,几年后她就离开宿舍,听说是去法国投靠她姐姐,之后的二十年没有一点音信。
“有一天,她又回到宿舍来了。她变得很苍老,而且没有职业,靠社会福利金过活。安丝玉小姐替她在附近找了间房子,每天三餐叫她来吃。就这样又过了十几年。”
法兰西丝说完了她的故事,我们都呆了。房间里很安静,伊素特——一个平日待人很好的比利时女孩子轻声地开口说话:
“我去过她家。有一次,她病了,好几天没来吃饭,我打听了地址去看她。她的房间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她好像很生气,不喜欢我去看她,一句话也不和我说。我只好赶快走掉。
“后来,安丝玉小姐去看她,大概给她请了医生。过了几天,她又回宿舍吃饭了,好像忘了跟我发过脾气,又对我有说有笑了。”
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不正是我最爱看的那一种吗?有着永恒美感的悲剧!假如搬上银幕,最后的镜头应该是一片白茫茫的森林,女主角孤单落寞的背影越来越远,美丽的长发随风飘起,悲怆的音乐紧扣住观众的心弦,剧终的字幕从下方慢慢升起,女主角一直往前走,没有再回过头来。可是,我看到的剧终,却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剧终虽然是真实的,却很难令人欣赏:一个古怪的白发老妇人,走在喧嚣狭窄的街市上,在她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自此以后,在胡凡小姐的面前,我再也不唱那首我一直很爱唱的法文歌了:
爱的欢乐,
只出现了一会儿,
爱的痛苦与悲哀啊,
却持续了整整的一生。
我们爱上某部电影,也许只是爱上了那部电影前的那个自己。
(生如夏花摘自南海出版社《槭树下的家》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