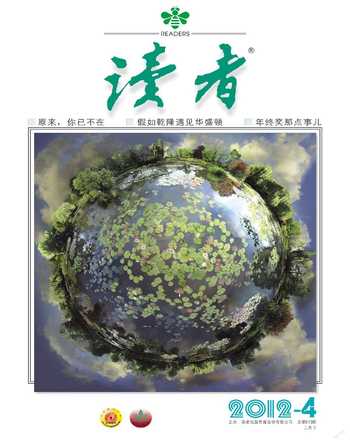原来,你已不在
〔日〕城山三郎

茫茫人海中,我只会对一个人用“喂”这样的称呼
原来,你已不在
云淡风轻,阳光灿烂,洒在海面上的光芒点缀了波浪,摇曳着,一片片金灿得耀眼。我独自走在细细软软的沙滩上,海浪顶着白色的浪头轻袭过来。这片沙滩,我和容子来过很多次。我走着,低头看见沙堆里有一块光亮的玻璃,于是蹲下来,轻轻地拾起它,然后举起来,透过它去看头顶的蓝天。
“啊,好漂亮啊!”
耳畔响起容子的声音:“是啊,的确很漂亮。”
我说:“喂,你看,那朵云真有意思,就好像在天空中飞翔的鸡蛋卷。喂——”没有声音回答我。
“喂——”
我回头叫容子。蓦然发现,身后还是那片寂寥的沙滩,还是那一次次涌上来的孤独的海浪,还是我一个人独自行走的足迹。低下头,我再次告诉自己:“原来,你已不在。”
没事的,有我
容子走了过来,停在了门口。夕阳照进房间,轻柔的风掀起窗帘。我转身看着她,容子也望着我,眼里闪动着泪光。我张开嘴,欲言又止。刚刚还在高声唱歌的她,终于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你啊……”我苦笑了一下,打破了沉重的空气,但是接下来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也哽咽了。我张开双臂,迎接着一头扑进我怀里的容子,紧紧地抱着她:“没事的,没事的,有我在你身边,没事的。”
也许怀抱是我能给她的唯一一点安慰,但是我口口声声说着的“没事”却是那么软弱无力。什么叫“没事”,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还那样不停地说着自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但是,那时那刻,我唯一能说出来的,也就只有这一句毫无意义的谎言了。
我轻轻地拍着容子抽搐着的脊背,让她在我怀里尽情地哭。容子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衬衫,渗到我的皮肤上,凉凉的。身为丈夫,面对哭泣的妻子,我的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无奈和无能为力。
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反复地问自己。我不能代替她生病,不能代替她痛苦,我能做的就只有这样——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给她一点点心灵上的依靠。在病魔面前,在生死面前,再伟大的人都只能俯首称臣,我渺小的力量又如何能撼动这摧毁性的悲哀呢?我抱着容子,同时也抱着我自己不知所措的心。
“没事的……”我继续机械地说着。
依旧是那最灿烂的阳光,它投射进来,用暖暖的光辉将我们这对无助的白发夫妻环绕在淡淡的金色中。从那一刻开始,容子一天天走向衰弱和死亡。她的生命就这样被突然宣判了,猝不及防。
回首,君已逝
看着挚爱的妻子即将离我而去,对我而言,是难以承受的痛苦。我们一起走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日子穷的时候她没有怨言,日子好时她也从不挑剔。容子是我的贤内助,生活中所有事情她都替我打点、为我准备,我从未担心过饮食起居。我们好不容易携手到白头,突然之间,永远的离别却摆在我们眼前。
面对生离死别,活着的人能做些什么呢?我该怎么做呢?守候在病床前,紧握着容子冰凉的手,我只能默默地祈祷,希望分别的时刻来得晚些,再晚些……
三个月过去了,容子并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离开,而是在病床上迎来了新的一年。不过容子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
容子不拒绝使用抗癌疫苗。我查到了一种疫苗的购买渠道,于是每周去一趟东京取药。独自坐在客车上,望着窗外的行人,我试着去想象每个人的生命旅程。出生,死亡,每个人都逃不出这个命运的循环。为了让容子能够多一线生的希望,我来回奔波着。这世上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有着自己一生珍爱的人,在最珍爱的人即将离去的时候,谁都会像我一样去极力挽留,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我每天去两次医院,从家或者工作室走过去,路上买些吃的。我和容子每天一起吃晚饭,我亲手把饭喂到她嘴里。我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着容子,吃完饭后就和她漫无边际地聊天。容子靠着窗台,我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和着温柔的光线,我们讲起很多往事:我们去旅游时发生的种种趣事,我专程去阿拉斯加待了一周也没看到极光的糗事……
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容子的笑声还是那么爽朗。容子性格开朗,喜欢和别人交流,聊天的同时会把自己的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不论走到哪里,只要容子是开心的,她周围的人也一定会跟着开心起来。护士小姐有时候也会加入我们的谈话中。她问我们一起旅游时会不会经常吵架——她跟她丈夫新婚旅行时就开始吵了。
于是,容子解释了一遍我们不吵架的原因:“到了观光地我们就各走各的,他喜欢逛名胜,而我特别喜欢逛商店、买特产,所以我们想吵也没机会吵啊。”
说到极光的事情时,护士小姐都在笑我:“先生您居然不知道白夜现象啊!”我一脸尴尬,笑得最开心的却是躺在病床上的容子。
容子住院那段时间,女儿纪子几乎天天都在医院照顾容子,经常陪容子聊天。一天,我还没走进病房就远远听到母女俩在笑。
一进门女儿就朝我坏笑着说:“爸爸,原来是这样的啊!”
“什么这样的?”我不解。
“我长这么大一直以为爸爸和妈妈是相亲认识然后结婚的呢!”
“哈哈,你猜错了吧?”容子接过话去,“我和你爸爸可真正是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
于是,我们又讲起在图书馆的相识,讲起那封坚决的绝交信,讲起我们奇迹般的重逢。
女儿嘲笑我:“看不出来啊,爸爸,你第一次见妈妈就上前搭讪啊?”
“哈哈,我那是真男人的行为,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
“哈哈哈哈……”我们都笑了起来,整个病房都被笑声点亮了。我们就这么回忆着过去的美好,谁都不愿去触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
好景不长,进入二月,容子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到了起不了床的程度。看着病床上痛苦的容子,我意识到任凭我有多么舍不得,任凭容子有多么不情愿,离别时刻还是要来了。
2000年2月24日,杉浦容子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我常常觉得,和容子的分别是那样突然。检查出身患肝癌后的第四个月,入院治疗的两个多月后,容子就永远地离开了。太突然,我甚至没有准备好该如何去面对。作为丈夫,我比容子年长四岁,从未想过容子会走在我前面。容子曾经答应过我,一定照顾我直到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因为没有她我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
“我知道啦,你走了以后我还要健健康康地活十几年呢!”容子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而如今她失约了,先走了,留下不知所措的我。
容子走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每次意识到她已经不在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家里每个角落都有她的身影——她在我面前打扫着,在我耳边说着话,一切都还那么清晰,仿佛就是上一秒钟的事情,可下一秒她却不在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容子走了七年了,可我依然无法适应没有她的日子。写关于她的故事时,我总会在不经意间叫她:“喂,容子,你还记得我们去那个地方旅游时你为了买便当没赶上火车吗?喂,喂……”抬头一看,空荡荡的房子,客厅、厨房……到处都是空的,只有我的回音。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又不得不再次提醒自己:“啊,原来你已经不在了……”我低头继续写作,过一会儿又会不自觉地叫:“喂,容子啊,帮我加点茶好吗?”
最后的日子
容子最后的那段日子,每天都要与病魔抗争,每天都要忍着疼痛接受治疗。因此那些日子就像一张张排列着的灰白卡片,但最后留下的画面却是一张耀眼的彩色明信片。
那一次,在纽约工作的儿子有一回来看望母亲。因为隔得太远,儿子担心一旦母亲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不能及时赶回来,所以他专门请了假,捧着一大束鲜花,回来看望母亲。当儿子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我打算把他送上出租车,于是也跟着起身了。
容子的目光跟随着我们,我们正要出门的时候,身后传来容子的声音——爽朗高亢的声音:“有一!”
我们回头,看见容子突然从床上支起身体,要下床,滑了一下,好不容易才站稳。更让我吃惊的是,紧接着,容子整理整理病服,朝儿子微笑着挺直腰背,敬了一个军礼,说:“一路顺风!”
瞬间,世界安静了,我们都怔住了。
容子那么精神抖擞地站着,背后是透过窗帘的暖暖阳光,她站在那里,闪着光芒。
看着母亲的笑靥,儿子也随即举起手来朝母亲回敬了一个军礼:“是!我出发了!”
空气凝固了一会儿,看着互相敬礼的母子俩,我哈哈地笑了起来,容子和儿子也都笑了。我们脸上都笑得那么开心,但是眼中却含着泪水,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是母亲跟儿子最后的道别。
身为小说家的我,见过也写过很多场面,但是容子最后一刻的爽朗是我没见过也写不出来的。她明明心里无限悲伤,脸上却还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后来儿子说,长时间的旅途中,他反反复复想起母亲最后的姿势和笑脸,忍着盈眶的眼泪,他一遍遍地举起右手行军礼:“是!我出发了……”
每次回忆起那一幕,我都说不出话来。不,是颤抖着泣不成声地默念:“这样一种最后的谢幕方式,对于给了我这么多年快乐的你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格兰·米勒的音乐再次响起,我恍惚回到了那个与容子重逢的夜晚。吊灯旋转着,洒下点点金黄色的光芒,酒意氤氲,音乐弥漫,我牵起容子的手走向舞池。
容子一袭白裙,配一双精致的白色高跟鞋。偌大的舞池只有我们两人,没有天花板,抬头便是皎洁的月亮。我们轻轻地迈着舞步,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容子低着头对我说。
“但是我一直相信我们还能再遇见。”
“呵呵,你真会哄女孩子,这么会说话。”容子以为我是在讨她欢心。
“不,我是说真的。”我肯定地说,语气坚定。容子停下了舞步,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
看着容子清澈的眼睛,我告诉她:“你知道吗,这是命中注定的。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一切都注定了。”
容子笑了:“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是我的守护天使。”
“守护天使?”
“你将一生守护我,让我幸福快乐。我们此生要彼此相依在一起,这是命中注定的。”
四目相对,容子看到了我的一颗真挚的心,她迎过来轻轻地抱着我。音乐继续,我们的舞步继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是我们一生的约定。
(青豆摘自古吴轩出版社《写给亡妻的情书:原来,你已不在》一书,图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黑白画创作形象图库》一书,岑圣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