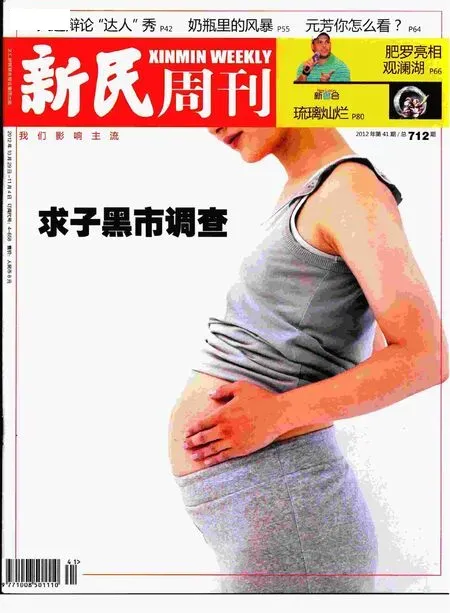12版安娜
马莅骊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然而,日光底下并无新事。就像使徒約翰说的,这世界上的事不过三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不幸的源头,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样事中找到。
除了那些道德立场极为鲜明的人,人们对于婚外恋的态度也在不断游走。我的一个朋友说,她在看97版电影的时候,万分扼腕安娜与沃洛斯基的爱情;而在历史上第12版《安娜·卡列尼娜》中,她对安娜的出轨和命运毫无同情。她的立场基于演员和表演,这是苏菲·玛索之于凯拉·奈特莉的胜利(可能还有12版中饰演卡列宁的裘德洛的推波助澜)。其实在公布演员表的那会儿,我就对凯拉十分存疑——这位惯演古装剧的美女,过于现代和硬朗;但没法子,谁让她是导演乔·怀特的最爱呢。几年前,在对《傲慢与偏见》二小姐的把握上,凯拉就显得咄咄逼人,好在青春靓丽帮了她很大的忙;而在这部戏中,安娜那种打动沃洛斯基(也可能是托翁本人)的害羞温柔气质荡然无存了。在后半段的歇斯底里中,我周围几个女观众毫不客气地骂着安娜“神经”和“活该”……
然而,要真正读懂安娜的故事必须回归到托尔斯泰的信仰。我觉得那些把离婚看成顺理成章、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现代人,是无法真正理解安娜的自杀的——他们或者会把安娜和沃洛斯基之间的感情,当作另一个波兰斯基“苦月亮”式的故事;不同的是,安娜身为已婚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家庭、地位、爱子……
今天,一个为爱出轨的安娜可能不会因此被逼入绝境,但背后隐藏的危机却是相同的。安娜的悲剧在于她孤注一掷地把爱情作为了上帝,当爱情退场时,安娜的世界也因此被颠覆了。所以,她最后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厌弃(“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以及无法面对上帝的愧疚(呼喊着“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这是安娜真正让人同情和怜恤的地方。
托尔斯泰的立场,其实体现在列文这个人物身上。电影里,导演只是在饭桌上让列文含混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肉体的情欲的不以为然,这很可能让人误会列文只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然而在小说里,拉图、斯宾诺莎、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完全不能给列文安慰。他没有安娜那样的经历,他是一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因为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最后他从一个农夫那里获得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为上帝而活。这是安娜在沃洛斯基的“爱情”里找不到的,不是沃洛斯基的爱不够深不够长,而是有罪有限的人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上帝。同样,卡列宁也无法靠着自己的理性和节制而成为上帝。我对于卡列宁的同情一点也不比对安娜的少,尤其在看到他努力地想要遵循圣经原则、去接纳背叛自己的妻子时。我们沉重的肉身总是在拖我们的后腿,或心甘情愿地受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诱引(好像安娜和沃洛斯基);或误以为我们可以凭借沉重的肉身得到上帝的嘉许,成为有道德感的人(好像卡列宁)。
这样一个富有神性的故事,是电影不能告诉我们的。所以在最后,当农夫反问列文你是凭着理性恋爱娶妻的吗,列文的恍然大悟会被人误解为对于情感的高举。但若此,我们又怎么去解释安娜的悲剧呢?十字架信仰早就沦落为基督教文化,所以我们会看到电影里极尽奢华又极为轻浮的舞台剧改编,看到裘德洛在一片风吹草低之中不知该摆出怎样的一副表情,看到编剧和导演最终没有让列文对妻子说出自己所领悟的——或许他们根本无法给予他可靠的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