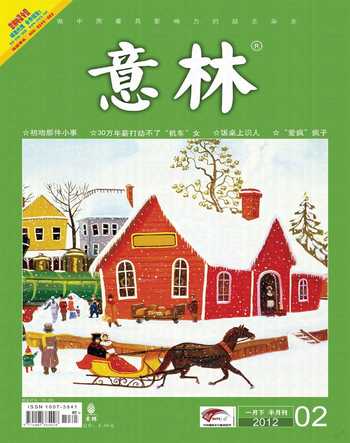顾城夫妇家的“战斗鸡”
顾城
壹
我十二岁离开北京时,自认读过两本书。一本是法布尔的《昆虫的故事》,另一本就是《养禽学》。我们的畜牧业可以从此开始。你想,且不说鸡生蛋、蛋生鸡的壮丽前景,仅鸡粪一项就蔚为大观——可育树,可卖,可产生沼气做饭、取暖……
说了半天,保守党谢烨终于投了赞成票,拿出了最后的钱。
四级投资:1.鸡和小鸡舍;2.大鸡舍和鸡运动场;3.实验鸡地(基地)包括鸡粪收集处理使用系统;4.沼气池。
先实践第一级投资。
钉子、树干、一堆废木板、一个旧窗子、锈铁皮,第一个小鸡舍在斜坡上站起来了,可以从后边拿蛋,不用进去踩鸡粪,撞脑袋。
鸡都装一个笼里运回来,一掀就跑了只黑鸡。我急忙和它比登山。
它穿梭自如时隐时现在黄玫瑰和斯里兰针叶中间,我则沿着棵歪树攀上一跳,跌进个藤草坑,还没站起,就听山下雷喊声异样,心中一喜:抓住了?急急滚跌下山,雷的第一句话就是:“鸡都跑了!”
天啊,怎么了?笼子开着,鸡正自由自在,一个个地穿草过木,捉虫采果。我一边撒米,一边绝望地咕咕叫着。
贰
雷去告诉卖鸡老太太鸡跑了。老太太说可在夜间上树抓——只要天一黑,鸡飞上树。
天色渐暗,鸡一个个飞起,隐进树盖。
天黑了,全黑了,我们死死地记住一只只鸡隐没的位置。
手慢慢地伸过去,慢,极慢,突然一个触觉,鸡大叫,吓死人了。谢烨也叫,低声叫:“抓住!”“快!”我把鸡放进网里,网被放进桶,桶给扣进大箱子。
真想不到,在树上抓鸡跟摘苹果一样,一只只抓,一只只大叫,蹲在边上的居然不逃。
两只黑鸡不在其中!早上黑鸡叫了,我们一齐跳起。鸡没走远,但也是只闻其声。
叁
下午五点半上山,谢烨先就等在那里了。我拿了渔网、渔叉,一路磕磕绊绊,一种缠不清的细草蔓老阴谋摔我跟头。正藏猫猫的谢烨见我就蹙眉:“这个放下,没用!”我放下了渔叉。“这个也没用!”我放下了渔网。
谢烨脸色好了:“你来,看——”她声音柔和极了。
我跟着她:“哪儿?”“那儿,那棵大树这边,再上边一点儿,大石头上边,往下看——”她索性转我的脑袋。
我这才看见,离我们约五十米的地方,有个红红的冠子。
那鸡真安静,在那发愣,听山谷里大树叶偶尔落下的声音,冠子红极了,我真没看过鸡那么美。还有另一只谢烨也看见了。
我们被这寂静震慑,退下来;过一会儿再去看看,好像舍不得多看。暮色渐临,那么明朗的云霎时暗了,一派金红,天蓝成墨绿,鸡被暮色搅动,渐渐不安起来,咕咕噜噜叫着,忽然飞上一棵倒树,向上走,又一飞。我说看不见了。真的,天暗得太快,老藤又缠满了树。但谢烨坚持说,她看得见,鸡已经上得很高了。
一阵晚风袭来,大树一阵叹息。我贴近树身听到潮水的声音。鸡低低地咕咕叫了,我才知道它就在附近。捉一只鸡,就像捉一条鱼,把网伸过去,慢得不能再慢,你判断不出距离。我觉到它在暗中不安,咕咕咕咕,于是一扣,网挂在树枝间,它冲下去,连飞带叫——我捉住了我没看见的另一只。
跟着的两个星期,谢烨一直失魂落魄,也顾不上娃娃哭不哭,一听鸡叫就冲出去。鸡也不曾走远,就在方圆一里的山坡山坳间漫游,在倒树里挖虫子,落叶中寻蚯蚓,还有一种叫声是很清楚的——“那只鸡在下蛋!”谢烨不无伤感地说。她每天不远不近地“跟踪追鸡”几小时。
后来我开山扩建鸡舍,在一块大石头下发现了这只鸡用自己的软毛铺成的舒适空间,和十几枚坏了的蛋。可惜那时它已经被我们吃掉好几个月了。
(黄小美摘自《树枝的疏忽》江苏文艺出版社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