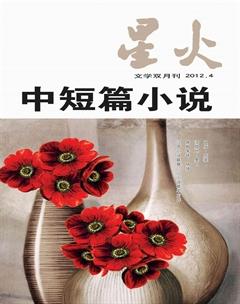等火车
谢方儿
我们家的事,我要从三年前的一个下午说起。那个下午,和我记忆中的所有下午截然不同。焦益生刚刚爬上火车,突然又跳下火车跑过来,当时,母亲张有根抱着胖乎乎的焦地,身子却斜靠在我身上,就像把我当成了一棵大树。其实我才八岁,身体瘦弱得像一根豆芽。焦益生沐浴着午后灿烂的阳光冲上前,把焦地从张有根怀里像萝卜一样拔了出来。焦益生二话没说,在焦地粉嫩的脸上又啃又舔,像津津有味地吮吸着一块奶油雪糕。母亲闷声闷气地啊了几声,她的身子失去了重心,差点把我压断了。
这个时候,父亲抬起了头,我发现他的脸上湿了,焦地的粉脸也湿了。父亲朝我招招手说,焦天,你过来。我象征性地动了动脚,焦益生抱着焦地弯下腰,亲了亲我的脸蛋说,焦天,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我的脸上湿冷了一下,我想都没想就躲开了。我觉得父亲的身体里正在冒一种气味,这种古怪的气味充塞了我的胸膛。
这句话他在上火车前说了很多次,我已经听得没有感觉了,仿佛不是我爸爸在说话。父亲抬起头用手揩揩脸又说,焦天,爸爸要对你说,我挣了钱就回来,供你读书,将来送你上大学。我说,我不要上大学,我要爸爸。父亲愣了一下,然后摸了摸我不大规整的头皮,我发觉他的手像死人一样冰冷。母亲依然没有说话,她又啊啊了几声,身体也恰到好处地颤抖起来了。父亲把焦地扔进母亲怀里,说你是哑巴呀!说完他就昂首阔步地爬上即将启动的火车。
父亲上火车的形象,很像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火车慢慢爬动了,某一个车窗中露出了父亲的头,他的表情庄重得像粘贴在玻璃上的一张画像。母亲突然老鹰抓小鸡一样抓起我就跑,她边跑边说,焦天,焦天你快和爸爸说再见。我刚想对贴在车窗玻璃上的人头喊爸爸,火车突然吼起来,这种熟悉的吼声,铺天盖地湮没了空气中所有来回奔跑的声音。我们的家就在铁道的边上,火车的这种尖叫和飞奔而过的咔嗒声,我熟悉得像焦地的哭声。载着父亲的火车很快消失了,铁轨空荡荡地伸向远方。张有根拉着我停下来喘气,后来她哭了起来,再后来她对我说,焦天,我们回家吧!
父亲离开家后,我的生活改变了。虽然有时候我会想到他,但我想不起他在上火车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的日子比以前自由快乐多了。我放学扔下书包,悄悄带着黑美去铁道边玩耍,黑美是我们家养的一条黑母狗,它是父亲带回家养大的,可它对父亲的离开一点也不在乎。当然,黑美曾经也多次报答过父亲,有几次我亲眼看到黑美叼着鸭子回家。有鸭子吃的晚上,我们吃鸭肉,黑美吃鸭骨头,人和狗都吃得啪嗒啪嗒地响。后来就不一样了,至少我从此不想吃鸭肉了。那天我放学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门口哭,她哭着哭着就坐到地上大把大把拧起了鼻涕,我听别人说,老太太家里的一只鸭子找不到了。这个晚上,我们家吃鸭子的时候我没有吃。父亲笑着对我说,鸭子是买来的。我在心里骂,焦益生,你这个坏蛋!后来,我想我教育不了父亲,教育黑美总是可以的。我打了几次黑美,我是拿着木棒打的,从此它就不再咬鸭子了。
一列火车隆隆开过来,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会触景生情,想到坐火车去远方的父亲,而且他上火车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也想起来了。想起父亲对我说的话,我的心里很难受,要我具体说出来,想多久也说不出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不是一个想读书的孩子,所以无论父亲有多少钱我都不想上大学。
我的弟弟焦地虽然只有四岁,但父亲离开家后,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每天夜里都要哭闹,有时候他的哭闹声和火车的吼叫差不多。夜里,母亲会很有耐心地哄逗焦地,而且还会唱儿歌给他听,可焦地仍然哭闹,有时接不上了,他的喉咙咔咔地响,像要断气一样。日子一长,我听得烦了,经常跑到焦地面前装出一脸的狰狞怪相,弄得我们的家里经常像鬼哭狼嚎。母亲当然比我更加烦躁,在我脑袋上狠狠地敲,我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抱住脑袋大喊,你为什么不打焦地?
接下来的日子里,焦地还在一如既往地哭闹,以前他哭闹我都没留意他在喊叫什么。这天夜里,我觉得他在哭着喊爸爸,我从床上跳起来说,妈妈,焦地在喊爸爸!母亲听了听说,焦地真在喊爸爸。母亲抱起焦地说,焦地,你别哭了,我叫焦天去铁道边等火车。焦地居然马上破涕为笑,他还看着我拍拍小手说,我要爸爸。母亲使个眼色说,焦天,你去等火车吧,看看你爸爸有没有回来?说到等火车,我又想起了父亲在上火车前对我说的话,焦天,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现在母亲说了这个话,所以我只好揉着眼睛走出门。
屋外漆黑一片,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黑美听到我的声音从狗窝里跑出来,摇头晃尾地希望我带它去玩耍。我轻轻踢了踢黑美说,你去等火车吧!黑美逃开转个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当然没有去铁道边等火车,我站在门外等时间。一列夜火车开来了,隆隆响过后,我进屋,焦地已经安静地躺在床上,母亲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她朝我指指我睡的小床,暗示我赶紧睡吧。
我还没爬上床,焦地突然坐起来看着我,他发现我的身后没有父亲,结果他的哭闹声在一秒钟之内就达到了嘹亮的程度。黑美在門外也叫了起来,人和狗的声音在黑暗中此起彼伏,搞得我们的夜晚心烦意乱。母亲举起手说,焦地,你再哭,我要打了。这种威胁对焦地不起任何作用,他反而哭得更加起劲了。母亲当然舍不得打焦地,她抱起焦地说,焦地,别哭了,我叫焦天去铁道边等火车吧。焦地一听,像吃到了解药,立即只流鼻涕没有哭声了。
我要听妈妈的话,我再次走出门去。黑美兴高采烈地跑过来想舔我的手,我顺手打了它一巴掌。黑美以前被我打慌了,忍气吞声地逃回狗窝。我想,焦地再哭闹,我也给他一巴掌。秋风不动声色地吹过来,我的身子上起了一层冷冷的疙瘩。母亲没有来叫我回去,铁轨上也没有火车开过,夜风吹得我家的破窗户啪嗒啪嗒地响。我悄悄在狗窝边撒了一泡憋急的尿,然后一身轻松悄悄走进房间,母亲张着嘴巴已经睡着了,她的喉咙里呼嘟呼嘟响着,像有一个个气泡在喉咙里奔跑。可焦地还坐在床上,他不知疲倦地玩着一只又旧又脏的黑绒狗,他的鼻涕一直挂到被子上,在鼻息的吹动下像玩具一样软软地左右摇晃。
焦地抬头看到了我,他扔掉手中的黑绒狗放声大哭,好像我不是他的哥哥,而是一个突然闯进门的鬼怪。母亲惊醒了,她刚刚坐起来,我奋不顾身冲上前给了焦地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不偏不倚,准确地打在焦地像喇叭一样在哇哇响的嘴巴上。焦地的哭喊声停止了,但他的脸色发白了。母亲惊叫一声跳起来,一手扭住我的衣服,一手啪啪给了我两巴掌。从这以后,我不叫她妈妈,我叫她张有根。我的脸上胀膨膨了,然后热辣辣的疼。其实,我并不怨张有根打我,只要焦地不再哭闹了,再打我几巴掌我也愿意。问题是,焦地又哭闹了,而且比以前更上一层楼,他不光是哭喊流鼻涕,开始边哭闹边从棉被里爬出来翻滚,像个肉陀螺。
这种日子当然不可能长久,有一天夜里,张有根终于抡起巴掌打到了焦地的嘴上,打一下安静几分钟,然后焦地继续哭闹。我觉得焦地一定是想爸爸了,想起来,父亲自从那天坐火车走后,快有一年了。我第一次问母亲,爸爸他什么时候回来?张有根看着我,后来眼睛红了,再后来她居然也放声大哭起来。张有根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她的哭声告诉我,她也想父亲了。我们家里哭声一片,大人小孩都在哭,像死了一大堆亲人似的。
每天晚上焦地先哭闹,然后张有根抱住焦地一起哭。这种烦恼的现状,最后发展到只要我一离开家,焦地马上就不哭了。这里是我的家,我不可能每天夜里都站在外面过夜。对焦地的愤怒开始在我心里疯长,有好几个夜晚,我都在考虑如何掐死他。就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张有根悄悄对我说,焦天,你睡到外间去,我对你弟弟说,你等火车去了。好不好?张有根的英明决策化解了我堆积在心里的愤怒,自从我搬到外间后,焦地真的睡得安稳了。不过,每天夜里张有根都要说,焦天,你去铁道边等火车吧。我知道这是张有根的一种暗示,她要我早点去睡觉了。我说,知道了。然后,我还会对焦地说,焦地,我去等火车去了。
开始的几个夜晚,我在外间的小床上能听到张有根的呼噜声,还有焦地玩黑绒狗的咿呀声。后来,除了张有根的呼噜声,又响起了焦地喃喃喊爸爸的声音。我们确实有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了,这个外出挣钱的男人什么时候回来呢?自由自在带给我的快乐远不如以前了,现在我经常会带着黑美到铁道边等火车,每看到一列火车飞奔而来,我就会想起带走父亲的那列火车,我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等火车,并且希望有一天父亲能坐火车回家。我坐在铁道边,看到有火车缓缓开过来,像要停下来了,我的眼前闪亮了一下,看到父亲跳下了火车,我跑上去大声喊爸爸,我记不起有多长时间没有这么心向往之地叫爸爸了。可惜,这都是我坐在铁道边产生的幻觉。
张有根的心情开始有了变化,她经常会小题大做地打我,喋喋不休地骂焦地,更可怕的是,一到夜里就呜啊呜啊地哭,仿佛我们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哭。我问她,妈妈,你想爸爸了?张有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告诉我,天呐,啊啊,四只脚的畜生好管,两只脚的人难管。我不知道张有根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她现在一定把父亲当成了畜生。夜深人静时,张有根还在缠绵悱恻地哭泣,天呐,啊!我叫天——天不应;我叫地——地不灵。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呀。
对张有根的这种心情,我多数时候缺少同情。某一天下午放学回家,我像以前的下午一样准备带黑美去铁道边等火车,可找遍屋里屋外也没有黑美的影子。这个时候,张有根正在痛骂焦地,听起来她不像在骂自己的儿子,像在骂一个该死的坏人。焦地坐在地上像个聋子,他对母亲的臭骂无动于衷,埋头专心地玩着一堆零碎的旧积木。
我小心谨慎地从屋子里跑出来,很快在一个废弃的园子里找到了黑美。黑美和一条健壮的大黄狗在一起,其实他们正在进行甜蜜的爱情。大黄狗骑在黑美的屁股上,旁若无人地享受着狗幸福。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两条狗的这种场景,我的感觉是黑美被大黄狗欺负了,在惊惶失措之中,我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赶紧回家向张有根求教!我上气不接下气跑回家说,妈妈,快快,我们家的黑美被一条大黄狗咬住了。张有根扔下手里的大白菜说,在哪里?我說,在我家边上的一个破园子里。张有根操起一支木棒说,焦天,快带我去看看。
我带着母亲跑出家门,焦地从地上爬起来跟了出来,他边跑边带着哭腔喊,我要——爸爸,爸爸!焦地一定以为是父亲回来了。我们来到这个废弃的园子,发现黑美和大黄狗还像原来的形式在一起。我说,妈,你看,他们还在这里。张有根拿着木棒突然呼吸异样起来,脸色也换成了暗红,眼神中有了一层层跳动的闪亮。
我拉拉她的手焦急地说,妈,你快救救黑美吧!我感觉到张有根的手在颤抖,手心涌起一层湿热的汗气,她突然撒开我的手尖叫一声,畜生,我打死你!我惊慌地向后退了几步,张有根举起手里的木棒冲上去,对准大黄狗的后背“嘭嘭”打了下去。大黄狗悲痛欲绝地尖叫一声,然后倒在地上翻了几个沉重的滚,站起来时摇摇晃晃,像个快要死去的病人。在大黄狗下面的黑美估计也感受到了棒打的威猛,惊惶失措地站在原地发呆。张有根继续抡起木棒朝大黄狗痛打,大黄狗的爱情遭受到灭顶之灾,它放下一条公狗的尊严忍痛逃蹿。张有根一边追一边高喊,打死你,你这条公狗,我一定要打死你!
张有根当然追不上大黄狗,她发现黑美跟了上来,尽管黑美的眼神中流露出幸福的歉意,但张有根还是毫不留情地给了它一顿棒打。黑美呜呜叫着朝大黄狗的方向跑掉了,张有根挥舞着木棒大声咒骂,黑美,你这个烂货,下流的母狗,我也要打死你!我想不到张有根会发这么大的火,她简直是发疯了,大黄狗是应该打的,她为什么还要打自己家的黑美。当然,这个时候,我绝对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很怕她会把我也当成狗打,我相信她会这么做的。
我们眼前的狗都逃走了,她只看到像木头一样的我,她说,焦天,你过来。我的脚动了动,但我的身子不敢动。张有根举起木棒又说,焦天,你耳朵聋了?我想我要倒霉了,看张有根现在的气势,我会受到狗一样的待遇。这个时候,我和张有根都听到了焦地痛苦的惨叫,我们同时惊慌起来,拔脚就往焦地的哭喊声跑过去。
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焦地坐在一摊烂泥上绝望地哭喊,张有根跑上前大声说,焦地,你哭丧呀!焦地坐在地上一脸的眼泪鼻涕,张开挂满口水的嘴巴嚎叫。我突然看到焦地的小腿上流出了鲜血,鲜血已经慢慢流成了一朵红彤彤的小花 。我说,妈,焦地腿有血。张有根扔掉手里木棒,先给了我一巴掌说,你看到了为什么不早说?她抱起焦地看了看,发现焦地的小腿上一块皮肉破了,鲜血还在往外兴奋地流淌。我惊叫一声说,妈妈,这是狗咬的!张有根顺手又给了我一巴掌说,可恶狗,你快去给我打死它。
短时间接连挨了两巴掌,我有些晕头转向。我说,找大黄狗还是找黑美?焦地边哭边说,啊啊,疼呀,黑美咬我,打死它。我觉得一定是焦地看错了,黑美怎么可能会咬焦地呢,除非它不想回来了。张有根抱起焦地往家里走,我跟了几步不敢再跟了,因为我要去找咬焦地的狗。张有根走远了,但我能听到她和焦地的哭声都很悲伤而响亮。我不知道我到哪里去找狗,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父亲,如果这个男人在家里,我们就不可能发生这些事,而且我也不会接二连三被挨巴掌。我的心一下子冷了起来,眼泪突然流成了两条线。
我边哭边奔跑到铁道边,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暗红的阳光把铁轨照得像两条望不到头的粗红肠,我咽着一波又一波的口水,坐在铁道边等火车等父亲回家。这个时候,我是多么想看到父亲手里拿着香喷喷的红肠回家。突然,我看到铁轨的那一边蹲着一条黑狗,这不是我家的黑美吗?我跳起来挥手高喊,黑美——黑美——你快回来吧。但黑美冷漠地蹲着没有一点反应,看上去像一条石雕的狗。我想翻过铁轨去,但一列火车开了过来,等火车远去后,我的眼前没有黑美了。
天色朦胧时,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家,走到家门口,我发现家里安静得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张有根的身影在灶间晃动,估计在做菜烧饭了。焦地的小腿上缠绕着白纱布,他还是坐在地上埋头玩那堆零碎的旧积木,嘴里则含着一支丰满的棒棒糖,嘴角流淌着粘柔的口水和糖水。我怀着惊异走进家,焦地兴奋地拔出嘴里的棒棒糖说,哥哥,你看糖,我吃的。说完他赶紧把棒棒糖又塞进嘴里,还朝我心满意足地笑了笑。
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张有根的身边站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叫洪水,早几年我就认识了,张有根一直要我叫他洪叔叔。洪水是镇上开小超市的。以前,父亲还在家的时候,张有根带我去过洪水的小超市。洪水见到我就像见到了他的亲儿子,他每次都要兴奋地摸着我的头皮说,啊,焦天,你看你又长高了。然后,洪水会把酸奶、棒棒糖、饼干、水果什么的都往我手上塞。我的手很小,洪水给我的东西很多,我的脚下就会掉落许多东西,洪水笑着蹲下来拣起又往我的手上塞,但最后我的手里还是只有那么几样小东西。
张有根笑着说,洪水,你傻呀,焦天的手怎么拿得住这么许多东西,你去拿只塑料袋呀。从此,我去洪水的小超市都能拿到一塑料袋的东西,当然都是吃的。自从父亲离开家后,张有根没有带我去过洪水的小超市,但有时候我放学回家,会发现家里多了一只装着酸奶、棒棒糖、饼干什么的塑料袋,张有根不会说明这袋东西的来历,但我一看就知道,这一定是洪水送来的。
说真的,我不喜欢洪水,说得具体点就是我不喜欢长在他身体上的这张脸,因为他的脸从哪个角度看我都觉得像一张狗的脸,其实我喜欢狗的脸长得像人的脸,这样狗也会像人一样笑了。当然,尽管我不喜欢洪水的脸,但是他送给我的东西我都喜欢的。
张有根正和洪水有说有笑,我在家里已经听熟了哭声,听到笑声我居然愣住了。张有根抬头看到了我,说,焦天,你去干什么了?快过来叫洪叔叔。我觉得现在的洪水比以前英俊了,他的络腮胡子刮干净了,脸也胖乎乎。我轻轻地说,洪叔叔好。洪水红光满面地摸住我的头皮说,啊,焦天,你看你又长高了。我觉得他的手很暖和,他摸了一会儿又说,焦天,来来,你看洪叔叔给你带来了什么?洪水不知从哪儿拎出两大塑料袋的东西,我看到两只塑料袋都饱满得像一身肥胖的妇人。
张有根说,焦天,今天全靠洪叔叔了,他帮我一起去卫生院给焦地打针包扎。洪水又从衣袋里摸出两支棒棒糖说,焦天,给你两支棒棒糖,焦地只有一支的。张有根说,焦天,你怎么成了哑巴,快请洪叔叔坐下来吃饭吧。洪水在我家里吃张有根做的晚饭,我和焦地都匆匆吃完了。焦地扔下饭碗就像醉汉一样扑向那两只塑料袋,我赶緊追上去护住袋子说,焦地,洪叔叔给我的东西你不能动。焦地一把抓住塑料袋说,我要——我要吃酸奶。张有根笑着说,焦天,你是哥哥,给焦地一盒酸奶,你也拿一盒,带弟弟去外面玩玩吧。我觉得今天张有根的笑脸很好看,而且她对我们的淘气也表现出了极好的耐心。我想,带焦地去外面也好,省得他盯着我的塑料袋没完没了。
这个时候,洪水还在喝酒,他喷着酒气说,焦天,带好弟弟,当心恶狗咬哦!我们刚刚走出门,张有根就把门关上了,我们走了几步,焦地一屁股坐在地上说,脚痛,我不走了。我把焦地背起来说,我背你,我们到铁道边去找黑美吧。焦地的小手在我的后脑勺上敲了一下说,不,我要你到铁道边等火车。我说,好好,我们等火车去。可是,我背着焦地才走了几步,焦地扔掉手里的酸奶空盒子大声说,焦天,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吃饼干。我没理睬他继续朝铁道方向走,焦地的屁股在我的背上转动起来,他开始大声哭喊,我要——我要爸爸!我背不住焦地了,他转动屁股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他的重量,我赶紧背着焦地跑回家。
酒杯和饭碗都在饭桌上,但两个人不见了。我放下焦地喊了几声妈妈,张有根从房间里走出来说,焦天,你没有带焦地去玩?她的脸红红的,边说边拉着身上的衣服。我说,焦地喊脚痛,是他不想去了。洪水也从房间走出来,他走到饭桌旁坐下喝一口酒说,我明天再带焦地去换药。洪水像在自言自语,然后很快吃完了,他站走来摸住我的头说,焦天,我走了,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洪水消失在黑暗中,我想洪水说的话怎么会和父亲说的一样。这个晚上,张有根和焦地睡得很踏实,他们先是呼呼沉睡着,然后咿咿呀呀地各自说想说的一大堆梦话。前半夜我一直在想洪水说的话,后半夜我也做梦了,我梦到自己在铁道边等火车,但我的梦中居然没有等到一列火车。
接下来的几天,洪水几乎天天傍晚来我家,他抱着焦地去卫生院打针换药,然后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洪水走的时候,依然会摸着我的头说,焦天,我走了,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他不摸住我的头,估计就说不出这个话来的。有一天,他又同样摸着我的头说这个话,我说,洪叔叔,你别说了,你说的话,我爸爸早就说过了。我头上的这只手颤抖了几下,然后像一片枯叶从我的头顶上滑落。洪水走后,张有根阴沉着脸说,焦天,你真没礼貌,啊,你这个孩子,我管不了你了。
第二天,洪水又来了,他对我说,焦天,焦地的伤快好了,明天开始我要忙自己的活去了。我觉得洪水很好笑,他来不来和我有什么关系。晚饭我们又坐在一起吃,有了洪水坐在我们中间,我们的这个家看上去确实像个完整的家了。我看到洪水快吃完了,赶紧站起来说,妈妈,我出去玩了。焦地拉住我说,哥哥,我也要去,我要去等火车。其实,我是不想洪水摸着我的头皮说父亲说过的话,我不想听一个外人对我说父亲说过的话。洪水站起来走上前,又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说,焦天,我要走了,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我忍不住说,哎呀,我肚子疼了。说完我奔跑着冲出家门,我听到焦地带着哭腔在尖叫,我要——我要爸爸——
我跑到铁道边发呆,我希望看到黑美,它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甚至想到,黑美是不是去找父亲了?我没有等到火车,也没有看到黑美,但我惊讶地发现洪水在我面前了。洪水坐到一块石头上,在我的对面,他点上一支烟说,焦天,你生我的气了?我说,没有。洪水说,你不想见到我?我说,不,我只是不想听你说我爸爸說过的话。洪水的目光投向远方说,哦。焦天,你想爸爸了?我不想回答他的问题,我站起来说,我等火车。洪水也站起来说,火车是不能随便停靠的,火车要进了站才能下客。洪水的手抬了抬,又想摸我的头。我拔腿就跑,边跑边说我回去了。我跑到一个转弯路口,忍不住回头望去,看到洪水静静地站在原地望着我。
后来,洪水不来了,张有根脸上的笑容也暗淡了。这天,张有根突然问我,我们家的黑美呢?我想笑,看到张有根的脸色像一块生铁,低下头说,黑美不是被你打跑了吗?张有根想了想说,天呐,被我打跑了?狗是打跑的,焦益生怎么也跑掉了,这个畜生!我讨好地说,妈妈,我去找黑美吧。焦地走过来说,黑美咬我,我要打它。焦地扔出一块旧积木,正好打在我的头上,疼得我流下了眼泪。我趁张有根没注意,在焦地的胳膊上拧了一把,焦地立即大声哭泣,我要爸爸!张有根大声说,啊,天呐,吵死了吵死了。焦天,焦地,你们是虫,和你们的爸爸父亲一样都是虫。
焦地昂起挂满眼泪鼻涕的头,像一只报晓的公鸡不停地叫。我拉住焦地被我拧过的胳膊说,焦地,我们等火车去。焦地马上又破涕为笑了,他拉住我的手说,我们走吧。我带着焦地在铁道边走了一圈,看到一列火车隆隆飞奔而来,我贴着焦地的耳朵大声喊,焦地,火车来了,快喊爸爸,喊焦益生!我们趴在铁道的路基下齐声高呼,爸爸——爸爸——父亲——
飞奔的火车让我们头晕目眩,我们不停地叫喊着。火车远去了,我拉着焦地站起来,焦地一阵东张西望后说,爸爸呢?我说,爸爸一定回家了。焦地一听,摇摇晃晃像一只企鹅奔跑起来。张有根看到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说,焦天,找到黑美了?我说,没有。焦地说,妈妈,爸爸呢?张有根说,他死了。焦天,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等火车了。我想张有根在骗我们,父亲不会死的,因为他离开我们的时候胡子还没有白,而且现在也不会白的。过了些日子,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我坐在铁道边开始会想到,父亲是不是真的死了?我的心里有了反复的悲伤,这种悲伤开始陪伴着我的日日夜夜。
责编:朱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