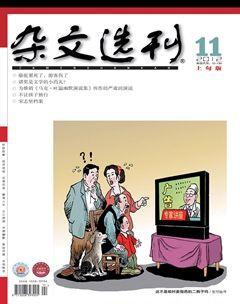信任危机
张恒
没人喜欢去医院,孩子的父母更是如此。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总杨樾却不得不去,因为女儿又是发烧,又是呕吐。他带着女儿去了全国闻名的北京儿童医院,结果医生怀疑是急性脑膜炎,让他先带孩子做腰穿刺和脑部CT。他心存疑虑,又带着孩子去了协和医院,大夫只是诊断为感冒。后来孩子的体温真的就降下来了,“迫不及待地要下床淘气了”。
杨樾把这件事情发到微博上,结果引来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普通网友以结果为依据,认为儿童医院的医生过度医疗。“面对同一个患者,不同医生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诊治。不同的诊治手段,结果可能一样。”北京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医生的看法。有医生在杨樾的微博下留言:如果孩子真是脑膜炎,怎么办?
仔细梳理双方的争论,不由得让你慨叹,医患之间的信任感,怎么就脆弱到这种程度?批评、指责甚至是谩骂医生无德的人,一旦生病,却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自己不信任的人;而给病人看病的大夫,心里卻不断地打着鼓:万一出现意外,自己的病人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医闹求偿算是轻的,近几年恶性刺医事件也时有发生。所以即便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他们也要患者去检查核实。
两个没有安全感的群体就这样被捆绑在一起:患者提到医院就头皮发麻,挂号困难,求医难见。终于见到医生,又在担心,医生是否能尽责,是否会通过过度医疗掏空自己本已干瘪的钱囊。除了看病难、看病贵,还有潜在的医疗事故——这是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他们满心希望却又战战兢兢。
对医生来说,看病已经不单纯是看病,更像是一道选择题:要么穷尽一切手段,将患者治愈;要么将为医院带来无尽的麻烦和高额的赔偿,甚至是自己受到生命威胁。
除了高风险,他们的工作强度也极大,而收入则严重不成比例。结果是,医生越紧缺,想做医生的人却越少,好医生则更少。前两天媒体报道,国家每年培养的六十万医科毕业生,竟然只有十多万人成为了医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经告诉世人一个观点,我们把生命托付给医生。我们不会把这种信心赋予吝啬或处境糟糕的人。医生的收入应该高到这种高度:使他们拥有一个体面的、值得信任的社会地位。而加上他们从业所需教育耗费的巨额金钱和时间,必然推高了提供服务的价格。
之前我们更多强调,加大对病患者的医疗保障的投入,但其实,对医生的保障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建设。
就在医患相煎,甚至恶性事件不断的节点上,一座由深圳市投资三十五亿元成立的深圳香港合作医院开始试运行。他们不但通过全科每次一百三十元的“打包”收费制度,试图让90%的病患在全科门诊得到治疗,而且还采用更为灵活的医生聘任制度,薪酬方面,最高年薪可达百万。更重要的是,参照香港,医院为医生购买了“职业责任险”,将医疗事故责任交予第三方处理,保证医生在治疗环节更加专心,改善医患关系。
在看病治病的问题上,医患本应是一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本不该因为制度的设计缺陷而成为彼此猜疑,成为互相对立的双方。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但要给患者以支撑,让他们有更好的医院看病;也要给医生以保障。
【原载2012年8月26日《燕赵都市报·燕赵观点》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