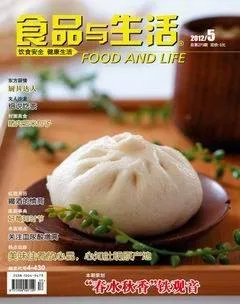吃豆腐
上海闲话“吃豆腐”,意味着明知你不会动怒,惹惹你,大家寻寻开心而已。因豆腐软嫩宜入口,不伤脾胃,因此也有存心“吃吃侬”的意思(善意的)。
说起来,豆腐还真是价廉物美的大众化美食,又富有营养。相传在2 1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在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因其成本低廉又富有营养,很快传至民间,有人专门以此为营生。所以,旧时的豆腐作坊都以淮南王为其祖师爷,以香火供奉。一度,许多民间习俗一概以“迷信”给否定掉,事实上,许多传统的习俗恰恰是出于民间的、朴素的一种道德阀门,所谓“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连小小的豆腐作坊都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大概因为现在不供奉祖师爷了,无所畏惧,因此豆制品良莠不齐,添加剂乱加。
豆腐进入寻常百姓家
豆腐行业可说遍及大江南北,各有风格特色。光南方就分上海帮、宁波帮、镇扬帮、安徽帮、浙绍帮等。其中,上海帮产品流传较广,除嫩老豆腐外,还有厚薄百叶、豆腐衣、油豆腐泡、油结子等。最有上海特点的当属臭豆腐,无论是清蒸还是油炸都美味可口,炸得金黄的臭豆腐脆卜卜、滚烫烫,趁热抹上一层嫣红的辣酱,是很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小吃。清蒸臭豆腐别有风味,夏日炎炎,人容易疰夏,蒸上几块臭豆腐,汪汪地浇上一层麻油,再撒上点榨菜丁和毛豆,是平民大众十分喜好的夏日开胃菜。马桥香豆腐干和老豆腐也是上海帮中很有代表性的。老上海人家还十分风行家制冰豆腐(冻豆腐),要在寒冬腊月时,将老豆腐放在板上,上面浇一层冷水,放在室外冻一晚,第二天豆腐冻结,裂成许多小孔,正好方便汁水渗入。所以,用冰豆腐做火锅涮料、砂锅鱼头时特别鲜美,还可与塌窠菜同炒,绿白相映,清口又好看。
宁波帮是以小板豆腐见长。此外,无锡的油面筋、苏州的卤汁豆腐干、镇扬帮的厚香豆腐干(如扣三丝)和浙绍帮的油豆腐都各有特色。
豆腐洁白无瑕,出身平民,恰如老派的小家碧玉,奉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都能尽心融入新的家庭。豆腐可以白烧也可以红烧,荤素随意搭配。故而,根据不同的地方口味和特色,豆腐可以衍生出各种地方特色菜,比如川湘帮的麻辣豆腐、镇扬帮的扣三丝、宁波帮的雪菜黄鱼豆腐、闽粤帮的茄汁杏仁豆腐,还有上海帮的各色豆腐羹。
老上海豆腐业者以特色和诚信取胜
豆制品虽然成本低廉,却也能入酒席,特别在素斋席上,豆制品是唱主角的。尽管豆腐如此受欢迎,但制作者大都贫困辛苦,主要是挑担窜巷自做自销。民间有句俗语:世上最苦莫如撑船、打铁、磨豆腐,可见,豆腐好吃,但制作豆腐的劳动强度很高。
为了改善自身处境,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有几位豆腐业中的元老,在南市乔家栅鸳鸯厅创立“豆制品同仁会”,以联络感情,团结同业。到底是东方巴黎大上海,连目不识丁做豆腐的也深切体会到要齐心协力,争取切身的利益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消费者的一份承诺。八一三战后,同仁会迁入租界,正式称为“上海市豆腐业公会”。
一般豆制品行业多分布在菜场闹市,前铺后坊,走的是小本经营、自给自足的作坊式之路。按理说,豆腐经营成本那么低,真的很难赚到大钱,然有个别精明的经营者,刻意在低成本中注重产品质量和特色,以提高产品的含金量。譬如,老上海有位叫金信生的,擅长做薄百叶。他做的百叶薄得呈透明状,摊在报纸上字迹隐约可辨,不但可作佳肴,用它来卷裹热油条,更是别有滋味,所以远近闻名。他还定期向著名的熟食店“陆稿荐”、“杜六房”酱肉店提供薄百叶,以制作鲜肉百叶包和酱汁百叶结,为这两爿名店锦上添花。这两爿店还特别注明:本店百叶由金信生提供。
另有依仗地段优势广交朋友而发家的,譬如有位姓顾的,他的摊位靠近成都北路富春茶楼和富春书场。他通过茶楼的堂倌和书场的茶保,兜销自制的酱汁豆腐干、素鸡、素鸭、素火腿等,然后双方拆账分成。因制作讲究、口味鲜美而广受茶客、书客的欢迎,成为上述场所的定点供应商,居然也发了家。
上海人就是会做生意,连最普通的油炸臭豆腐也上了霓虹灯广告。有位姓沈的业主在店门前马路口设摊,架起大油锅,亮起“油煎臭豆腐大王”的霓虹灯广告,吸引过往客人,生意兴隆。
可见,只要肯动脑筋、保证产品质量、老实做生意,低成本的产品也可以做得风生水起。问题是,你能否耐得住寂寞。
现如今,豆腐制作已是现代化的流水线,成批生产,传统的前铺后坊难觅踪影,当然偶尔也能见到,但终怕来路不明而不敢下手。
而今想美美地“吃豆腐”也不容易啊!
上海俚语与吃食
文‖程乃珊
民以食为天,不少坊间俚语都与吃食有关,生动贴切且朗朗上口。比如上海方言中,“面孔红得像杜六房的酱汁肉”、“侬这面孔哪能啊,像勒杜六房里的酱缸里浸过了”。“杜六房”熟食店创办于1938年,以酱汁肉、酱鸭、烤鸭、熏鱼等熟食制品享誉沪上。其中,红米烹调的杜六房酱汁肉尤为出彩,其味香甜、酥而不腻、入口即化。“酱汁肉”这三个字更一度被视为具有时代特色的上海地方语言。
“耳朵忘记在陆稿荐”,指前听后忘记,对人家关照的事情不上心。“陆稿荐”于康熙年间在苏州开设,上海何时有不详,是与“鸿云斋”、“杜六房”齐名的老上海三大卤食店。“陆稿荐”的猪头肉十分出名,“耳朵忘记在陆稿荐”,隐喻你的耳朵是对猪耳朵。
一般有经验的食客都知道,去饭店千万不能点炒什锦和三鲜汤,因为大多是厨房里的下脚料混在一起煮成。“烂糊三鲜汤”,指做事没有章法,乱七八糟,邋里邋遢、混沌不开,“侬做事体有点计划好伐,不要这样烂糊三鲜汤。”此语尤指作风不检点的女性:“这个女人是个烂糊三鲜汤,随便啥男人伊都要搭讪。”
“蛤蚌炒螺蛳”,指硬来横插一杠,掺杂在其中不受欢迎。想来因为蚌蚬、蛤蜊和螺蛳都是硬壳食材,可独立成菜,硬把它们混在一起,既不协调,味道也相冲,多此一举。
“阿旺炒年糕,吃力不讨好”,指卖力干活却得不到赞赏。炒年糕讲究慢火细活,火太旺反而要炒焦。此话源自宁波,因宁波男子名字中多“旺”,凡名字中有“旺”者,小名就被叫作“阿旺”。旧时习俗男人不上灶,阿旺一上灶就乱套了,干不了活,还要被老婆臭骂。
方言带有很强的时代特性,比如“飞机上吊大闸蟹——悬天八只脚”,指毫无着落、不着边际,这句话肯定是飞机发明后才有的。“吃外国火腿”,指被外国人欺负。洋人在旧上海目中无人,拳打脚踢中国人是常有的事,挨了外国人一脚,穷苦百姓不敢反抗,只能来点阿Q精神,自嘲一番。被外国人欺负,有理没处讲,就是吃了外国火腿。看来这句话也是在洋人现身上海滩才有的。
“吃大餐”,西餐刚进入上海时,因餐桌礼仪多繁文缛节,菜单也全是蚯蚓文,看也看不懂,稍不留神就会让人贻笑大方。上海人怕失面子,很惧怕吃西餐,将西餐称为“大餐”。同样的,洋老板和洋校长找你谈话,看似不是破口大骂,其实话中有话,让你下不了台,所以也叫“请客吃大餐”,其实是批评你。
“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其实跟山东人没啥关系,一方面是押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旧上海人对异乡人的偏见。
过去上海人一般是不吃辣的,一点点微辣都受不了。“请你吃辣火酱”,就是给你点颜色看看。
“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叫花子穷,只要能吃的他都说好,意指对人对事没要求,“侬要帮这个人介绍女朋友难啊,伊是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