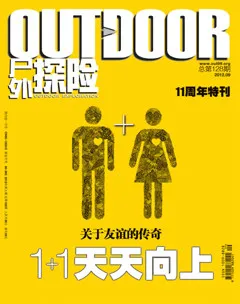相望江河






同船同帐
说起来,2003年漂流汉江初识晓光兄,最初,我还看着他并不怎么顺眼,原因大约是觉得这老兄喜欢扮酷,据说年轻时还演过电视剧,而我的习惯是不修边幅,对演艺圈文艺圈人士一直有固执成见。他是“野人”队长王方辰带来的,虽然我们两个都在湖北,都找“野人”,但之前一直未曾谋面。两月汉江下来,觉得这老兄其实是个热心的好人,但也仅此而已。直到后来,当我们“雅漂队长”杨勇要漂流长江南源当曲河以及通天河,与晓光兄等同船同帐,才结下了兄弟般的生死情谊,在老兄身上学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这次漂流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看河,看看这神秘的长江南源当曲,究竟是怎么回事。虽然我走过三年长江,但当曲一直是心中之谜。与长江正源各拉丹东和可可西里深处的长江北源楚玛尔河不同,南源当曲遍布沼泽,据称世界上最大的一片泥炭沼泽地就在这里。当曲,又名阿克达木河。在万里长江的三个源头中,是比较出新闻的一个,隔几年总会热闹一番,闹出与正源沱沱河孰为正源的争论。当曲之名,来自藏语“沼泽河”音译,位于青海省西南部,发源于杂多县境内的唐古拉山的北侧,一路形成巨大的沼泽水域,网状水系极为复杂。在陆地称王称霸的哪怕世界上最先进的越野车,在这里也被拒绝。但就漂流而言,这里地处高原面上,地貌落差不大,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急流险滩,我们就单艇前进。水上五人除了两个没有漂流经历的大学生,就是我与晓光兄和杨勇这两个老家伙了。
虽然我有过不少的野外经历,有些属于探险,但熟人都知道,我其实是个懒人,属于有地方坐着就决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的那种。和大多数人一样,经济条件允许的话,飞机能到首选飞机,机动车能到就机动车,机动车没路就自行车。1995年,在为徒步长江做前期准备的时候,我和晓光兄就在成都弄了自行车走甘孜玉树昌都芒康中甸丽江直到武汉。问题是很多地方自行车能走的路也没有,那就只有靠两条腿走路了。问题还在于,很多地方你走路也没有办法到达,对于认识江河而言,漂流这时就成为最佳选择。只为了走路而走路,只为了刺激而漂流,我们一般没那份闲心。晓光兄对此也深以为然,对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好奇和探究,就成为我们喜欢野外的源泉之一。
属于男人的英雄情结
这是一次不同以往的漂流。以前我们1998年的雅鲁藏布江漂流、2003年汉江漂流,都与之绝然不同。在那段梦幻般的高原水上行程中,与无人区浩瀚蓝天、罕见泉花台潺潺流水、孤狼和野驴慈眉善目等等诸般令人陶醉的美好景象相伴随的,是时时让人感觉仿佛置身炼狱般的肉体折磨。一切,都仿佛在传说与现实间徘徊。
“炼狱般的肉体折磨”—这是晓光兄的总结,他说:我们都快赶上特种部队生存训练了。
晓光兄又说:起码比美军特种部队还牛,特种部队哪有在这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连续体力透支还吃不饱饭喝不上水的?……夏季的高原烈日中,坐在镜子般的水面上的橡皮艇里,我盯着晓光兄皮开肉绽的嘴唇听着他的高论哭笑不得,但同时也慢慢理解了此兄浓重的军人情结或者说英雄情结。晓光兄15岁参军,自称有济世理想,常打抱不平,多以头破血流结尾,祖母在世时训诫为:好咬架的狗落不了一张好皮,仍屡教不改。他说:同龄人抱怨的那场“文革”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对于我这个不爱读书的家伙来说,恰相反,常窃喜,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逃学”了。这还真是与我不谋而合,虽然我现在做着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可打小还真不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也总逃脱不了男孩子心里的英雄情结。大概也正是这些发自骨子里的相似,才能让我们多年来一起不断地去经历生死。
我们那次高原漂流,壮丽背景中的悲惨日子,起因说起来却有点搞笑,这也使得晓光兄这位老警察很是自责。本来,当我们在青海玉树杂多县境内过澜沧江与长江的分水岭,抵达当曲源区那天,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正是黄昏时分,只见视线尽头的唐古拉山脉呈一个个尖尖的小三角,看起来并不高大,高极之高,其实平平和和。远近都金光闪闪,当晚,我们在海拔4800米左右的一个大水塘边扎下营来。前半夜还繁星漫天,一直深到地平线以下,下半夜却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很快,帐篷里就进了水。
两根木棒和进口油炉
刚开漂时,感觉漂流船重量惊人,行动十分困难,全船五人的各种装备和预计半个月的食品等全都在这只橡皮艇上,不可预知的漫长水上生活,这只船就是我们的家。
下水漂起来,所有的紧张和不快都烟消云散,天气也好得惊人,两岸风光美若天堂,正是久违了的美妙感觉。与以前漂过的大江河一样,源头地区水浅,都少不了拖船。当曲地处沼泽,水系更是复杂,平均10分钟就要搁浅一次。时值7月,头上的温度感觉起码有40℃,脚下的水却还是冰凉刺骨。这天,刚漂了一两个小时,天气就忽然大变,暴雨夹着冰雹狂砸而下,一会儿就浑身尽湿;一根烟的工夫,风吹云开,又是太阳暴晒。途中看到最多的野生动物是藏野驴,笔名苍狼的晓光兄,比我勤奋,每天日记很详细,他最喜此物,记曰:“它总是昂着头,迈着优雅的步子,绅士般的凝望。当它凝望着你的时候,圆润的眼睛透着一种真诚,它总驻足在岩石上,像一座雕塑,像一幅油画。它们一路疾跑,一路烟尘,消失在天际,带走人无限的遐想。”虽然我嘴上没事儿就嘲笑他酸文假醋,可心里还真是有那么点小敬佩。
漂到黄昏一靠岸,才发现一个重大失误,两顶帐篷的支撑杆都忘记在接应组的汽车上了。举目四顾,心中茫茫,在这样的地方,高于50厘米的灌木都不可能生长。而在预定的500公里漂流行程中,海拔一直在四五千米以上,也根本不可能有树。老天眷顾,望远镜里发现一个小白点,似乎是一家牧民的帐篷,忙去打探。不久,一大群热心的藏胞飞奔而来,两个小孩还扛着两根木棒,开价60元。晓光兄后来说,当时我还嫌贵,漂完以后,我觉得600块都值。因为到处都没一棵树,直到治多县城我没看见一棵树。
风太大,两顶帐篷搭得艰难无比,虽有藏胞相助,也是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的帐篷是在玉树买的80块钱一顶的白布做成的当地藏胞也只是用来喝茶的最简易的那种。开漂首日,搭建帐篷用去两小时。杨勇开始做饭,至凌晨1点才弄出一锅夹生饭——原因是晓光兄带来的一个进口汽油炉,老是出问题。
帐篷狭窄,中间一根木棒占去核心部位,人只有做S状态,舞蹈演员般睡觉。第二天早上,杨勇早早起来折腾到11点,还是拿那个炉子没有办法,仍是一锅夹生饭,饭后众人均腹中响如鼓。晓光兄特地搞来进口汽油炉,开始是炉头进沙,用细铁丝捅捅,再用嘴巴使劲吹,勉勉强强还能用,多花点时间,烧开一小壶水要两小时而已。那时担心的是,照此下去燃料很成问题,如果燃料耗尽还未到接应地点,后果将会很严重。头两天,除了夹生饭,我们每天每人还能分到白开水二两。随着炉子的脾气越来越大,最夸张的一次从6点多靠岸,到夜里12点多吃上饭,竟然用了将近七个小时。
本来,我们这帮人群威群胆在野外活动时,一直使用的就是家用普通煤气灶,挺好。这次,我们单船,只有五个人,为了减轻重量,晓光兄就搞了这个进口的小炉子。也不能说这精致的进口小玩意儿不好,在别的地方,在雪山、森林,大概都会挺好。可这当曲,沙子太多了,这玩意儿水土不服,这就有点要命。我们的高原漂流这就有了炼狱般的成分。高原烈日加上水面反光,几天就搞得人手脸脱皮,每天最渴望的就是能有充足的饮水。可最正常的时候,在船上一整天每个人分配的饮水也就二两的样子,堪比上甘岭。虽说没人埋怨他,但我依然能够感觉到晓光兄心里的自责。
有一天正午,气温升至极点,连空气似乎都在燃烧,人昏昏欲睡,感觉视线都有些模糊,晓光兄说:这是中暑的前兆,赶快掏出珍藏的法国“双人水”每人分数滴喝下,精神顿觉一爽。这一招望梅止渴,还真有效。口渴难耐时,两三滴这玩意儿进口,感觉上真就像喝了一大杯水,晓光兄郑重宣布为“重大发现”,喊着回去就要联络厂家改写说明书……
晚上,照例没水喝。晓光兄说:革命乐观主义不能少啊……其实,这一路上,最苦的也正是他,原因是他不光口渴还正在闹牙疼,腰疼病也犯了,但每天高强度的划桨,从没见他有过一点痛苦的表示。他要求我保密,免得影响“军心”。
他说:男人嘛,很多事情,你只有挺住。
我的“蜜友”
好几个晚上,我被狂风吹醒,只见晓光兄坐在中央,抱着帐篷杆说:你睡你的,反正我睡不着……我很是有点抱怨自己没心没肺。这帐篷,没老兄抱着杆杆,早就倒成一个薄睡袋了。然而,的确太困了,我嘟囔一句辛苦老兄了就又沉沉睡去。
几天下来,我觉得这老兄几乎就是个铁人。牙疼得呼呼啦啦,白天没吃没喝,晚上还要抱着帐篷杆杆给我撑起一片能睡觉的空间。这就叫真男人吧?抓起酒瓶请他喝,他嘧了一口,顿时龇牙咧嘴,一是嘴唇早已烂得惨不忍睹,酒精一刺激,生疼。再则,他老人家酒量实在一般,一两白酒,绝对不省人事。但此行之后,我们出野外,他总忘不了备上好酒,而我也绝不会跟他客气—是兄弟,就不用多言。
好几次我也睡不着,就坐起来聊天。晓光兄说: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很能跑,也很善于跑的人,这个跑,不是指简单的“跑路”。我们现在都很少使用“探险”两个字,虽然很多地方是“冒险”也有男人骨子里的那种英雄情结的驱使。但我们喜欢用“考察”,因为考察是带有科学的元素,一个探究未知领域的使命,同时他也给你带来很多风险,反过来,一旦超越,就是一种超级的心灵与感官上的“逾越”。
天长日久,我发现晓光兄几乎每天都要整理背包,有人也问过晓光兄类似的问题:用时尚的话说,您的着装很酷,能谈谈您的着装吗?这与追求有关吗?
晓光兄说:一个男人到了30岁后,知识和阅历应该写在他的脸上,气质和风范应该表现在他的衣着上。服装不应该是最好的,但一定要是适合自己的。我选择服装就是觉得比较合适。我当兵和从警加在一起有近30年,军装和警服一直陪伴着自己,也许是一种情结难以挥去,所以我的服装多是军装风格,这些服装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都很耐脏。其实,我服装来源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赞助商,他们提供的户外专业服装,一个是我在超市买的批发,像汗衫,我身上穿的是在超市买的,九元钱一件,我一般会买一打,穿两年没问题。
十多天后,我们终于和接应的杨八爷等人汇合,结束水上漂流。晓光兄说:虽然在唇开手裂的时候,我曾经诅咒过爆裂的阳光和大风,但一坐到飞机上,我又开始思念它了,也许这就是高原的魅力所在……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现在的记忆里也真的更多是一幅幅天堂般的画面。有兄弟在身边,那些苦难,也都变得美好起来。
在野外,良好的团队气氛和愉快的精神生活对活动的成功至关重要。事实上,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最难过的大概就是晓光兄。这使他几乎落下病根,后来我们一起同行的多次野外行动,只要有晓光兄在,我就不担心饿肚子,他总能变戏法似地给我摸出巧克力啊压缩饼干呀之类不占地方的甜蜜食物。这时候,我觉得晓光兄真是一个“蜜友”。
不安分的兄弟
晓光兄是一个“不安分的人”,骑摩托车穿越过青藏高原,还是一个汽车越野高手,滑翔伞高手,曾从高空坠落大难不死,伤愈后从腰里取出的半斤钉子,看得我心惊。他滑翔伞出过几次事故后,胳膊骨折过,腰部骨折过。但这两年,我们在山里找老虎,很多时候不得不重装穿越,从没见他落后。我知道,他是硬挺着。脾气也一点也没变,去年,我们在湖北长阳看到一个天坑,为了看得更清楚,他一激动,就又找来滑翔伞航拍。为的就是看就要看清楚,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他是满意了,可让我这做兄弟的一阵心惊肉跳,还真是不让人省心。
这几年,我们一起在神农架找野人,在大巴山找老虎,还一起跑过很多次高原,也越来越默契。有一年冬季穿越可可西里,遇到大雪坡,为了安全,前两车都只留司机向下冲。我和晓光兄同车,坚持不肯下车,理由是我要睡觉,别烦我。而内心里,是希望车上多一人,能给开车的晓光兄打打气,使他能够更加平静。当然,对他驾驶技术的信任是前提。这,晓光兄理解,视之为同生共死。而我也越来越喜欢这种兄弟般的感觉。在晓光兄身上,体验到了很多男人之间才会有的东西。
有一年冬天,记得是大年初五,北京时间21点,长江源头各拉丹东雪山前,正在冰上驰骋的越野车发出一阵熟悉又令人心悸的轰响,车头扎进了冰面崩塌的尕尔曲。可怜的越野车像一头掉进井里的水牛,底盘搁浅在冰上。不幸之万幸,离岸边还不算太远。在这里对外援不要指望,全靠自救。多日的陷车、拖车已经养成了我们高度的协调和默契,各自抄家伙开始往水下打千斤顶、垫沙土。温度计显示,此时的温度已经接近零下40℃,但我俩头顶仍然冒着腾腾热气,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反复折腾,自救成功,越野车吼叫着爬出尕尔曲。看看表,已经过了12点。
此时的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于是决定就地扎营。这个季节的各拉丹东的夜晚,我们把能盖的能垫的都拿出,包括几张膻气冲天的羊皮。大衣裹在了汽车发动机上,对汽车丝毫不敢怠慢,那是我们的半条命。那个晚上的寒冷,已经载入永远的记忆。羽绒睡袋就像报纸一样盖在身上,后半夜双脚失去知觉,好像一直放在冰箱里。半梦半醒,我们哆嗦着挤成一团,挣扎着到了天亮。早上爬起来,帐篷被冻得像腊肉一般坚硬,里面雪花一片,每个人的睡袋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室外的温度已经达到零下43℃。双脚像被打了麻药一般,失去知觉,勉强走了几步,仍然没有感觉。数天以后,晓光兄三个趾甲变黑,开始脱落。但谁也没有抱怨,都说那天很值。
晓光兄说,举目四望,各拉丹东的早上显露出昨天没有见到的颜容,金色的朝霞铺满在尕尔曲的冰河上,湛蓝的天空如水洗过一般,远处的各拉丹东主峰闪着玉石般的光芒,我实在找不出赞扬的辞藻,只能说有种跪拜的冲动。
多年以后,也许我们都已老迈得无力再去探险,再去那些艰苦却美丽的地方,但我坚信在我们的心里总有那个兄弟,那个一起经过生死,一起吃过夹生饭,一起陷过车,一起钻山下河的兄弟!
税晓洁
记者、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曾历时三年徒步长江。曾参与过汉江、长江、雅鲁藏布江等多次漂流探险考察活动。著有《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寻找野人》、《我难忘的N个隐秘之地》等书籍。
徐晓光
探险作家,笔名:苍狼。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珍稀动物考察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航空协会会员(滑翔伞A级飞行员);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参与汉江文化漂流探险、金沙江上游生态考察、大渡河峡谷地质灾害考察、长江源头科学漂流探险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