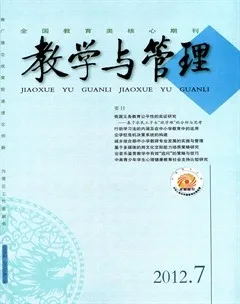荀子养成教育体系初探
所谓养成教育,是指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系统教育,通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使教育对象将社会规范内化为自我要求,逐步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行为习惯的过程。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荀子立足于儒家的基本立场,批判地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各派的思想、观点,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养成教育思想,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研究荀子的养成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人们加强个体修养将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荀子养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论
荀子的养成教育思想首先是建立在他对人性的考察基础上的。他从人性恶的基本假设出发,论证了养成教育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养成教育的基本体系。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在这里,荀子所讲的“性”是指天赋的本质,是指人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他认为人生来就有好“利”的本性,如果任凭这种恶的本性自由发展,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进而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发生“犯纷乱理”的事情。要防止这一行为的发生,就必须对人的恶进行控制,使其合于社会的要求。
荀子正是从人性恶这一前提出发,论证了对人进行养成教育的必要性。第一,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需要加以引导。因为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对人性加以限制,使人养成相关的品德,孝子之道和礼义法度都是限制人性的必要手段,有了这些管理的手段,才能收到避乱的效果。第二,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可以教育。养成教育对人性发挥约束作用是可能的。他用“人性朴”的观点说明实行养成教育的可能。尽管荀子认为人性恶,但他并不是极端的性恶论者,同法家韩非的性恶论有很大的区别,他的基本看法是“人性朴”,即人性经过改造是可以变善的。第三,圣人是教化人性之人。在他看来,人的社会意识、道德修养等并不是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正如他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仪。”(《性恶》),而是圣人“化性起伪”的结果。他提出“圣人化性起伪”说,认为人的本性只是质朴的材料,而礼仪道德是人为的,没有后天礼仪道德的加工,人不会自动变为善。圣人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化性”,用礼仪道德教化人们去恶从善。
二、旬子养成教育的目标——成就“君子”、“圣人”
“君子”、“圣人”的概念,是我国古代学者对一种理想社会的人格写照。儒家哲学在探讨人生问题时极为重视人格、人品等问题。荀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理想就是要通过养成教育塑造和培养君子、圣人,认为君子、圣人具有社会理想人格。
所谓“君子”,即能够接受道德教化、积累文化历史知识、实行道德礼仪的人。他说“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性恶》)。荀子之所以强调“君子”的培养,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君子有定国安民的谋略,可以治理天地、役使万物,对上可以辅佐王朝,对下可以引导万民。他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王制》),“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王制》);“君子者,法之原也。”(《君道》)、“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他说:“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君道》)。在这里荀子要求塑造君子人格,其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国家输送合格的人才。
所谓“圣人”,是指思想道德品质达到最高层次、人格最为完美的人。关于“圣人”,《荀子》中有多处描述:“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全称也。”(《正论》)。强调圣人的言论行为是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是人们效法的榜样。“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圣人是道德上十全十美的完人,“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即在“礼义辞让忠信”方面达到了极致,按照荀子的话说就是“积善而全尽”(《荀子·儒效》),所以圣人是众人学习的榜样,“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荀子·礼论》)。
三、旬子养成教育的内容——礼
荀子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准则,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大问题。“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修身》)。“人无礼则无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礼贯穿于人们的生活和政治统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在,无处不谈。
荀子还认为,礼有助于人们修身养性,培养情感,安乐人生。荀子说:“礼者,人之所覆也,失所覆,必颠噘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人无礼仪则乱,不知礼仪则悖。”(《大略》)。认为礼是人修身养性的根本准则,关系到个人的社会名誉。“人无礼则不生。”(《修身》),礼是人生之本,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人能懂得礼仪。“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认为规矩是方圆的准则,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无礼无以成人,礼是人道的准则,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他在《修身》中说:“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按照荀子的认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把“隆礼”放在核心的位置。
荀子还认为礼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礼的作用可以从根本上涵养个别性的情感欲望冲突,并使之可以理智化,这样就可以获得教养,这是对生命的最好安顿。“今以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固邪。”
由此可见,荀子强调的“礼”的内容是很宽泛的。它包括:第一,修身之礼。荀子说,无论个人的衣食住行,还是个人的礼仪交往,都应该符合礼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各方面顺利通达。衣食住行方面,荀子在《修身》中说:“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谩;饮食、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而不生。”在人与人交往方面,荀子在《修身》中也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第二,别贵贱上下之礼。荀子认为,人类是好群居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仅仅依赖个体修养无法形成良好的秩序,必须有一套规则完成社会整合任务。为此,“别”就成为荀子礼治思想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别”不仅仅指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而且是指严格的社会分工和等级秩序。荀子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非相》),“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同上)。荀子认为人或物都有相应的职分、地位、等级、权利、身份、亲疏关系、所属关系等等。但人们最难以忍受的是与自己同样的人凌驾于其上并控制着自己的各种行为,所以社会要稳定就必须人为造就一定程度的差别,“分均则势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王制》)。借助于贫穷与富裕、高贵与卑贱的差别,就可以使社会分工趋于合理,社会达到稳定。第三,治国之礼。治国要“分”。荀子认为人的各种欲求乃是出自其本性。所以,他认为治国要“分”。“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王霸》)。只有坚持这种“分”,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
四、旬子养成教育实现的方法和途径——学习、践行、积累、修身、榜样、陶冶
荀子开篇即以《劝学》告诫人们“学不可以已”,“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荀子指出,要改变自己贫贱愚昧的处境,实现富贵聪明的意愿,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要做到知礼懂礼,“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止乎礼而止矣,夫是谓道德之极。”荀子强调学习“礼”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他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騏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不仅如此,荀子强调学习过程中要专一,要不学六跪二鳌“用心噪也”的螃蟹,告诫人们要学无爪牙之利,劲骨之强,却“用心专一”的蚯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享受“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的愉悦。
人的道德修养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知与行的关系历来为我国的思想家所重视。荀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行重于知”的思想家。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儒效》)。强调“闻之”、“见之”、“知之”这些获取认识的过程,但更强调“行之”,只有践行才能将获取的认识用于规范和指导自己的实践,才是学习的根本目的。
荀子还特别重视“学以致用”。认为,假如不能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实践,即使学得再多,也无补于善心仁德的培养。将能否践行作为界定“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尺度。他认为,凡能做到“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行于动静”(《劝学》)者,为君子之学;若只是“入乎耳,出乎口”武装嘴巴,不见诸行动,则是“小人之学”。学风不同,人格自然不同。
荀子认为,对于礼的形成来说,要从细微之处做起,这样才能有潜移默化之功效。当一个人接受任何教育以后,其思想、性格的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对此,荀子做了专门的论述。“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也博,其为积也大。”(《强国》)。意思是说,有些人总觉得小事频频而来,早办迟办都可,期程甚宽,于是忽视小事,等到大事一旦到来才骤然奋起从事。这种人通常比不上那些对小事也认真对待的人。因此,他说:“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积微者速成。”(《强国》)。
荀子继承历代注重修身的传统,非常重视修身的作用。他认为,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之者穷。故大者不能,小者不为,是弃国捐身之道也。”(《大略》)。行为的善恶将反归于自身:“凡物有乘(因)而来,其出者,是其反也。”(《大略》)。善则安,恶则危,乃是一般规律;善而处危,恶而得安则是偶然情况。所以,君子由于仁厚睿智,立足于一般规律,故吉多凶少。小人行险徼幸,立足于偶然情况,故凶多吉少,所以荀子强调用仁义德行修身,“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漫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荣辱》)。
荀子还认为,修身对于统治者治国来说尤其重要,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君道》)。“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君道》)。
那么如何修身呢?关于修身,孔子强调“见贤思齐”,荀子也有类似的认识。他说,“见善,修然(整饬其容,敬貌)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偢然(容色变貌)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坚固貌)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蓄然(被污貌)必以自恶也。”(《修身》)。荀子强调修身过程中一定要诚。诚是关键。所谓的诚,即指真情实义,不自欺欺人。诚是一切行为的根本。只要做到了诚,就可以不怨天尤人,就会常常反躬自问:“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良善)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凯不迂哉?”这一思想显然是对孔子学说的一种继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使人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荀子特别抬出圣人、君子作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模仿的范型,并对圣人、君子的品行高度赞扬。在他看来,圣人、君子“佚而不惰,劳而不蔓,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恻,夫是之谓诚君子。”(《非十二子》)。另外,为了使人有效法的直接榜样,荀子还试图从不同角度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楷模,以引导和规范整个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成员的行为。所以,荀子将孔子、子弓称之为“大儒”,作为儒的典范;把尧、舜、禹等称为“名主”、“圣王”,作为君主的榜样。这样,就使道德规范既可以通过学习教育的方式获得并指导自己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暗示诱导影响人们的行为。
孔子曾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光辉论断,旨在强调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对人的影响。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观点,认为良好的文化氛围对人发展有陶冶作用。他说:“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在他看来,社会习俗和社会风气对人的发展会有很大影响,即所谓“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儒效》)。荀子曾明确指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因此,要注重良好文化氛围对人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
荀子的养成教育思想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力求改革、发展、稳定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挖掘、整理和研究荀子的这一思想,发现其对现代社会有价值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
在现代社会中,养成教育思想实质上是针对青少年个体进行行为规范教育的重要形式。目前,无论是从青少年成长阶段的特殊性,还是他们将来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来看,养成教育都不是可以忽视的。所以,探讨青少年如何在观念上、意识上接受社会道德规范并努力内化为自我要求,最终形成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就成为教育工作的核心问题。
当前我们养成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对青少年的主体地位关注不够,过多强调了教育中的灌输,造成了实效性不强的状况。荀子所提出的学习教育、实践锻炼、修身、榜样示范、陶冶等一系列养成教育思想的途径和方法,为我们在养成教育实践中关注青少年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为我们的教育工作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受时代和阶级观念的影响,荀子的养成教育思想还存在有一定的局限,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参考文献
[1]本文注释引自《荀子译注》,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中华书局1979年版。凡引〔荀子〕只注篇名。
(责任编辑 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