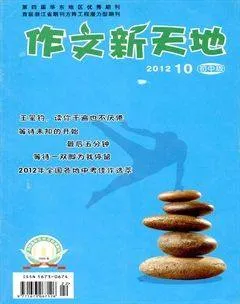芙蓉镇与伤痕文学
提到南方古镇,人们会想到丽江、凤凰,当然,还有芙蓉镇。古华在《芙蓉镇·后记》中说:“我探索着,尝试着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寓政治风云于民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这样,便产生了《芙蓉镇》。”
古华写这本书时,正是伤痕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伤痕文学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重要内容,以悲欢离合的故事,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是血、声声是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实际上,伤痕文学的前期作品大都质地粗糙,只是直白的陈述与控诉,没有反思和打磨。而《芙蓉镇》作为伤痕文学的后期优秀代表,不仅仅有着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作者进行了反思,并且,着重描述了人性的美好与丑恶。
芙蓉镇是湘南的一个小镇,处于三省交界,用书中杨民高的话来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死角”。打开小说,首先映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山镇风俗图,作者用了四分之一的文字来描写这座湘南小镇的环境以及主人公的背景介绍。这四分之一里面,有对芙蓉镇秀丽风光的自然环境描写,更多是对湘南淳朴民风和特殊民俗的社会环境描写。我们看到有美丽、温馨的画面,例如“满庚哥和芙蓉女”邂逅的渡口码头,那薛荔古树所形成的夹道浓荫,和明净的河水倒映着的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同样,也有令人心酸、伤痛的画面,例如公安局召集“五类分子”对笔迹时,一个十二三岁稚嫩的孩子替爷爷当了“历史反革命”,也许这个时候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革命。
芙蓉镇虽小,但各色人物各级政权倒也齐全,正如书中李国香所说,“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里有美丽善良却被划为新富农的“芙蓉姐”胡玉音,有佯装癫狂的“右派”秦书田,有正直仗义却屡遭打压的南下干部谷燕山,有内心矛盾备受煎熬的本地支书黎满庚,有好吃懒做却深得组织厚爱的“运动根子”王秋赦,还有叱咤风云无恶不作的“政治女将”、外来干部李国香,甚至还有奸诈狡猾的幕后黑手县委书记杨民高。同样,芙蓉镇还有各级革委会,有公社,有大队,现实中大时代有的人物和东西,小山镇里都有。小山镇里的遭际,让读者看到了大时代的悲剧。
当全国开始“左倾”思潮泛滥时,一切开始改变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美好风俗一下子或者说是猝不及防地变成了“人人防我,我防人人”,现实就是那么严峻。大时代尚且如此,小山镇岂能例外。芙蓉镇原本美好而又质朴的风俗,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互相举报,道路以目。就如同秦癫子,采集民歌编制民曲,为保留传统民俗奔波辛劳,却被冠以用反动歌曲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罪名。
古华在小说的扉页上题下了这样的几个字: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在这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中,我们看到人们虽满目疮痍却从未停止过反思,问号在他们的大脑中不停地闪现,其中包括了对党的政策、对革命等重大问题的思索和怀疑。比如谷燕山与黎满庚吃狗肉喝酒一节中,老革命谷燕山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今有的人,心肠比铁硬……他们吃得下人肉啊!……可是上级就看得起这号人,器重这号人……人无良心,卵无骨头……这就叫革命?叫斗争?”黎满庚甚至以嘲弄的悲愤的口气喊出了“革命革命,六亲不认!斗争斗争,横下一条心……”等等一系列的提问。小山镇的荒诞故事使读者进入到作者的沉思之中:“中华大地到底怎么了?”“这个大时代到底怎么了?”
黑暗不可怕,罪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在这种黑暗与罪恶中沉沦。正是有这样的一批人,对心中的美始终没有放弃,良知仍然没有泯灭,才使得在党性大于一切的环境里,人性显得弥足珍贵。只要心没有死,哪怕是像秦癫子所说“像牲口一样活着”,都会有光明的那一天。“文革”结束后,黎满庚一家心里虽不好意思邀请胡玉音带着自己的孩子进屋坐一坐,但一直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着小军军。小山镇里的朴实民众的这些行为,让我们看到,人们互相关心爱护的美德,并没有因为十年浩劫完全泯灭,现在又重新回到了人间。这让人快慰,但也使人辛酸,因为这场浩劫毕竟在人们的感情上制造了裂痕,要完全恢复到“牵了娃儿过来坐坐”的境界,似乎还得走一段相当的路程,可见在大时代里,“四人帮”对人们心灵的戕害是多么严重。
古华对心灵和人性的描写,对政治运动的反思,使得《芙蓉镇》在同类作品中鹤立鸡群。尤其是小说的结尾,更是令人深思。曾经癫狂的人正常了,还当上了县文化馆副馆长;而曾经正常的人却真正癫狂了,由镇长沦落为乞丐。但是,李国香没有处分,杨民高没有处分,真正的底层人物王秋赦却遭到了处分。“让文化大革命隔个五六年再来一遍”的疯子般的嚎叫让人心寒,更让人深思。作品的这些描写,没有抱怨什么,也没有高兴什么,而是理性地让我们记取那些令人心悸的教训,卸却身上因袭的负担,重新开始更美好的生活。
小山镇里,秦癫子和谷燕山也许是唯一清醒的人,他们如同诗里所说: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而在大时代里,同样,也只有那些知识分子和真正的革命老干部是清醒的;同时,他们也是最孤独的,领先于时代的人注定是孤独的。他们或冷眼旁观,醉酒相看;或坚守底线,誓死不从,都没有主动参与这幼稚而疯狂的政治斗争。正是这些人的反思和抗争,才使得阴暗的时代得以走过去,才使得芙蓉镇得以恢复到淳朴的本性。
小山镇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时代的盛衰兴亡;大时代下,我们得以反思小山镇的离合浮沉。小山镇与大时代,一本充满人性思考的书。这,也许是《芙蓉镇》最想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