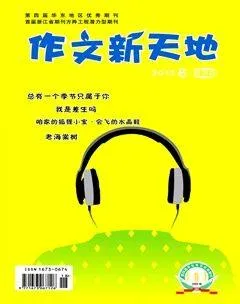文学,我的秘密花园
此刻我坐在电脑旁,打开文档,想要写一篇和写作有关的随感,竟对着空白文档木然了近十分钟。本以为想说的有很多,那些和阅读写字有关的感受,它们在无数深夜或白天化成只言片语冒出来再消失,像瓶口的啤酒泡沫,抓不住,或者被囫囵咽了下去。写作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三年前五年前和在现在,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十五岁时,妈妈送给我一本小说,是秦文君的《十六岁少女》。妈妈说,这是一本给人力量的书,我可以读读。我怀着期待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之后久久回不过神来。确实是一本好书,我被书中的人物深深触动。在读完那本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脑子里时常浮现出故事里的片段、画面、对白,我开始忍不住手痒,也想写一些句子,并渐渐迷上那种创作的感觉。我开始非常认真地对待作文,不再像以前一样愁眉苦脸敷衍了事,而是当做一种享受,一种表现机会。兴趣果然是最好的老师,我的作文进步飞速,常拿高分,到初中时甚至成了作文尖子生,作文簿常常被老师拿上讲台作为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
是在那个时候,我在这样一种令人眩晕的成就感中认定,我要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吧。我开始扩大阅读量,去书店的次数更多了,渐渐把目光对准大部头作品,比如张爱玲系列、绿皮外国名著系列。同时心里有种蠢蠢欲动,像是一个幼芽在骚动,它时不时地蹿出来几下,等待着机会破土而出。初二时我在一本青春文学杂志的内页看到一则征文比赛的启事,一等奖有三千元的奖金。我很用心地花了三天时间写了一篇作文,一个月后我收到通知,我进了初赛但需要汇款三百元才能进入第二轮比赛。我很疑惑,爸爸说这是骗取参赛费的山寨比赛。我虽沮丧了很长一阵子,但并没有因此泄气,而是更加积极地给靠谱的报纸杂志投稿。初二时我收到《中学生学习报》的样刊和汇款单,拆开信封的那一刹那我的心跳得极其诡异,激动得语无伦次,在报纸的第二页赫然看到我的一首小诗——《这年我们十三岁》。我推着自行车回到教室时,因为自行车的脚踏外壳掉了,只有光秃秃的一根尖铁棍在那杵着,等我到教室门口时才发现小腿肚子在流血,是一路上被铁棍戳的,而我竟因为太高兴而浑然不觉!
那的确是个至今想起来心头还有阵阵暖流的时刻,我第一次领稿费,也第一次体会到自己的名字和文字印到纸张上的感觉。晚上我把那张报纸放在枕边反复摩挲,兴奋得睡不着。
中考后我进入一所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级,学业的压力、竞争之强烈一度让我灰心丧气,我变得内向寡言,也只有在放学后,偶尔在摘抄本中写一些心情随感让我感到放松。有时我会写很多很多,长篇大论地倾诉高中生活的苦闷,情到深处泪水打湿纸张。现在看来是多么矫情的事情,但在当时,文字确实给了我那么多的安慰。高三时我收到“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赛通知书。我早就知道这个比赛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知名青年作家的起点。又一次兴奋得睡不着。事后种种也证明那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我通过新概念认识了很多同样爱好写作的朋友,那几个夜晚我们在比赛主办方安排旅馆彻夜长谈,聊梦想,聊文学,那些画面成了今日金光闪闪的回忆。也是在那时我才知道,或许是从某一个我没有留意的瞬间,我已经把文学放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了。在那以后我又投过稿,上过一些文集、杂志,进入过TN2文学之星比赛的全国45强,见到郭敬明、笛安、落落等作家。之后上了大学,对文学厌倦过,又重拾,又厌倦,又重拾,直至今日,发现我可能真的离不开写作。
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不是好玩刺激的游戏,此时的我,可能再也不会把文学挂在嘴边,动辄热爱文学。因为这条路艰辛困苦,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但我也深知,艺术都是血泪之子,只要渐渐克服了这过程中的寂寞、厌倦,以及对自我能力的怀疑,它终究会给人意料之外的回报。比如,它给你一片私人精神花园,这是没有付出过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快乐。我会一直写,写到这片精神花园越来越庞大美妙斑斓。
- 作文新天地(初中版)的其它文章
- 只等季节,没有不开的花
- 细化,让作文丰盈起来
- 于祠小记
- 生活中有语文
- 三岔口
- 奶奶爱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