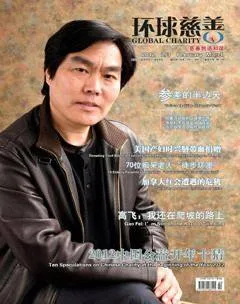大额捐赠局中局
好似因为坎坷颇多,2011年早早地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早到的春节使漂泊在外的人开始酝酿回家这件大事,却在此时得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要发布《2011中国捐赠百杰榜》。我们实在不知经历了剧烈震荡的中国慈善,还有多少富人会站出来义无反顾地捐,怎么捐,捐给谁,又将有多少富人淡出公益的舞台。
■悲观预测
2011年公益议题成为主流媒体所追捧的热门,也成为很多人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然而,这种主流化却是来自公众尤其是网民对于慈善组织和慈善人物相关丑闻的关注,以及引发的一系列信任危机。
谈及慈善人物,满身争议的陈光标占据了2011年上半年的主题。2011年年初,“标哥”率领50余位大陆企业家组团赴台发红包,先在台湾遭遇尴尬,又被大陆公益组织指为暴力慈善。
“我从来没否定过基金会的功劳和成绩,但中国目前的慈善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非常需要我这样的富人去高调推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首期中国基金会领导人高级研修班”上,陈光标与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基金会秘书长展开对话。在对话阶段,数位基金会秘书长建议陈光标建立基金会,或与专业公益组织合作,提高慈善的效率,但其称,目前不考虑与专业组织合作。
2011年9月,陈光标又毅然在贵州毕节举行了个人慈善演唱会,并把2000头猪、1000头羊、113台农机具拉到了演唱现场。他依然继续他那“标”牌式的“光标”精神,继续面对面派红包的巡回活动。
“标哥”的高调慈善到底是慈善不透明的无奈之举还是自己的有意而为?信任危机虽非2011年的专利,却从未像2011年这样蔓延,并直接导致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在个人捐款方面大幅缩水。近几年,个人捐赠在年度社会捐赠总额中所占份额有明显上升趋势,其中八成来自企业家。依此类推,我们似乎有理由猜测,富人慈善可能再度走回“标哥”的面对面派红包,或彻底蛰伏起来。
■出乎意料的统计
“一开始大家估计慈善家不敢捐了,没想到,慈善家们在质疑声中开始了大额捐赠。”2012年1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小会议室里,院长王振耀手里拿着《2011中国捐赠百杰榜》,回应在场记者询问的目光,“统计的结果我也很吃惊!”
据《2011中国捐赠百杰榜》统计,2011年大额慈善捐赠活跃,单笔1000万元以上捐赠超过250笔,其中本榜单100人千万以上捐赠超过140笔。年度捐赠总额超过1亿元的22人,其中曹德旺因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股票3亿股市值35.49亿元,位列榜单第一,黄怒波向北京大学捐赠9亿元等,大额捐赠笔数远超过往年。
对此王振耀认为,2011年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质疑,是中国公众接受现代慈善理念最好的契机,更是促使中国慈善家理性思考现代慈善的契机。
2010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之行,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富人如何慈善的风暴,接之而来的是牛根生、曹德旺等慈善家携家眷低调来到美国,拜访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国际慈善组织,探讨基金会的管理,甚至慈善家家庭的管理经验。
美国基金会以独立基金会为主,其多为企业家及企业家家族发起,他们将自己的商业思维和企业智慧运用到基金会中。在美国,基金会扮演着三大社会角色:驱动者、伙伴、孵化器。他们认为,有组织、成系统的科学捐助才是解决贫穷和消除罪恶的根本方式。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将私人及企业慈善从临时性资助带向长期、有规划的慈善。但如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中比例最大的并非个人或家族发起的独立基金会,商业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的程度还不高。
但此次牛根生、曹德旺等慈善家的美国之行,可谓收获颇大,他们开始向研究界寻求帮助,积极调整自己的慈善战略、基金会的组织结构和投资方式。
■未来三年趋势
“我预计,大额捐赠将成为未来三年的趋势,并逐步成为常态。真正的现代慈善模式正在静悄悄地建立起来。”对于王振耀这样的猜测,既是意料之外也是预料之中。
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11月24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达到1324家,其中以企业或企业家名字命名的公益慈善类基金会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特别是新成立的基金会,往往是资产较多、收入较多。
《201l中国捐赠百杰榜》分析简报显示,2011年度政府接受捐赠约17亿元,约占总捐赠额的14%,较之以往大额捐赠进入政府的情况,2011年,发起成立基金会或在基金会、慈善会等公益组织中成立冠名基金成为个人或企业捐赠的重要趋势,体现出大额捐赠开始向制度化发展。
大额捐赠在中国的出现对中国财富的传承、道德建设、诚信建设都将产生巨大的作用。其能集中解决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让慈善的社会功能展现出来。因为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只需花掉基金余额的8%。其可以自主地确定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公益项目和善款自主方向。所以,对于原始基金动辄过亿的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富人的大额捐赠,意味着捐赠方对资金的使用将有更大的话语权,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改变。
但在看好大额捐赠趋势的同时,如何引导更多的慈善家走上社会投资家的道路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如何界定非公募基金会与企业家之间的独立性问题上,一度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企业家应完全脱离对基金会的管理或参与;一种认为只要不存在公益营销行为,就可以包容。我们不否认企业家个人魅力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我们也期待善于与慈善家沟通的专职工作人员的增长速度能够承载此类基金会增长的速度,这是保证大额捐赠向制度化方向稳步发展的基石。